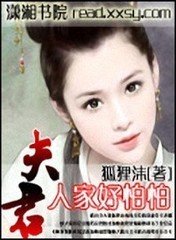河套人家-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芳哽咽难语,反反复复就一句话:“谁也别想夺走你! ”
两个人紧紧相拥,忘记了多长时间。
于芳一直生活在赞誉中,光环中,平生第二次饱尝了什么叫屈辱。在最痛苦的时候,她记忆中偶尔闪过被夺走心上人的刘改芸,她忘不了改芸脸上的眼里的绝望神情。
原来,被人欺凌,是这种滋味。那会儿,她体谅过刘改芸吗? 不仅没有,还十分憎恶她,一个地主的女子竟敢引诱工作队员,也不撒泡尿照照?
也许,当她狼狈不堪时,在别人眼里,她也并不光彩照人吧。
风声平息一些后,于芳和方力元在夜深人静,相互温存后,对心里的疑团寻找答案,他们从什么地方得知方力元在红烽发生的事情呢?
于芳回忆每个细节,均滴水不漏,而且在他的档案中,也没有记录。金如民队长曾想给他个警告处分,于芳据理力争,强调阶级敌人的伎俩在于破坏“四清”运动,终于让金如民松动了:“那你可得狠狠枇评他! ”
这句一锤定音的话,于芳至今记得真真切切铁板钉钉。
“只有一种可能,”于芳说出她的推测,“你的入党申请交上去有半年了吧? 说不定,搞外调的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听到点风声,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呀! 何况那会儿……满村风雨。不过,查无实据,红烽的人决不可能信口开河。”
事情正像于芳预料的,是方力元单位的人从红烽公社道听途说,把方力元关起来的。他父亲那会儿已经成了走资派,牵扯一下也合情合理。
虽说一场虚惊,方力元不仅受了皮肉之苦,他的入党也成了悬案,三四年以后才如愿以偿。
于芳苦心孤诣把方力元弄到手,一直风平浪静,这一波折,使她顿悟,世界上还真没有铁打的江山,当初,她毫不留情斩断了方力元和刘改芸的情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安安稳稳经营他们的爱巢,哪能料到风波又起,备受磨难。
可见天下大事,并非谁能运筹了的。
这次小小的灾难,并没有使他们的小家庭伤筋动骨,比起那些家破人亡的不幸者,仅伤皮毛而已。
随后的日子,风云变幻,翻云覆雨,他们俩就随波逐流,既无力回天,那就听之任之吧。
不过,经过十来年的折腾,一回想那叫人发疯的一幕,于芳仍然心有余悸,对自己当初为了爱选择这个小镇已毫无感情,这也是她听说“四清”工作队长金如民当了旗委书记后,赶快调动的原因。
但愿我们的后代,再也不要重复那个梦,一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她首先想说这句话。
“要是刘改芸和赵六子有了后代,也该二十来岁了吧? ”于芳偶尔也在脑海中掠过这样一个推测。
1
从从梳洗打扮完毕,家里的其他人还没有动静。
她吹灭了煤油灯,屋子里立刻就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把她用过的这粉那膏的芬芳,把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都淹没了。
窗户开着,纱窗外面的天色还一片漆黑,星斗齐辉,一钩淡淡的几乎看不出的残月,悬在院子当中那苗白杨树上。
东边的屋里,传出父亲深沉的鼾声,连妈妈都还在梦中呢!
西边,丕丕的屋里静悄悄的。
昨天晚上,从从向成波请教音乐的事。回来得挺晚,妈妈把饭热了两回了,一个劲地嘟哝。
从从匆匆扒了几口,就放下了,她说要备备课。
看到女儿又精神焕发,有了生活的劲头,当妈的自然求之不得,也就不强迫她了,只要心劲足,人是不会饿坏的,不是六十年代勒紧裤带的年头了,如今的年轻人,只有撑坏的可能。
水成波给从从拉了一个提纲,让她“参考”。田从从对它的重视,早已超过了“圣旨”的水平,岂能参考一下而已。
从从只看别人站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她可从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品味一下是什么感觉,她倒不胆怯,只觉得心虚:咋讲,砸了锅可咋办?
田从从在成波那儿获得的,与其说是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更不如说是上讲台的勇气和信心。
水成波以校长口气对她说:“不干则已,一干就得成功,如今时兴‘炒鱿鱼’,小心我把你又炒又煎! ”
“炒鱿鱼”这个时髦字眼,从从比他早听到而且有切身体会,招弟早就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对她讲过该字眼的含义了。
这个字眼儿,一旦从水成波口中说出,从从格外爱听,她笑着说:“成波哥,啊不,水校长,你煮我,炸我都行。”
水成波瞪她一眼,挺怕人的,她不便再说什么了。
从学校往回走,从从还哼着: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牧童的歌声在荡漾
她把成波的亲笔提纲抱在怀里,按在嘴上,捂在眼上,仿佛它是有血有肉,能笑会说的一个活人。
“成波,成波……”
一副痴迷人魔的神情。
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子,教个小学的唱歌,绰绰有余,她找成波,是为了寻找他的支持和亲近。
田从从把提纲看了两遍,就胸有成竹了。为了证实一下她的成功,她还对着镜子演习了几次,从表情到表达,她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还低声细气地唱了一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成波也没让她非教什么歌子不可。农村的小学,没有什么现成的教材,能唱几支歌子就行,包括《酒干倘卖无》之类。
原则就是“内容健康,朗朗上口”。
至于“健康”的尺度是什么,成波更没具体指示,那就全靠任教老师心领神会了。
直到快一点钟,从从才睡下了。
她刚盖上毛毯,忽然想起来,这几天弟弟总是天一黑就出去,挺晚才回,就像今晚,可能他还没回来。
从从又爬起来,拖上鞋,走出屋子,到丕丕屋的窗子下面往里看,里头漆黑一片,不过,从从还是看出,床上没有人。
“这人,到哪儿去了? ”
从从把村子里的同龄人过了一遍,只有李宝弟人过伍,跟丕丕能“纸上谈兵”乱侃一气,但要有个条件,没有烧酒,俩人是侃不成的。
可她看不出丕丕喝了酒更看不出有醉意。
丕丕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令人怀疑的神情。
他天天跟谁在一块儿?
从从心间放人了一个疑团。
回到她的屋里,从从好一会儿没能入睡。刚刚打一个盹,院子里忠于职守的公鸡,就喔喔地报开了时间。
她今天早点起,是因为开学的日子到了。
东边屋里有了动静,母亲边穿着衣衫,边过来,对她说:“吃点东西吧? ”
从从不置可否。
母亲到春灶上,往锅里添上水,开始点火,火光白烟一块儿从灶膛往外扑。
从从走过来,帮母亲烧火。
“妈,多煮几个鸡蛋吧! ”她这样说,与其说在商量,还不如说在下命令。母亲决不会拂逆她的愿望。
从从可以看出,母亲对她最近的状况表示满意,那眉毛疙瘩,舒展开来,脸上也涂了笑意。
“你晌午不回来了? ”母亲试探着问。
“今天开学,事情挺多,不回来吃午饭了。”从从显然在撒谎,火光照出她的兴奋和俏丽。
母亲点点头,锅里放了十个鸡蛋。
煮鸡蛋的工夫,丕丕披着衬衫从屋里走出来,脸上的睡意还没退尽。
“姐,我能不能享受几个? ”他走到从从面前。
从从放下柴火,把他拉到一旁,悄声说:“丕丕,老实交待,搞什么地下活动? ”
“我又不是八路军的交通员! ”丕丕笑嘻嘻地说。
“你不告诉我,就自己煮去。”从从说着,准备离开他。
丕丕的手指在她嘴上一按:“嘘! 你不能悄声点! ”
从从胜利地笑了。
母亲在灶台上忙活,根本不注意这姐弟俩神神秘秘干什么。
“鸡蛋熟了,我凉在盆子里了。”母亲说,“再熬点拌汤哇? ”
“好好,熬吧! ”从从连忙说。
丕丕把姐姐拉到墙角处,这儿立着许多去年的葵花秆,当柴火烧的。
别人的视线到这里就被遮断了。
丕丕说:“姐,我还正想找你,汇报汇报。”
“鬼精! ”从从哧地一笑,“顺杆子就爬上来了? 这么多天,咋不请示也不汇报? ”
“顾不上呀! ”丕丕笑着说,“我不能谎报军情哇! ”
“听你说,这回是八字有了两撇了,对不对? ”
丕丕点下头。
“丕丕,你是不是在搞对象? ”
后生又点点头。
从从心里又惊又喜,到底当过兵,行动雷厉风行,神不知鬼不觉,就搞上了。
“谁? ”
“你猜哇! ”
“你这么神秘,我咋猜? ”
丕丕在她耳朵上说:“她就是月——果! ”
从从没有惊讶,而是不安地问:“她,她跟你好? 月果,可是咱们芨芨滩的人尖尖! ”
“看你说的,姐姐,月果不愿意,我还能按住人家压手印呀? ”
从从说:“你真有眼力,姐姐支持你! ”
丕丕把她的手一拍:“多会儿咱们也是统一战线。姐姐,我看爸爸妈妈的阻力不会小。”
“还有大姐,她早给妈说过,在城里给你找对象……”
“这事,我能当家,别人的意见,只能供我参考。”
姐弟俩的话渐渐低下去,变成耳语,担心母亲听见他们向纵深发展的谈话。
“将来,爸爸妈妈要反对,我找水老师去给他们做工作。”丕丕说。
从从的心抖了一下,沉吟地说:“他,肯吗? ”
“咋不肯? 谁有了难处,水老师都肯伸出支助之手。”丕丕充满信心。
“但愿一帆风顺。”
“哎,姐,我看你近几天喜眉笑眼,碰上什么高兴事了? ”弟弟改变了话题。
“我? ‘民办’上了,为人师表了,能不高兴? ”
“哄我! ”
“少瞎说! ”
“看看嘴不硬哇! 姐姐,我真心希望,有个男人爱你。”
“会有吗? ”从从的声音颤颤的,这会儿天亮了,从从的脸色有点‘苍白。
“过来吃饭。”母亲喊他们,姐弟俩只好暂时结束交谈,到春灶跟前喝拌汤。
“给你,鸡蛋。”从从把盛鸡蛋的盘子推到弟弟面前。
丕丕向她投去含义深长的一瞥,笑着说:“姐,你可表里不一呀! 让人是个礼,锅里头没下米,你的眼睛里头伸出两只手,拨拦我哩! ”
从从在他的脊背上爱抚地打了一下。
“当了两年兵,嘴头子倒磨快了。”
丕丕嘻嘻地笑了。
吃过拌汤,丕丕说,他要去起山药,从从用一块大手绢把鸡蛋包上,满面春风地向学校走。
半路上,碰见宝弟,从从立刻沉下脸,目不斜视,想从他身边过去。宝弟挖开手拦住她,认真地说:“从从,我能不能跟你说说话? ”
从从想给他几句难听的,但转而一想,似乎不妥。从根本上说,宝弟并没有干下对不起自己的事,再说,自己成了老师,以后要注意形象和影响。
水成波不是谆谆告诫自己吗:“从从,为人之师,可得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己之不正,焉能正人? ”
是啊,出口不逊,岂不有损老师的形象?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李宝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宝弟,还加个李,”后生气哼哼地说,“从从,我那天喝多了,说了些屁话,你不要计较,行不行? ”
从从不做声,一脸不屑一顾的神情。
前几天,白白找见她,拐来绕去,刚说到这个话头,就被她生气地打断。
那次谈话,是在苏家的房顶上进行的。地方高,又没人打扰,还十分凉快。
从从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白白就无法代行红娘之职了。
“从从,我知道你想跟谁好,”宝弟一副破釜沉舟的果决,“可你就不回头思谋一下,那可能吗? 那现实吗? ”
从从的脸哄的一下红透了,也同时失去了冷静,怒目圆睁,扔过一句话:“葛针地里头放毛驴,有你入嘴的地方? ”
宝弟似乎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不恼不走不气,看着她说:“从从,你不心疼自己,也该心疼一下水老师。”
田从从一下愣住了。
他听出了宝弟话里的“骨头”,被击中要害而又不想承认的痛苦,使田从从的脸成了灰白,她几乎摔倒,宝弟急忙过来扶她,被她一把推开。
宝弟说:“从从,爱别人和被别人爱,中间没个等号不行呀! ”
从从已经心灰意冷地直想哭。
没想到,平时稀里糊涂的宝弟,对问题看得那么一针见血,那么入木三分。
她只能有气无力地说:“你,走,走开! ”
宝弟向她行个军礼,很听话地走了,一边走,一边频频回顾。
田从从手里的鸡蛋,差点掉在地上,宝弟走远了,三三两两的娃娃们又打又闹地出现了,他们是去报名的。
从从努力使自己恢复常态,跟他们一块儿往学校走,她昏昏沉沉的,有的娃娃们向她打招呼,她也没有听清,答非所问。
手里的鸡蛋变得像千斤石头,从她的心里坠下去,坠下去。
今天的好心绪,全被宝弟破坏了,双腿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