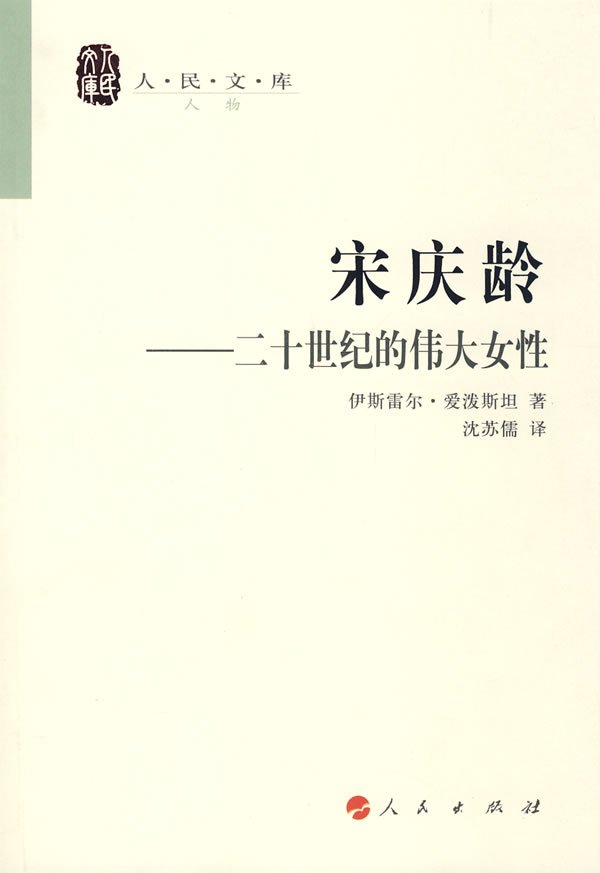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0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盖个戳子,打个码子的;我最留神这个,因为常有开了要紧的药,那病人到那小药铺子里去抓,我常常知照病人,谁家的药靠得住,谁家的靠不住,所以我留神到这个。继翁,你看这件事奇不奇!”我和继之听了,都不觉棱住了。我想了一想道:“这个是他家甚么人,倒不得明白。”端甫道:“他家一个少爷,一个书启老夫子,一个帐房,我都见过的。并且我和他帐房谈过,问他有几位同事,他说只有一个书启,并无他人。”我道:“这样说来,难道是底下人?”端甫道:“那天我在他们厅上碰见他,他还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抽烟,并不象是个下人。”继之道:“他跟来的穷亲戚本来极多,然而据他说,早都打发完了。”端甫道:“不问他是谁,我今天是过来给继翁告个罪,那个病我可不敢看了。他家有了这种人,不定早晚要出个甚么岔子,不要怪到医生头上来。”继之道:“这又何必呢。端翁只管就病治病,再知照他忌吃甚么,他要在旁边出个甚么岔子,可与你医生是不相干的。”端甫道:“好在他的病,也不差甚么要痊愈了。明天他再请我,我告诉他要出门去了,叫他吃点丸药。他那种阔佬,知道我动了身,自然去请别人;等别人看熟了,他自然就不请我了。”说罢,又谈了些别的话,方才辞去。
我和继之参详这个到底是甚么人,听那个声口,简直是要探听了一个吃得死的东西,好送他终呢。继之道:“谁肯作这种事情,要就是他的儿子。”我道:“干是旁人是不肯干这个的。干到这个,无非为的是钱,旁人干了下来,钱总还在他家里,未必拿得动他的。要说是儿子呢,未必世上真有这种枭獍。”继之道:“这也难说,我已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了。这里上海有一个富商,是从极贫寒、极微贱起家的。年轻时候,不过提个竹筐子,在街上叫卖洋货,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不多几时便发了财,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货铺子开着,其余大行大店,他有股分的,也不知多少。生下几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内中有一个最不成器的,终年在外头非嫖即赌,他老子知道了,便限定他的用钱,每月叫帐房支给他二百洋钱。这二百块钱,不定他两三个时辰就化完了,那里够他一个月的用。闹到不得了,便在外头借债用。起初的时候,仗着他老子的脸,人家都相信他,商定了利息,订定了日期,写了借据;及至到期向他讨时,非但本钱讨不着,便连一分几厘的利钱也付不出。如此搅得多了,人家便不相信他了。
“他可又闹急了,找着一个专门重利盘剥的老西儿,要和他借钱,老西儿道:‘咱借钱给你是容易的,但是你没有还期,咱有点不放心,所以啊,咱就不借了。’他说道:‘我和你订定一个日子,说明到期还你;如果不还,凭你到官去告。好了罢?’老西儿道:‘哈哈!咱老子上你的当呢!打到官司,多少总要化两文,这个钱叫谁出啊!你说罢,你说订个甚期限罢?’他说道:‘一年如何?’老西儿摇头不说话。他道:‘半年如何?’老西儿道:‘不对,不对。’他道:‘那么准定三个月还你。’老西儿哈哈大笑道:‘你越说越不对了。’他想这个老西儿,倒不信我短期还他,我就约他一个远期,看他如何。他要我订远期,无非是要多刮我几个利钱罢了,好在我不在乎此。因说:‘短期你不肯,我就约你的长期,三年五年,随便你说罢。’老西儿摇摇头。他急道:‘那么十年八年,再长久了,恐怕你没命等呢!’老西儿仍是摇头不语。他着了气道:‘长期又不是,短期又不是,你不过不肯借罢了。你既然不肯借,为甚不早说,耽搁我这半天!’老西儿道:‘咱老子本说过不借的啊。但是看你这个急法儿,也实在可怜,咱就借给你;但是还钱的日期,要我定的。’他道:‘如此要那一天还?你说。’老西儿道:‘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你只在借据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说我借到某人多少银子,每月行息多少,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咱就借给你了。’他听了一时不懂,问道:‘我借你的钱,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莫非你这一笔款子,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么?’老西儿道:‘呸!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怎么错到咱的爸爸头上来!呸,呸,呸!’他心中一想,这老西儿的主意却打得不错,我老头子不死,无论约的那一年一月,都是靠不住的,不如依了他罢。想罢,便道:‘这倒依得你。你可以借一万给我么?’老西儿道:‘你依了咱,咱就借你一万,可要五分利的。’他嫌利息太大。老西儿说道:‘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格外相让的;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总是加一加二的利钱呢。’两个人你争多,我论少,好容易磋磨到三分息。那老西儿又要逐月滚息,一面不肯,于是又重新磋磨,说到逐年滚息,方才取出纸笔写借据。
“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提起笔来,要有十来斤重。平常写十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也要费他七八分钟时候,内中还要犯了四五个别字。笔画多点的字,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及至仿了下来,还不免有一两笔装错的。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贡士殿试写一本策还难点了。好容易写出了‘某人借到某人银一万两’几个字,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没奈何,请教老西儿。老西儿道:‘咱是不懂的,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他一想,先是爸爸两个字,非但不会写,并且生平没有见过。不要管他,就写了父亲罢。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父’字,却不曾写成‘艾’字,总算他本事的了。又写了半天,写出一个‘亲’字来,却把左半边写了个‘幸’字底下多了两点,右半边写成一个‘页’字,又把底下两点变成个‘兀’字。自己看看有点不象,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了。又想一想,就写‘死了’两个字,总不成文理,却又想不出个甚么字眼来。拿着笔,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偏又在‘父’字上头,漏写了个‘等’字,只急得他满头大汗。没奈何,放下笔来说道:‘我写不出来,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再来写罢。’老西儿没奈何,由他去。
“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是他们日常聚会所在,自有他的一班嫖朋赌友。他先把缘由叙了出来,叫众人代他想个字眼。一个道:‘这有甚么难!只要写“等父亲死后”便了。’一个说:‘不对,不对。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不如用“等父亲殁后”。’一个道:‘也不好。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刻起讣帖来,必称孤哀子,不如写“等做孤哀子后”罢’。”正是:局外莫讥墙面子,此中都是富家郎。
不知到底闹出个甚么笑话,且待下回再记。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内中有一个稍为读过两天书的,却是这一班人的篾片,起来说道:‘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何故。那人道:‘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啊、殁啊的;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也嫌不祥。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包你合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个字是二千银子。便说道:“承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八折了,如何使得!’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两个说定,这四个字,一百元一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充了,才说出是‘待父天年’四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西儿了。那人代笔写了,老西儿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式式齐备。老西儿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西儿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三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西儿叫给他看。测字的看了道:‘这是一张写据。’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说道:‘不通,不通!甚么父天年!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甚么!’老西儿听了,就不答应。那人道:“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西儿道:“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儿的了。’于是一起同行,到得一家票号,各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西儿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其时票号里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西儿觉得票号里各人都看过了,惟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借据向桌子上一拍道:‘这是那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帐畜生忘八旦干出来的!’老西儿未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甚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道:‘到底写的是甚么?我们看好象是一张借据啊。’那客人道:‘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票号里的先生不懂道:‘是谁的老子,可以把性命抵得钱用?’客人道:‘我知道是那个枭獍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唉!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气罢了,唉!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的。’一席话,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西儿听了,知道写的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去划了一万银子给他。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他还问道:‘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甚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道:‘他几时说你孝敬?’他道:‘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细想,方悟到‘枭獍’二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七八万了。”
我听了不禁吐舌道:“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继之道:“大约分到他名下,几十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
过得几天,便是那陈稚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甚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地,所以他讣帖来了,我亦已备了奠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甚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七长八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缪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摘缨帽子,在旁边还礼谢奠。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计醉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揖;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枝笔不能叙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吊的事叙完了,再补叙他们来历的了。
当下计醉公让坐送茶之后,又说道:“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稚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排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卜子修接口道:“那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道:“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醉公又道:“今天开吊,子翁又荐了莫可翁来,同做知客。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员,上司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代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道:“没送帖子,不恭得很。”我道:“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费心,费心。”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卸下玄青罩褂,一面端详这客座。只见四面挂的
![[韩建国] 二十分钟等于_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