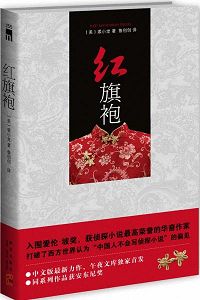蓝旗袍-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娘仨干着活,说着话,不知不觉一口袋玉米就要碾完了。说着话一抬头,一个人影窜进了灯影里,吓了玉翠一跳。看清楚了,来人却是桂兰,就阴沉下脸,骂道:“存粮发热,你不在家守着,跑来干啥?”
桂兰黑着脸,竟不答话,直冲春宝,气呼呼地问:“刚才你是不是回家了?”
“没有啊,俺一直在这儿。咋了?”春宝疑惑地望着桂兰。
“真没回去?”桂兰眼睛发直,声音发颤。
玉翠用髫帚扫着散落在碾盘四周的玉米粒,听桂兰问得古怪,手里的活没停下,话却早递了过去。“你得失心疯了?春宝一直在这儿,你一个劲地问这个干啥?吃饱了撑的?睡多了觉闲的?”
桂兰通的一声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玉翠气往脑门子上冲,手中的髫帚飞了出去,正砸在桂兰的脑袋上。“没用的东西,就知道哭!有啥说啥,嚎啥?”
桂兰不但没有停下,反而哭得更加厉害了。春宝急得抓耳挠腮,有心抚慰自己的老婆,却碍着玉翠,不敢太亲近,怕娘吃味。
春晖最见不得这个阵势,躲到了一边,眼睛里噙着泪,不敢看桂兰,又忍不住看桂兰。
玉翠心里像着了火,担心小孙子有了意外,就问:“老祖宗,老奶奶,你倒是说话!是不是存粮咋得了?”
桂兰缓过一口气来,抽抽噎噎地说:“存……存粮睡得好好的。”
“那你嚎哪门子丧?嫌俺老不死啊?”玉翠听桂兰这么一说,心放下了,火气却更大了。
“俺……刚才也迷糊住了,听见门响,以为春宝回来了。他爬到俺身上就要干那个,俺说,俺说……”桂兰又捂着脸呜呜地哭。
“你说啥了?姑奶奶!”玉翠弯下腰,瞪着眼直逼桂兰,脑袋几乎要抵到桂兰的额头上。
“俺说……孩子生病,你还有……心思干……干这个。”
“那干了没有啊?”
“这不,俺觉得不对劲,就来问春宝,他真没回去,呜呜……”
玉翠把嘴巴凑到桂兰的耳边,扯着喉咙喊:“问你到底干了没有?”
“呜呜……干了。”
玉翠抡起胳膊就是一巴掌,打得桂兰眼前金星乱晃。“丢人现眼的东西,畜类!连是不是自家的男人也分不出来,你还算是个人吗?”
春宝听明白了,抱住脑袋蹲到地上,像牛似的嗥叫了两声,忽然站起来,抽出一根碾棍,吼叫说:“奶奶的,俺去骟了那个杂种!”
“小祖宗,你找谁去?省省吧,先把你这脓包老婆拖回去,别在这里丢人!”春宝刚要往外冲,就被玉翠厉声喝住了。
春宝丢了碾棍,一把提起桂兰,像扛一口袋粮食似的扛在肩上,走出了碾坊。门外早立满了闻声而来的乡亲,春宝羞得差点儿没把脑袋缩进胸腔子里,埋着头一个劲地往前闯。
玉翠也不管碾好的没碾好的玉米,一股脑收进一个口袋里,背起来就走。走到门口,想起了春晖,便招呼:“好孩子,跟大娘走。”春晖早吓直了眼,听见玉翠叫他,才从角落里出来,挽住玉翠伸来的手。
玉翠对着碾坊外看热闹的人群气恼地嚷嚷:“看什么看?没见过推碾么?”人们闪出一条道来,玉翠牵着春晖风风火火地向家走。
春晖禁不住好奇,不明白桂兰为什么突然间又是哭又是叫的,就悄悄地问:“大娘,俺嫂子干啥咧?”
“小孩子家不兴问这个!”玉翠不耐烦地说。
春晖心里一震,感到委屈,眼泪就流了出来。这个玉翠大娘,虽说平时说话就响亮得像吵架似的,对他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硬邦邦地说话。
玉翠到家后,随手把玉米口袋丢在院子里,让春晖去睡觉,自己直奔东厢房。春晖还惦记着油饼的事情,没有挪窝,立在当院里。
春宝两口子相对无言,桂兰抹眼泪儿,春宝怔怔地发呆。玉翠进屋后,也不理他们,奔到土炕跟前。炕上睡着她的小孙子存粮,小脸儿红彤彤的,挨着存粮是一窝凌乱的铺盖。玉翠一把把被子扯到了地下,露出一条麻花一样扭曲的褥子,玉翠一眼就瞅见褥子上零星沾着些秽物,那刚刚压下去一点儿的怒气,又噌地一下窜了上来。她揪起褥子,提着出了门。
春宝两口子大眼瞪小眼,不敢说,也不敢动。玉翠顺手拿起春生赶大车的鞭子,到了大街上,把褥子往栓牲口的木桩上一搭,甩起鞭子,抽得啪啪响。尾随而来看热闹的,呼地一下子围了过来。
“羞死先人咧!”玉翠一开口,就声如金钹,响彻云霄。“瞎了眼的杂碎,你他娘的要下种,看清楚地茬再下,咋学满街乱窜的牙狗子,随地撒尿儿?你家先人都死绝了?缺爹管你吗?俺日你祖宗,日你八辈子祖宗,你的祖宗在棺材里也不得安生,天天翻身哼唧儿!”
桂兰听见玉翠骂大街,臊得头撞墙,打鼓一样咚咚响。春宝拉她,她沙哑着嗓子说:“你娘不让俺做人,俺不如死了干净。”
“娘也是气糊涂了。”
“她糊涂,村里的人可不糊涂,以后的日子也不糊涂。俺没法做人哩!”
春宝劝不了桂兰,就跑出来想劝回玉翠,在大门口一探头,见一街筒子的人,一缩脖子,没敢跨出大门半步。桂兰在东厢房里哭,玉翠在大街上骂,春宝在院里转。忽然春宝看见了木桩子似的春晖,便如同见了宝贝,奔过去拉住他的手央告:“好兄弟,去把你大娘叫回来。你要多少兔子,哥就给你套多少兔子。”
“我不敢。”春晖低声嗫嚅。
“没啥不敢的,你大娘最听你的话。好兄弟,哥求你了。”
春晖还惦记着油饼的事,春宝的话给他了勇气。
“畜类啊,辱没了先人们呐!自家男人都分不清楚,这哪是人啊,披瞎了一张人皮,活活的畜类啊!王八蛋的牙狗子,睡不着觉掂量掂量,你家的墓田就是大粪坑,窑姐儿的家什,千人拉,万人尿!……”
玉翠骂几句,抽打几下褥子,褥子被抽开了花,露出白花花的棉花絮来。玉翠正骂到兴头上,被春晖打断了。春晖拉着她的衣襟摇晃,连声说:“大娘,大娘,说话要算话,你还没给我烙油饼呢!”
气头上的玉翠,不管不顾地骂:“吃你娘个头!一边呆着!”
春晖被骂傻了眼,抹着眼泪钻出人群,撒腿就向学校方向跑去。
白香衣早睡下了。自从坠胎差点儿丢了命,她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加上心里有许多说不得的心事,便病歪歪的,少气无力。她刚合上眼,便看见春生向她走来。在梦里她竟无法拒绝春生,他的怀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她牢牢地吸住。半夜的敲门声惊心动魄,差点儿吓破了她的胆,梦境和现实混到了一块,她以为自己和春生的私情被人发现,人们来捉奸了。
敲门声还在继续,白香衣终于挣脱了残梦,回到了现实,心狂跳得如同逃命的兔子,紧赶慢赶地奔命。
“妈,开门!”
白香衣听出是春晖哭咧咧的声音,心里堵得慌。赶紧披上衣服,开了门。“怎么了?又哭什么?”
“俺大娘骂我。”春晖见了白香衣,委屈更盛,一双眼睛像两眼丰水期的泉子。
“哪个大娘?”
“俺春宝家大娘。”
白香衣的心一沉,心想莫非嫂子察觉什么了,心里便凄惶起来。“跟妈说说,她怎么骂你?”
春晖就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说自己的委屈。
听完了,白香衣明白了一个八九不离十,说:“春晖,你大娘不是骂你。走,咱们看看去。”
春晖不肯去,白香衣自己走向玉翠家。街上站满了人,玉翠还在叫骂。白香衣好不容易挤了进去,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有人掐了一把她的大腿。
“嫂子,咱有话家去说。”白香衣劝着,把木桩上的褥子拿下来,向家里推玉翠。
玉翠骂街早骂累了,但没人劝,骑虎难下,不好收场。白香衣一劝,玉翠象征性的挣扎了两下,就由着白香衣推进去,仍叽叽咕咕骂不离口。
进了院,白香衣反手关了门。玉翠停了骂,站在天井里呼哧呼哧地喘粗气。白香衣埋怨道:“嫂子啊,这是什么事儿啊,藏还藏不住,你这样子张扬,咱家桂兰以后还做不做人?”
“白老师,对付这帮子奸夫淫妇,就得狠!”玉翠咬牙切齿。
白香衣打了一个激灵,她说:“桂兰也不乐意这样啊?”
“她又不是死人,是不是自家男人还分不清啊,俺看她是明明白白地给人家的。”玉翠理直气壮地说。
白香衣想到了自己和春生,有些心寒。她定了下神,才说:“嫂子,你去你屋里歇着吧,我去瞧瞧桂兰。”
玉翠却紧追上来,夺她手中的褥子。香衣惊问:“嫂子,你这是干啥?”
“你别管。瞧好就是!”玉翠夺过褥子,扔在地下,进了自己的屋,一会儿端着煤油灯出来了。她把灯里的煤油撒到褥子上,擦着了火柴,扔了上去。一朵火苗摇曳着大起来。
白香衣嚷道:“嫂子你这是干什么?”说着就要扑过去救。
玉翠一把抱住了她,不让她动。“烧吧,烧吧,把杂碎留下的种烧得干干净净!”玉翠发狠。
火苗子一蹿老高,红彤彤地映红了小院,映红了玉翠的愤怒,映红了白香衣的错愕。春宝跑出来,看清楚了漠然地退了回去。白香衣好歹把玉翠劝回了屋,抽身过来看望桂兰。
桂兰蓬头垢面,额头青紫了一大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傻了一样,坐在炕上倚着墙角。春宝哭丧着脸,起身让座,白香衣坐在了炕沿上。春宝话没出口,先长出了一口气:“白老师,俺没法做人哩。”
“一个男人家,不兴说丧气话!”白香衣软语开导,“男人,就得有担待,这时候谁也没有桂兰难受,你要多劝劝她才是。”
“白老师,这事儿俺没法担待。”春宝长吁短叹地抱着脑袋。
桂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却明明白白的,听了春宝的话,心如死灰,撩起衣襟,胡乱擦了一把脸,对白香衣说:“白老师,他们娘俩,这是多着俺,往死里逼俺。”
白香衣才要替他们娘俩开脱,让桂兰别想偏了,钻牛角尖儿。屋门咣当一声大开,玉翠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指着桂兰的鼻子尖破口大骂:“你个不要脸的骚娘们!是俺们娘俩往死里逼你,还是你往死里逼俺们?你恣了,快活了,还想让俺们替你背黑锅呀!天理良心,你自己摸摸,还有没有?放在过去,凭你守不住妇道,俺就能让春宝立马休了你!够高待承你了,给脸不要脸!”
桂兰忽然疯了,破天荒地顶撞起来:“别总拿不让春宝要俺了吓唬人,俺才不怕哩。有种让春宝现在就不要俺。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眼巴巴地瞅着你家的儿子呀,那样的话,老二家的孩子早爬一天井了。俺巴结不上你们家,还不巴结了,谁稀罕?!”
玉翠没想到逆来顺受的桂兰会给她这么一顿抢白,还拿老二春生说事儿,捅她的心系子,气得浑身发抖,嚷道:“反了反了,这娘们疯了!春宝,春宝!你就眼瞅着你的畜类老婆欺负你老娘?”
春就扬起巴掌要揍桂兰,白香衣慌忙拦着。玉翠在一边一迭声地喊打。桂兰麻利地溜下炕,铿锵有力地说:“白老师,别拦着,让他过来!俺倒看看他有多大本事,自己的老婆被人欺负了,他不寻思找出那人替俺报仇,反而和他老娘一伙,可着劲欺负俺。真有种,只会窝在家里打老婆的男人,才算真有种!这样的男人,他不休我,俺还休了他呢!”
春宝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沮丧地耷拉下了胳膊。玉翠气急败坏地嚷:“你听听,你听听,她做下不要脸的事,还有脸了!”她攥起拳头,捶打春宝。“俺咋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畜类,你去揍她,往死里给俺揍!”春宝抱头鼠窜,玉翠就跟在后面追,娘俩像猫抓耗子似的在屋里兜圈子。
白香衣紧张地护在桂兰身前,心里纳闷,玉翠嫂子挺明白的一个人,到了自家的事上怎么就这么糊涂?忽然,她听见存粮哼哼了两声,忙过去看。存粮紧闭着眼睛,眼泪哗哗地流,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可见他早醒了,大人们大呼小叫,他不敢做声,只好偷偷的哭。白香衣心里一酸,眼里便滴下泪来,回身不高不低地说了一句:“你们有完没完?看看把孩子吓的,哭成什么样子了!”
玉翠护孙心切,放下儿子,赶过来看孙子,摸摸存粮的头,火炭一样,就咬牙说:“要是存粮吓出个三长两短,你们就瞧好吧!”这是玉翠大闹一场,忽然感到无味,最后收场的虚张声势。
桂兰心灰意冷,这话听在耳朵里便特别刺耳,心想存粮吓着了,也是你的错,还不都是你闹的,到这会儿了,却反过来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