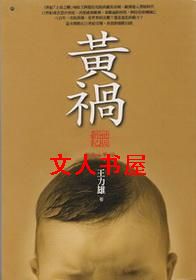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多楼一模一样; 都像又都不像。
他反复看图; 兜着圈子。
没有一盏灯光; 一个人影; 每栋楼都像鬼楼; 似乎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在里面居住。
忽然; 他在夜视仪屏幕上看见远处两楼的空隙之间走过一个人。
他从楼间小路把车开过去。
那人背着背包; 看上去远道而来; 虽然满天尘埃使数米外便一无所见; 却如白昼回家一样穿来拐去; 脚下没有半点犹疑。
这人可真是个救星; 一定能给他指明方向。
他刚想按喇叭叫那人; 可他一下发现自己也认识了。
这就是通向陈盼家的路。
方向、建筑、环境、标记; 全和图上一样。
他把车速放慢; 跟在那人身后。
尘埃和风声使那人毫无察觉。
看到那人走进陈盼家的楼门; 他一点没惊讶。
他已经从那背影的轮廓、走路的恣态和自信的气质上认出; 那就是欧阳中华。
一支蜡烛在陈盼的窗子里面亮起来了。
他看着那个窗口; 突然感到睡梦的深渊又在身下打开; 黑洞洞地深不见底。
他的手无意识地打开一个开关。
一幅彩色地图幻灯般出现在显示屏上。
那是一个中国; 内陆边境伸出一系列标着“6800km”的半径; 在太平洋上圈出一道曲折的线条。
他看一眼地图; 再看一眼陈盼的窗口。
烛光熄灭了。
几乎是立刻; 他伏倒在那幅地图前; 睡了过去。
中俄东方边境 黑龙江
那一夜; 从瑗珲到呼玛二百九十公里江段; 约有三千万人冲进俄国。
今年的春天迟迟不迈过北纬五十度。
往年这个时候; 黑龙江的冰面已经隆隆作响地开裂了; 现在却仍然结结实实。
只是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分; 冰的表面出汗似地化出一层水; 太阳稍一偏斜又重新冻死。
俄军的装甲车在冰面上奔驰; 拖起一道道白茫茫的冰渣尾巴。
然而; 冰层还是越来越薄了。
尽管大气温度还在冰点以下; 可失去了冬天透地数米的严寒; 在冰下流动的江水就开始侵蚀冰层。
下游成千上万往上走的人不断带来消息; 冰面开裂的地段一个劲上移; 昨天还在雪水温; 今天就到车陆了。
聚集在爱辉、黑河一带江边的人已经多得不能再多。
几乎看不见土地; 只有蠕动的人群; 乱七八糟的窝棚; 无数堆篝火黑烟遮天蔽日。
北方原来保留着中国最后一点森林; 现在却连一棵直立的树也看不见。
没烧掉的也全被人砍倒; 牢牢守住。
谁有火谁就不会被冻死。
为争几根树枝而丧命的人随时都有。
正是森林和黑龙江把人们吸引来的。
饥饿的人群抢空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那些大城市; 又席卷了每一座县城小镇; 最后连村庄农舍也被打劫一光。
能吃的都吃了。
凡是被人创造的也都被人毁掉了。
人们最后只能把手伸向上帝; 伸向幻想中富饶的大自然。
歌里不是唱过∶北大荒; 好地方;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尽管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形容了; 但是在饥饿的昏迷中; 美景永远就在眼前; 伸手可及。
只要到了森林里; 江边上; 狍子、野鸡、大马哈鱼、飞龙、熊掌、猴头就全到了嘴里。
蝗灾出现时; 乌云般铺天盖日的蝗虫落下; 无边的庄稼一会儿就被吃成千里赤地。
现在是放大了的蝗灾——人灾。
虽然人没有翅膀; 可人的嘴要大一千倍; 人的毁灭性要大一万倍; 人灾掠过之处; 整个世界都被毁灭。
不知有几个人吃到了狍子; 尸体却越来越多地到处散布。
人们看见死亡就像看见树叶落地; 哪怕是亲人在身边倒下; 也没有叫一声的力气。
唯一的念头就是继续走; 去寻找新的森林; 富饶的土地; 野兽和飞禽出没的地方; 肥硕的大马哈鱼一条条跃出冰窟窿! 他们停在了黑龙江边。
如果从天空俯瞰; 一定会看到一副极独特的景象。
黑龙江仿佛是一条蜿蜒的折缝; 江两岸如同被展开的平面。
中国这边是反面; 俄国那边是正面。
反面是黑色的; 黑得吓人。
积雪被无边的人群踩成肮脏的泥巴。
上空悬着黑烟。
城镇废墟好似一座座垃圾场。
正面则是一片银装素裹; 白得耀眼; 几乎看不到人; 只有无边的树; 间杂着一栋栋安静的房舍。
这景象连上帝在天上看也一定会纳闷: 一条江怎么能隔离出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 黑龙江的江面就更奇特了。
蜿蜒的主河道正中央有一条中心线。
在地图上那该是标明国界的点划线。
而眼前; 点是俄国边防军一辆辆奔驰的装甲车; 线则是履带在冰面上压出的辙印。
这条线的两侧更加分明。
俄国一侧是干干净净的冰面; 平滑得像玻璃。
中国一侧则凿满密如鳞片的冰窟窿; 露出黑黝黝的江水。
冰窟窿之间全都挤满着人; 紧挨在一起的黑头发就像蒙在江上的一张黑皮毛。
冰窟窿是用来捕鱼的。
这是北方特有的捕鱼方式。
鱼喜欢光亮和氧气。
如果江面上有那么星星点点几个冰窟窿; 鱼儿会争抢着聚到周围; 被上面的鱼叉扎中; 或者被送下去的鱼网罩住; 自己跳上来的也不少见。
然而半条江都被穿透了; 鱼儿们还有什么可争抢的呢 那半条江好似突然长出了无数根倒刺; 从上面伸下来一刻不停地搅和。
上面嗡嗡嘈杂; 透进人的臭气。
鱼儿的脑虽然不大; 这点聪明还是有的; 它们全都游到俄国一侧的冰面下; 反正它们也不在乎什么主权; 只当这条祖祖辈辈生息的江突然窄了一半。
捕鱼的人们停止了徒劳。
冰窟窿中的江水重新结起了冰壳; 冻住了树枝做的鱼叉。
人们相互挤在一起获得温度; 眼睛全看着对岸那片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
在众人的沉默中; 下游冰面开裂的隆隆声似在传来。
一头美丽的雄鹿突然出现在对岸一座山头上; 昂着高大的角; 雕塑一般挺立。
人们先是屏住呼吸看着。
多少年来; 中国这岸的野兽就没停过往那岸逃。
这边没有树; 没有草; 更没有安宁的天地; 只有专门割它们角、扒它们皮、吃它的肉的人。
它们会记住这个地方; 那就是逃出去就永远不再回来。
它们的生存本能中似乎已经有了国家的概念。
一江之隔; 它们的命运却完全不一样。
在对岸; 那雄鹿是多么的骄傲、大胆、甚至是蔑视地看着这岸啊! 连它身后的母鹿和小鹿也不在乎这岸的人群。
一个声音开始传播。
它最先出自黑河中学一位历史教师的口∶“那边本是中国的领土; 是被沙皇政府用不合理的瑷辉条约强占的! ”没经过几张嘴; 这话就简化成了∶“那边是我们祖宗的宝地; 是叫老毛子抢去的! ”中国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一直和苏联敌对; 近三十年的时间; 全民族饱受了新老沙皇侵略历史的教育。
现在昔日属于自己的大好河山就在前; 那有广阔的空间; 无边的森林; 肥沃的土地; 野兽出没; 飞鸟成群。
夏季的浆果成百万吨地落在地上腐烂。
声音越传越快; 变成潮水般的嗡鸣; 好似共振一样越振越强。
隐藏在对岸工事后面的俄军士兵紧张地探出身体; 架起武器。
嗡鸣突然在一瞬间消失; 无影无踪。
俄国装甲车的声音顿时显得非常刺耳。
然而装甲车组成的点划线开始变化; 如缓慢的波浪一般出现了曲折。
默默地; 后面的人开始推动前面的人; 岸上的人开始往冰面上挤。
不少人掉进冰窟窿; 却没有打破整体的沉默。
倒是俄国装甲车慌了起来。
它们紧贴着人群行驶; 把速度开到最大; 想把人群吓退。
然而即使有人被卷进履带之下; 模糊的血肉甩了前面人群满身满脸; 他们也无法后退。
背后那堵沉默而风雨不透的墙越来越厚; 越来越有力。
再多的装甲车也无法撞倒和碾碎这堵墙。
俄方的高音喇叭用中文发出严厉警告; 命令士兵们做好开火准备。
然而军事行动总是面对类似冲锋那样有幅度的爆发点才能开始; 对一寸一寸往前蹭这种典型的中国动作从哪开始呢 人群横着看不到边; 竖着看不到头; 完全是凝缩在大地上的一块史无前例的大肉饼。
人的数量可比子弹多得多。
爆发点终于出现了。
冰层本已变薄; 鳞状的冰窟窿又使冰层强度降低。
越来越多的人挤到冰上增加重量。
每只脚都使着劲儿; 往前挤或者往后退。
中心线凸起最大的那一段突然传出冰层之下一声轰然巨响; 大约一公里长的冰面垮下去。
上面的人一股脑掉进水里。
几辆俄军装甲车也一眨眼沉入江底。
千万人同时发出的恐怖叫喊如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震耳欲聋。
人群一下炸了窝; 冲向俄国一侧的坚实冰面。
俄军也呆住了。
他们不能向从断冰上逃生的人开枪。
然而逃命只是最初一秒钟的本能反应; 立刻就转变成突破封锁的全面大冲锋。
俄军仅仅犹豫了那么一刹那; 就已经淹没在人海中; 再也没有了反击的机会。
每个士兵身边都是滚滚人流; 怒吼着掠过; 把他们踩在脚底; 踩进洁白的雪中; 变成污黑的泥。
一处的突破带动了全线。
所有人全都向对岸疯狂地跑起来。
逃吧! 逃吧! 也许再过几秒钟冰层就全部垮掉; 就再也逃不过去。
留在这边就是死亡。
反正是死; 痛苦地饿死还不如挨一颗枪子儿更痛快! 突破口迅速扩大; 转眼就变成几公里; 十几公里。
冰面不断垮掉; 成千上万跑在冰上的人掉进江里。
更多的人被后面的人浪从陆地上挤下水。
在冰水里几分钟就会丧失活动机能; 几乎没有人活着爬上岸。
人群开始向上游跑; 只要哪的冰没垮; 就从哪接着往对岸冲。
上游的俄军开火了。
开始还有点犹豫; 逐渐越来越凶猛。
密集的子弹似镰刀割麦一样砍倒大片大片的人群。
尸体在冰面上魔幻般地堆积起来。
然而尸体没有吓住中国人; 他们的国土上到处都是尸体; 走到哪都如踩着破布般习惯自然。
现在他们不顾死活地往前冲; 踩着死人; 也踩着活人。
当俄国士兵看着那永不消失的人群瞪着疯狂的眼睛鬼怪似地攀着尸体冲到眼前时; 绝大多数都产生了手中的武器毫无作用的绝望想法。
他们甚至想把自己的手放到喷着火舌的机枪上试一试; 发射出来的子弹是高速的金属; 还是棉花甚或幻影 在那无数张肮脏、疯狂、兽性的脸中间; 有一张铁脸显得最平静、美观; 也因为没有任何激动与扭曲; 反而显得更加可怕。
一个抱着双筒机枪的俄军少尉吓得呆住; 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对这个从地狱里冒出来的魔鬼射击。
魔鬼的双手戴着薄薄的黑皮手套; 拧小鸡似地拧断了他的脖子。
李克明回老家来找老婆儿子。
他现在自由了。
通缉令已成被人遗忘的历史。
连他的铁面也引不起惊奇和恐惧。
人们全都陷于麻木和疯狂。
这种环境使他成了正常一员; 也使他从往昔的绝望中摆脱出来。
老婆儿子占据了他全部的思念。
但是昔日的家园已不存在。
一片烧焦的废墟; 满目断垣残壁。
自己的家只剩一角; 里面一个老头正在强奸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幼女。
无论妻子儿子还是父母都不知去向。
到处是人; 却没有一个熟悉的。
乡亲们、一起长大的童年朋友们、同学们、老师们、邻居们全都不见; 只有一张张、一排排、一片片陌生而遥远的面孔; 凝聚着饥饿与疯狂。
他身后跟上了七八个男人; 全拿着从俄军士兵手中夺来的枪。
没人说话; 只是紧紧跟着他。
也许由于他的铁面; 也许由于他杀死俄军少尉的功夫; 也许由于他身上那种让人慑服的气质; 反正他们认定了他就是头儿。
他开起一辆装满弹药的雪地运输车。
那些男人跟着上车。
他沿着江边往上开; 哪有俄军向过江的人群开火; 他就从背后消灭他们。
他已经有了一支队伍。
或者说; 一支队伍已经有了他。
那一夜; 从瑷珲到呼玛二百九十公里江段; 约有三千万人冲进了俄国。
黑河对岸的俄国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燃起了熊熊大火; 所有吃的穿的用的全被抢光。
沉溺于暴行的中国难民只占极少数; 多数人直奔北方的大山脉和大森林。
凌晨时分; 当俄军重新控制住边境时; 洪峰已经过去。
小股后赶到的人群重新聚集伺机过江。
被黎明青光微微照亮的江面上; 几十公里浮冰被江水摇动着碾磨尸体。
冰上水里全泛着黑红色。
上游没断裂的冰面整个被尸体铺满; 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