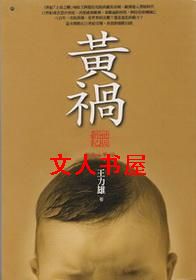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沉迪作了证,真相公诸于众,又将从另一面迫使我们讨伐北京。
但无论服从还是讨伐,现在都不是时候。
我们还需等待,静观形势发展,让北京耗损元气。
现在的结局恰到好处,给我们不服从的理由,同时逼我们讨伐的理由又不够充分。
随着形势发展,这个结局可以让它消也可以让它长,视我们的需要而定。”
白司令站起身,在地毯上走了几个来回。
他的腰杆像钢桩一样笔直,步伐也似在操练场上。
他在办公桌前转过身。
“解除各部队出击准备。
通知福州,在事情彻底弄清以前,我们将无限期中立。”他略停片刻。
“同时,参谋部组织秘密班子,制订进攻北京的作战方案。”May 26; 1998
郑州“有了它,至少能在最后那个没顶的关头,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得到一只拯救的手! 它简直是上帝之手啊。”
已经进郑州境内了,石戈让司机把车开出黄河新堤工地的简易土路,从正式公路进城。
可是前面的路又断了,一堆车堵在那,司机们骂不绝口。
从开封工地到这七十多公里,被刨断的路面不下二十处。
只好停车。
石戈走上新筑起的大堤。
表面看,施工质量很好,堤身光滑平整,斜面符合标准。
他抄起一把锹挖几下,浮土下面就露出用土块垒出的“蜂窝”。
大大小小的土块巧妙搭置,最大的“蜂窝”空隙能钻进去一个小孩。
一路上石戈已经多次发现这种“蜂窝”。
这是上冻以后新兴起的一种偷工方法,正在以极快的势头蔓延。
刨下同样土方的冻土块,能搭起多一倍的堤身,也就能领到多一倍的口粮。
现在土冻得还不深。
附近冻土刨完了,被汽车压实的土路面也可以刨成块充数。
一路那些无法通行之处基本都由于这个原因。
这种“蜂窝”堤现在看着高大雄伟,一化冻就会瘫成一堆烂泥。
俗话说“千里大堤溃于蚁穴”,何况“蜂窝”。
石戈已经懒得发火了。
他知道无论说什么也不能在周围那些木然的脸上得到反响。
民工们直愣愣地呆视他,穿著各种各样城里人为灾区捐赠的旧衣服。
其中不少是曾经流行一时又很快没法再穿的奇装异服,带着铁圈铜环亮闪闪的小玩艺﹑符号﹑外文,敞胸露腹,套在脏稀稀的农村式黑棉袄外面,再加上戴羽毛的女帽,凉盔,摩托帽,配在那些脸上,真显得又怪异又可怜。
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后,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把游荡在各地的大批流民强行集中到黄河工地上来。
黄河大水使根治黄河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多少年苦于工程浩大和资金人力不足,一拖再拖,在眼下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却不但大规模开工,而且采用了难度最大的根治方案──从郑州邙山到山东渤海,硬是从无到有挖出一条宽五百米﹑深三十米的新河道。
让黄河改道,脱离原来高出地面的老河道,重新变为地下河,并用挖掘新河道取出的土方在两岸筑起大堤。
新河道最大过洪量可达每秒五万立方米以上,能防两千年一遇的最大洪水,比旧河道过洪能力提高二十倍,算得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黄河危害。
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浩大工程,现在不但干起来,国家还不提供机械设备,全靠人挖肩挑。
这种故意退回到比修长城和挖运河还原始的技术状态出于一箭双雕的考虑──既省下了天文数字的投资,又提供了吸收大量流民的可能。
现在,从邙山到新选定的黄河入海口,至少有三千万以上的流民被固定在改道工地上。
筑起了黄河堤,也同时筑起一道控制流民洪水的堤,加上在全国实行通行证制──居民离开住地得经允许,发放证明,流民问题至少眼前已有所缓和。
但石戈清楚,这是靠大量军队和严厉镇压维持的。
工地上的流民几乎等于苦役犯。
给他们住的是简易帐篷,没有燃料,没有床铺。
一个强劳力苦干一天所得超不过一百五十克粮食,不用这种“蜂窝”方式偷工取巧连半饱也别想吃上。
可即使是维持现在这种低标准的粮食供应也已难以为继,来源全靠强制压低城市居民口粮标准和对非受灾农村地区强行征粮,这又激发了更多的新矛盾。
现在唯一还能维持稳定的手段就剩恐怖。
全国数千个有权实行就地枪决的军事法庭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
凡是有墙的地方几乎全贴着死刑布告。
黄河工地没有墙,也毫不吝惜地从奇缺的资源里拨出材料竖起一排排公告板。
每天都有新的枪决名单贴上去,一层又一层。
一个吆吆喝喝走过来的监工认出了石戈。
“没办法呀,副总理。”看到石戈脚下的蜂窝,他先向周围那些石板一样的脸扬扬手中的电棍,又无可奈何地辩解。
“我一个人管五千人,看见这头看不见那头。
这些人又懒又滑,你一转身他们就捣鬼。”
石戈不相信监工什么都不知道,他是装着没看见。
别看他拿着能连续击倒二十个大汉的新式电棍,挎着压满子弹的手枪,他心里虚着呢。
全工地已经有三十几名监工被杀,都是因为过于严酷。
千万张愚昧呆滞的脸组成一道攻不破的长城,每一张嘴似乎只会说“不知道”三个字。
然而藏在那城墙后面的却决不仅仅是愚昧呆滞,没有点心计﹑魄力和勇气是不会拋弃家园当流民的,流民生活又使他们见了世面,学到了种种混世手段。
他们再不是过去那种任人摆布的厚道农民。
他们中间有人贩子﹑走私者﹑贼﹑妓女﹑抢劫犯﹑赌徒﹑江湖骗子﹑哄抢者……工地军管司令部断言形形色色的黑社会已经在工地形成,却摸不出一点具体的轮廓。
呆滞只是掩盖着背后那些秘密的厚幕。
他们像黄河一样是条悬河,积蓄的能量全都以一种随时一泻千里的趋势指向外面。
眼下约束这条悬河的堤防是两岸三十个师布成的防线。
一旦决堤,他们就会铺天盖地席卷中国。
一条黄河已是中国的忧患,是悬在中国头上的剑,现在又出来一条新黄河,比古老的黄河更可怕,更让人毛骨悚然。
May 27; 1998
“返工。”石戈只说了两个字。
“是,是。”监工连连答应,立刻回身扬起电棍。
“马上返工,听见没有! ”
石戈知道这无济于事,别说他一走,返工就成了空话,就算真返工了,对于数千里大堤又顶什么用。
只有等开春以后,冻土自行塌陷,再全面重新夯实加土。
反正本意就是尽可能拖长时间固定这些流民,再返十次工也没关系。
现在被虚假的土方多骗去点粮,比起全国性的贪污舞弊,只是一点渣。
用黄河改道工程固定流民当初是石戈的构想。
十六号机关对此所做的研究一直是治黄决策的基本依据。
不同的在于石戈方案是用解散军队省下的资金吸引流民自觉参加治黄,现在则是以军队强行迫使流民无偿地治黄。
没有什么区别比这个区别更大了。
最高当局的决策过程根本没让石戈参加,却又在决策之后任命他担任黄河改道工程的总指挥。
表面看,这么大一个跨省工程,几千万人参与,涉及大量征地﹑迁移,一个副总理当总指挥有必要,先例也很多。
但以往都是挂名,只为增加权威性,具体工作都由下面做。
这次却不同,王锋以战时领导人身份向他宣布这项任命时特别指出: 他必须去施工现场指挥。
他那次在“绿展”亮相后,国外进行了广泛报道,加上流氓闹事,炸弹爆炸,一时被渲染得传奇一般。
有把他说成是“绿展”后台的,也有借此分析中共内部斗争的。
不止一家报纸非常肯定地断言,流氓和炸弹全出自军方控制的“意识形态指导委员会”。
国际绿色组织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条新闻又有足够的刺激性,一时石戈的名字广为传播,被描绘成有两名武林高手护卫左右的中共新开明派首领。
国内对这个事件一直保持沉默,对石戈也不采取任何动作。
这种方式很聪明,没有新材料补充,那些报纸电台也就难以为继,自觉没趣地收场了。
这时再让石戈去施工现场指挥,就是无声无息把他驱出北京,和三千万流民一起发配在黄河上。
石戈情愿这样。
上任副总理没几天,他就知道自己仅是个政治交易中被偶然夹上天平的砝码。
如果初始陆浩然还有加重这方天平的愿望,自己还能借重总书记名义起点类似保护“绿展”
之类的小作用,那么现在,陆浩然已经彻底撒手,什么都不管了,自己这个小小砝码对天平更是毫无意义,还不如到黄河上做一件实在事,至少对中国算个贡献。
监工命令正在修路的民工先把石戈的车抬过去。
被刨断的路面有好几百米。
民工们喊着号子把汽车举在肩上。
其它被堵车辆的司机全都惊讶谁能得到这种待遇。
石戈的车是辆不起眼的国产吉普车,又脏又破,满身磕碰痕迹。
石戈本人穿一身臃肿的工作服,鞋上沾满泥。
一个司机表示不满: “我先来的,怎么不给我抬?”监工回答: “撒泡尿照照你的脸。”
上了正式公路,石戈换下司机。
来到工地他才有功夫学开车,兴致正浓,同时也是为一个正在心里暗暗盘算的小诡计做准备。
驶出黄河工地要通过三道关卡。
第一道是民兵,第二道是武警,最后一道是由军队把守的铁丝网出口。
上千里黄河改道工地全被铁丝网包围,像口袋一样把几千万流民装在里面,只许进不许出。
铁丝网由荷枪实弹的军队看着。
一眼望去,沿着蜿蜒起伏的铁丝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望高台林立,巡逻车穿梭。
一队一队从四面八方押解来的流民正在继续被赶进铁丝网。
不管石戈如何厌恶暴政手段,他对眼前取得的明显效果都不能不承认。
流民迅速减少,社会秩序全面恢复,除了宣布自治的几个省,其它地方政权对北京百依百顺。
经济危机虽然照样严重,但北京借助强力恐怖从地方和民间获得的资金﹑资源比经济最繁荣时期还要多。
一方面进行着战争,大规模扩军,一方面又根治黄河。
仅仅保证每天供应维持工地流民生存的八百万公斤粮食这一点,就让石戈惊叹不已。
南方的叛乱看上去注定要被消灭。
若不是全国性军管牵制了一半以上的军力,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
对这场战争,石戈不知该持什么态度。
他不赞成任何种类的战争,尤其是同胞之间的残杀。
然而他也清楚,如果听任南方自治,整个中国就会分崩离析。
专制制度下权力是一种资源,分裂的单元越多,资源来源也就越多。
大一统一旦解体,人人都会宁做鸡头不做牛尾,到头来不会有局部的自治,而只会有整体的粉碎和死亡。
除了战争还有什么手段能制止这种结局呢?法西斯统治似乎成了唯一能救中国的出路。
但是,十六号机关很早就在研究结果中得出另外的结论: 中国一旦再有法西斯政权上台,就是社会将崩溃的开始,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崩溃之前,一定是法西斯政权上台。
法西斯是阻挡崩溃的最后手段,也是加速崩溃的催化剂。
May 28; 1998
铁丝网出口处的值班军官从通行证上认出这辆车是总指挥的,却不知该向谁敬礼。
坐在石戈旁边的司机和坐在后排的两个警卫都过于年轻,而石戈只像个不称职的司机,那么宽的出口,还差点碰倒标志牌。
石戈把车开上直通郑州市内的水泥公路。
如果恐怖能够无限地维持下去,也许崩溃就不会出现。
毕竟一千个乌合之众也不敢对抗一个手执武器的军人。
恐怖建立秩序,秩序挽救经济,经济稳定社会,这种先例不是没有。
中国在实行恐怖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几千年衣钵相传,举世无双,然而相克的因素在中国也同样达到极端。
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实行恐怖的成本就越高。
恐怖机器本身也随着大型化和复杂化更易发生内部故障。
后者往往会成为恐怖政治崩溃的最终原因。
此刻,中国军队已不是铁板一块。
广州军区的叛变实际是七省市联盟敢于宣告自治的支点。
虽然广州部队目前无法抵抗北军攻势,湖北湖南已被北军攻克,指日可进军广州。
但南京军区又突然将有限期中立变为无限期中立,这个变化更使北京不安。
四面环顾,亡国之兆俯拾皆是。
把一个正在坠落的瓷瓶缠上再粗的铁链,又怎么能避免最后那一下粉碎呢?这辆破吉普在工地上哪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