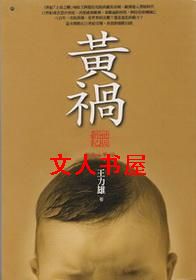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人民公社的解散失掉了最有效的治黄手段──人海战术。
村干部在暴雨中喊破了嗓子,农民们却只顾挖自己田地的排水沟,修自家房顶或盖自家柴垛。
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人懒懒散散,先争价钱,然后计较活的轻重,再想方设法偷懒。
城市更组织不起来,人们全在忙于各种游行集会。
以往抗洪有一支最强的力量──军队,这次却迟迟调不上来。
降雨面积不断扩大。
七月三十日下午,山东省东明县高村堤段突然开始坍塌。
三十多公尺宽的堤顶不到一分钟就只剩一层护堤石墙。
河务局的徐工程师声嘶力竭地喊: “快投石料! ”
他记得一九五八年,在花园口看到过同样险情。
当时上千名解放军战士抢着冲上去扔石块,一会儿就把缺口填住。
然而现在,他刚喊完,所有民工却四散逃命。
在他痛恨地跺脚时,轰然一声巨响,黄水像昂首的妖龙一样窜向正在低地逃散的人群。
徐工程师成了这妖龙吞噬的第一块点心。
他喊出最后的三个字是: “解放军……”
这条黄色的巨龙吞噬了一个个村庄,成千上万的性命,咬断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沪线。
无数耕地变为一片泽国。
东明﹑菏泽﹑定陶﹑成武﹑金乡﹑鱼台相继被淹。
工厂停工,学校停课。
大水接着淹及江苏﹑安徽。
七月三十一日,下游暴雨未停,三门峡水库上游又发生特大洪水。
本来水库已关闸蓄水,为下游抗洪减轻压力。
一天之间,水库满槽。
陕西的渭河﹑洛河,山西的汾河﹑涑水河泄洪不畅,全都开始泛滥。
河南也担心三门峡水库一旦被冲决或漫决,自己首当其冲。
三省联合向中央防汛指挥部施加压力: 山东已经被淹,多淹少淹只是程度问题,保未淹的地区不被淹更重要! 指挥部最终批准三门峡水库开闸泄洪。
五千秒立方米的泄洪流量加入到下游洪水中,使山东拼死拼活刚刚要完成的堵口又一次被冲决。
当夜,山东数名村民强渡黄河,在上游河南省长垣县石头庄堤段内,用九十公斤炸药炸开一条老串沟上的民□,使黄河主流改变方向,直扑河南省一侧堤段。
加上南风大作,推波助澜,八月一日凌晨,河南省一侧决口。
黄龙冲进河南境内,向北扑去。
长垣﹑滑县﹑濮阳被淹。
安阳被围。
河北省也告急。
山东方面则河水顿消,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了高村决口。
那几个强悍村民被当地百姓奉为英雄,披红挂彩。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眼光都盯在“增长型”项目上,防洪投资持续减少,加上黄河连续十几年枯水,人们已经习惯忘记这个“中国之忧患”。
大堤百孔千疮,獾﹑鼠繁殖。
几天下来,除了决口处,全线大堤出现几千处裂陷﹑管涌,四面告急。
八月二日,黄河支流伊河上游转成特大暴雨,八小时累计雨量四百五十二毫米。
千百条沟壑同时暴发山洪,冲垮陆浑水库。
一万七千秒立方米的巨大洪峰直扑黄河,使黄河总流量猛然涨至三万八千五百秒立方米,超过历史上所知的任何一次洪水。
京广线铁路大桥顿时被冲垮五孔。
洪峰一过郑州,便在南北两岸同时冲开二十八个口子。
大水南至徐州,蚌埠,北至德州﹑天津,只在史书上见过的“洪水横流,尸漂四野”又一次重现。
当石戈透过舷窗俯看变成泽国的华北平原时,绝望一重又一重压上心头。
视察水灾的专机上每个人都沉着脸,但也许只有他最清楚下面的情景意味着什么。
他的班子曾做过黄河水灾的预报分析。
那个分析里不包括目前狂躁的政治动荡,不包括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也没考虑升至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社会模块已在计算器荧屏上现出无数断裂,接近发散。
实际的水灾比理论上构造的大,除了要加上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脱□般的通货膨胀,还要加上那张轻飘飘的报纸。
昨天的《解放军报》用特号字印出“爱国主义是立军之本”的社论标题。
文中昂然提到: “卖国主义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也会被爱国主义的人民军队彻底粉碎”。
虽然没有点名,可昨天是总书记从日本凯旋归来的日子。
今日的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相继转载《解放军报》这篇社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却不予理睬。
一处高坡上,许多难民仰面向飞机招手。
坡顶用石头摆出“感谢恩人解放军”的大字。
他们以为飞机都是军队的。
在灾区最危难的时刻,军队终于开进灾区。
几十万解放军浩浩荡荡,给灾区送进粮食医药﹑设备物资,开展大规模的救死扶伤,抢救财物,维持治安,筑坝堵口。
灾区的百姓含泪感恩戴德,相比之下,就更加怨恨政府,怨恨那个刚从日本姗姗迟归的总书记。
北京西山他握住王峰的手使劲摇了几下,有一种蚍蜉撼树的感觉。
前导车通红的尾灯偶而在士兵之间的空隙中显露一下。
陆浩然又瘦又小,平时坐自己的车,从不许警卫坐到前面遮挡视线。
可在这辆装着隐蔽钢甲的军用车里,他被士兵的人墙紧紧围在中间。
每个士兵都紧握武器注视窗外。
王锋在电话里强调社会动荡,军队必须绝对保证自己客人的安全。
陆浩然很少与军队之间有直接联系。
下午秘书通报军委副秘书长王锋请求通话时他有点意外,尤其还是个通过保密机打来的的电话。
王锋只说“主席”想见他,说得很客气,但明确指定在今晚九点十五分,没有询问他是否有空或是否同意。
当然,他同意,而且为此取消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系列外事会见。
细节是两方秘书安排的。
见面要求绝对保密。
他坐秘书的车从侧门出了中南海。
在黑暗中靠到这辆等待已久的车旁。
两个车门同时打开,他只迈一步就换了车。
主席只当到军委第一副主席,四年前就退休了,一直住在西山养老,但如同在位的九年一样,他被军内始终不变地尊称为“主席”,即使是现任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也不能让这个称呼转移到自己头上,尤其在高级将领中。
总书记经营军队也有不少年了。
“六四”之后,谁都能看出未来只能靠枪了。
谁抓住军队,谁就抓住政权。
一方面军队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又要把军队变成党的驯服工具。
总书记在军内做了大量工作,也颇有成果。
军事院校出身的中层军官对他都有好感,他的意图也大都能畅通无阻地贯彻,然而不能由此认为他就掌握了军队,只能说军队暂时把“自己”退到幕后。
军队是最讲“自己”的,不会让一个外人进入核心,表面上一套法定的机制在周密运转,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一层外衣。
军队的心脏在西山。
陆浩然从公安部长处得知: 近来每天都有各大军区的军用飞机载着将军们在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他们直接被挂着军车牌照的“奔驰”牌轿车接到西山,呆上半天,又匆匆飞回。
各总部各兵种首长也纷纷到西山谒见。
中国最高级的轿车一时好象都集中到通往西山的僻静路上了。
他预感军队正在筹划重大行动。
解放军报的文章已表现出明确倾向。
他不加犹豫地来见主席,正是因为他现在需要军队,而王锋的电话说明,军队此刻也需要他。
刚登上国务院总理之位时,他即使不能压总书记一头,至少也旗鼓相当。
他长期主管国民经济,在国务院系统有雄厚基础和广泛关系,逐渐成为坚持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被几位元老看重,共同推举他出来治理八十年代改革留下的“市场后遗症”,同时也是给被国外称做“温和派”的总书记设下一个牵制。
那时“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尚能保持不同派系的平衡。
自从“老人家”去见马克思,对立和冲突就日益激化。
新的组合,新的阵线,新的交易,新的对比,每天都在纷纭变化。
他从攻势变成守势,现在则是步步后退,眼看退到悬崖边上了。
陆浩然总是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被人称为“强硬派”。
其实自己太软弱。
他虽然主张政治上严厉控制,但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发生矛盾的时候,做为一个搞经济出身的专家,却总是迁就经济的需要而做政治上的退让。
然而这二者似乎永远有矛盾,难道退无止境 有一个逻辑是谁也玩不明白的: 只有政治安定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政治才能安定。
这是多年的口号。
字面看上去二者相辅相成,为了政治和经济同时又安定又发展,他做了那么多迁就。
可终于回过味来,当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实际上互为悖论的时候,经济不发展政治不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治也不会安定,反之一样,政治安定经济不发展,政治不安定经济更不发展。
然而“温和”的总书记已经利用怕乱和怕失民心的心理,占领了太多的阵地。
现在他又要再玩一把火,企图用为“六四”翻案狠狠捞一把了。
这是危险的一着,却也是很高的一着。
陆浩然当然知道这位“温和”的总书记从不是个民主派,他冒这个险为的是他从中看到的可能收益: “六四”积淀的能量也许可以碫造成他手中的大棒,用来砸断“强硬派”的脊梁骨,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六四”造成的问题不在于死了人,损失了财产或弄坏了国际关系,那些没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从此失掉了一种心理结构的平衡。
不管表面怎样气壮如牛,执政集团多数人内心深处都暗暗发虚。
历史最终将怎样评说 “六四”之后的东欧变化更加深每人的疑问。
然而那时有老一辈在上面顶着,这种心理失衡还能撑住。
临到自己面对历史的时候,“强硬”的牌子就谁也不再愿意沾边。
一个个藏头缩尾,原来的心理颓势很快演变成行为上的虚弱。
总书记正是利用这一点。
为“六四”翻案是先天属于“温和派”的专利,不谈其中无穷大的政治资本,仅仅激发一下早已倾斜的社会心理,至少在“六四”问题上,人人就全都洗刷自己,唯恐摘不干净。
各级当权者拼命做出“温和”甚至“自由”的姿态,这种自下而上的连锁反应,怎能不使“强硬”派不战自败! 其实陆浩然和总书记一样,当时都未进入核心决策圈,对“六四”镇压并无直接责任。
然而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他必然要采取相反立场。
用中国官场一句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
“强硬派”是靠“六四”压倒“自由派”的。
就像当年一开枪,即使嘴上仍然喊改革,路线和班子都发生根本变化一样,如果“六四”翻了案,“强硬派”的路线﹑班子也就得完蛋,“温和派”就会把“强硬派”踩扁。
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立刻给陆浩然换了一辆最高级的“奔驰”轿车。
风景秀丽的玉泉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汽车在曲折的幽径中转了半天,停在一座古树掩映的别墅之前。
王锋已经等在门口。
“陆总理,主席本想亲自拜访您,不巧患了感冒,请原谅。”王锋的微笑非常动人,牙齿雪白。
“哪里,年轻的拜见年长的,这是天经地义……”陆浩然比主席年轻近三十岁,比王锋又年长近二十岁,他意识到在王锋面前说“年轻”二字不太合适。
“我早想来感谢解放军对灾区的支持了。”他握住王锋的手使劲摇了几下,有一种蚍蜉撼树的感觉。
王锋四十多岁,风华正茂,比他高一头,让他觉得像仰望一座挺拔山峰。
那张英俊瘦长的脸上总是一副自信表情,肩膀宽宽,昂首挺胸,尽管夏夜炎热,一身合体的毛料军服却扣得严严实实。
“我们该受批评,到晚了。”
“哪里能这么说,这不怪你们。”
比起以往救灾,这次军队赶到的时间确实晚了不少,然而声势却比哪次都大。
到处都是调动的军队,公路﹑铁路﹑满天飞机,军用物资滚滚如河。
半个中国都能从早到晚听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军歌声。
晚归晚,这次军队获得的赞誉却比哪次都多,也最热烈。
大部分灾区基层政府都已瘫痪甚至消失,全靠军队挑起了主要担子。
今天受灾严重的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天津,加上受到影响的陕西﹑山西﹑内蒙,分别在各省市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无限赞扬解放军慷慨无私的救援。
同时,陆浩然特别注意,那些文章全都以不同形式不点名地攻击了南方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