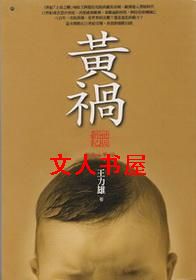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ƻ�-��2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ǿӲ�ɡ�·���Ѿ���ʼȫ��Ťת���º��ɡ���ȥ����Ϊ��
��������һ����������ը�Ե��¾��ߣ��ϳ������վ��ú�����Э�顱������ͣ����Ƿ�ձ�ծ��Ҫ����й�Ƿ�ձ���ծ�����й���ȥ�����ձ�ս�������ϵ��һ���ǣ�ȡ���������غ���ʡ���������ߣ��������ظ���Ԯ�ƺ������r�ط�����һ���Ͻɹ��ҩr���в�Ʒʵ�й����۩rũ��Ʒ�ָ�ͳ��ͳ���r���Ϻ���Դʵ������ơ���������߲�Ķ����У�ʯ�겻�����κ���ϵ������ʮ���Ż���Ҳһֱ�����м�ɫ�ʡ�
�Դ�ĸ↑�ţ��й�ʼ���ڶ�Ԫ״̬֮����
������������һ���ִ������֣����Ĺ�ģԶ���������������ã�Ȼ��ȴ����������ѹ�ȷ��ִ������ֲ����߽⣬���Է��������ij������������
�����ϣ����ɿ��ƺͼӽ����ƽ������������º��ɡ��͡�ǿӲ�ɡ��������£��������ݡ�
���ֶ�Ԫ���������ػ�Ϊ�ƻ��������ã�ʹ���ȱ���ȶ��������������ǽ�һ�������������롰һ�ž��ң�һͳ�����������Ѿ��ء�
��ʯ�꿴�������ֶ�Ԫ״̬���ת����Զ�Ҳ�����·�ġ�
ҪôһԪ����ҪôһԪ�ɣ�ҪôһԪ�ƻ����ã�ҪôһԪ�г����ã�ҪôһԪ����������ҪôһԪ�����Ż���ҪôһԪ�����ƣ�ҪôһԪ˽���ơ�
��϶����ŵ��ȥ����ȱ����м�ѡ����û�еģ�ֻ������������ȱ��֮��ɵĹ�̥��
�������ϣ�����������һԪ�ɣ�ֻ����һԪ����
������ά���������õĸ���ǰ������ģ����ԡ��º��ɡ������ܳ����ºͣ�Ҳ�����ܽ��ì�ܡ�
�����������շ�չ��Ȼ�ǵ������ⲽ��һԪ��������ȫ��ķ���˹ͳ�Ρ�
��֦���ſտڴ������ˡ�
ʯ�����õĹ���װ���ڴ���
�����˲���˵����˭�ø�ʲô���������
��֦�������úܽ�������ʱ������ͷ��ĥ�������ġ�
��ÿһ���������������������Ŀ������ſ����ƺ�ƫһ���ǶȾ��ܿ�������ʲô��
ʯ��̧���ۡ�
���ŵ��ݵ�ƽ�أ�Զ��������Ƭɽ�¡�
����������ï�ܵ���ݣ���ҷ���������Ũ�ܵ������ڵ�������
���ڣ������ݣ�һƬ���ơ�
ˮ����ʧʹ�����һƬ��������֣���������������ĸɿ����ߡ�
����������ǣ���֦��������һ�Ρ�
����δ��ɷ������������ڴ����̲ݵ��¿��ϣ����Ű���˫�ȡ�
��ֻ��ʮ���꣬ȴ�����ȿ���ڴ���������ס��ѣ�������ôֲڵ�С�����еؽ�����������һ��
Ϊ������Щ�ո�һ�յ�����֣�Ϊ��Щ����pɽ�º�����֮�������������л��֦��
ÿ�����������˴壬�����ഺ�����������ﵴ�������������ϴ�ѧʱ��֦������ϴ���Ӱ�ӣ���ͬ��Ȫˮ�ﲨ����
�������ߴΣ�ÿ�ι�֦���Ӽ�ʮ������żҸϻ�������һ�棬������������������������һ��һ��
���������ȥ����������������Զ���Ÿ�ʮ����Ĺ�֦��
�������April��12����1998
���ĸ����������ǣ�������������������֦��ȶ���溰��
�����������߳�����
���ҿ����ʯ���ɶ����������ǽ��ˡ���
����ɶ����˺��Ĺ��죡����
�����������㣬ʯ����Ǵ�ɲ��ˣ��������ֵġ�����
�����������Ǹ�Ĩ�������С�ӣ������ָ���׳�������ں��硣
�ϸ�������ͷ����������ɲ�������ȣ��ְ�ǰ��ץ�˵��ع����־������˸������������پ�ѡ�����˴峤��
����һ��������������峤�������ࡣ
�����㰡�����ǵ�ץ�����Ͽ����ʳ��⡣
��������Ѱ��ﱤ���ˣ���Ժ�ϵ���ʳһ�Ų�ʣ��
����Ҳ�÷����š�
��˵�أ�ʯ�硡��
������������ʯ���ʡ�
���٣�Ҳ˵�������ĵģ���������������ˣ���ʵ������ûɶ������
�����Ķ��У�����һ���˾�����
�����˶࣬˭������Ҳû�С�
�У�����ץ�����һ���ȥ�����������¡���
�������ˡ�
Ϊ�˷�ֹ�������٣���Χ���������ϳ����˱����ţ��ɸ�����׳������ɣ��ĸ���������ͻ���֧�֡�
��Щ���������¯���˲��ٴ�ì��
���˲�֪�������������өp��ҩǹҲ�ҳ�����
������ʳ�ں��л��˼�֧�˰�ʽ��ǹ�����������Ͼ�Ҵ��һ֧��
�����������ڲ����˴�ί��չ����ķ��ڻ�����
��˶�ķ��ɴ�ʩͬʱ��������˵Ҳ���а������ϵ���ʱ�䣬ֻ�о�ί���װ��������������
��Ȼ����Ϊֹ��ͷ¶���ȫ����ְ��������ʯ��ȴʱʱ�ܸо����ӵľ���Ӱվ�ں��档
û�����������������ĸı��Dz����ܵġ�
Ȩ�����й���Ἰǧ������άϵͳ�εĺ��ġ�
ɥʧȨ������ɥʧͳ�ε�������
���ֹ��Ͻṹ���ִ����������˲��ɽ�������⣺Ȩ��Խǿ����ἡ���Խ����������Ҳ��Խ˥����
�ִ������Ǹ��������磬���ο��Կ�Ȩ���ȶ�������ȴֻ�ܱ�Ȩ����ɱ��
�������ʹ���������ƽ������Ӣ����ʹȨ�������иĸ�ĸ�ı���ȴ������Ȩ���������ͷŻ������̼����á�
���峯͢�ĸĸ�ȸ������ĸĸ��һ�黹�࣬ȴ��������̨��ԭ��
�Ǵ�Ȩ����ɥʧ����������ʮ�������ݩp�����ս��
���Ž���ʯ�pë��һ���Ӣ�źͼ��ۣ����ϼ�ǧ����������ʹȨ���ؽ���
���ٴ�ͳ�εĽǶ��������������Ķ������������ѱ�סȨ�������˷�չ����֮�¡�
�����dz����Դ��dz���ð���v���߶��������ϲ��w��Ȩ���ڡ��ĸ↑�š�
֮���������������������ǰ��С��
��ʱֻ����Ȩ�ı�������������Ȩ����ÿ���������ṹ�е�ɥʧ��
ǰ�߳��˸�ë���ֿ����ؽ�����һ�ĵ���Ͱ��ɽ������ǧ��������͵Ķ�Ȩ������Ȼ�������ȥ�ף�һ��ɥʧ���Ǹ�ˮ���ա�
��ʱ����������Ȩ��������ǹ������û�б�ġ�
����ǹ���ӵľ��Ӿͳ���Ψһ��Ȩ����
����δ���ɹ��Ļ���������ȷʵ��ʹ�й����ά�ֵ�ʱ�䳤һЩ��
Ȼ�����й�������ƿ���ħ����
�ĸ↑�����й��������IJ��ɿ��������Ѿ�̫���ˣ�����̫���ˡ�
�������������ɽ���Ʋ��ɵ��غ���ȥ��
�赲������Խ��������Խǿ�������Ʊع�ͬ���顣
������赲������ȴ�����������¡�
�����Ѿ��ڽ����ө������������ǽ�����һԪ�Ƕ�Ԫ���������һ��Ҫ������
�Ǹ�����ġ�Խ��Խ���ˡ�
��Щ�꣬��ʱ���о�������
��ʼֻ�����������������Ҳ��ˣ�����Խ��ԽƵ����
�����Σ����������û�߲����Ρ�
���ţ������ڱƽ�������̫���ſ������š�
��һ��һ����������Ϣ��ȴ�ض�ɽҡ��
���������ĺ������һ����
�����ε��۾������ɽ�������汼����������������ȫ����Ѫ���ڡ�
��ʯ�磬����֦ҡ����һ�ѡ�
����զ�ˡ���
��ûʲô��������ġ���ʧ�ˡ�
��ׯ�����Ŵ��̡�
����ȥ�ɣ��ó��η��ˡ���
�����ٸɻ����
�����˺���һ������
���ҿɱ�������������ˡ���
ʯ�꿴��֦һ�ۡ�
ƽʱ��δ������˵���ֻ�������ʱ�ȵ���С���ӣ����ڿ���һ���ٽ�Ҳ�����ߵø���һ����
��֦���۾�һ�Ӵ�������������һ�¡�
������Ļ����ܰ����ջ���
��Ҫ������ӣ���֦�ֲ��á�
������ҷ��ŵ���С�����������������
��ֻ��Ӳ��������
��������һ���в���Ա���ȫ���Եľܾ����۹����������ۡ�
���Ŀ����������ɣ���ʳ�Ϳ����p����һ������ȫ�������������������ġ�
������ռ�����ةp������ʳ�����ֹ���ͬ��
���ַֹ�����������Ȩ��������ֻ�ܴ�������
�����κ�һ�������߶�û�оܾ������ȫ���Ա������ʳ��Ȩ����ֻ���ṩ��ʳ������
������ɹ�ȵĹ������ʵ�ѹ�ڼ��ϣ���֦Цӯӯ������һ�ԡ�
�����ճɻ��㲻����
ÿ��ũ�����������㣬�����ܶ��һЩ��ʳ��
��Щ������Ǹ�գ�������Ļ̡̻�
�ƺ�ˮ��������ǧ��ĵĴ���ȴ������ˡ�
ũ���Ϊ������ȫ����С�Ķ��ӣ�Ҳ�������۷��ǵ���ͷԽ��Խǿ��
��ʳ߬���Լ�����ʱ��Խ������Ǯ�ͽ�Խ�ࡣ
�ڴ�ͳ����ʮ��֮�����ϵ������ս���Ƥ���������ٵ���Դ����һ�����ݼ������ϲ㡣
���ڡ��������ĵײ���ʶ��ƶ����֤��������ʹ�����������Դ�Ĺ�ϵ���Ա����൱�ȶ���ƽ���״̬��
���������������ȫ��ƽ�ȵ���ʶ���ĸ↑���ְ���������ƽ��ƶ���������Ʒ����ƽ�ȱ�������ÿ�˶���Դ�������ʱҪ����һ����ı�����
��ʮ��ũ��ȫ���Ը���Ͷ�����ⳡ��ȡ�ı�����ʱ���й�����Դ��ϵ�Ͳ��ɱ����������ɥ�ӡ�
��Ȼ�Ѿ��뿪��ע�������������λ�ã����뵽���ʯ�����ﻹ��˵�����ij��ء�
�������ó��η��ˡ���·����կǽ�����ǣ���֦����������
��֦������ָ��ʩ����
�����÷��ٽ��ҡ�������ͷҲû�ء�
��ȥΪ�˷����ˣ����˴��й�һ���ָ��ֺ����կǽ��
��������Ȩ�Ժ�ʮ��û�����ˣ�կǽҲ���ò�ࡣ
���ڣ�Ϊ�˷����������٣�����������ɹ�̯Ǯ���ذ�կǽ��������
��ȹ�ȥ����ˡ�
����Ҷ��ᵽ��կǽ���档
��֦����Զ��������·��
��կǽ�ã����Ҷ�Ҫ���կ�ӣ������Ȱ���η�ͷ���ȥ��
��·�Ͽտյ�����
�����ΰ�Խ��Խ�ң�����û�иҵ����ܳ�;��˾����
Զ��ɽ���ϣ�һ�ӿ��������ģ��һ���ӹ�·��ͷ�����ʻ��������ϸС���̳���
˾��������׳����
��·��Ҫôû����Ҫôһ�����Ǽ�ʮ���������ϰ�����
��֦��ʯ��ѹȴ����£�ת�������ϲֿ��š�
�ַ���ں����ģ�ֻ��ͨ�������һ�����⣬���ڻƳγε������ϡ�
��ʯ�磬�ҿ������ˡ�����֦��ס�����������������ϡ�
��֦��ͷ�����������ںڣ�ɢ��������ɲݵ�������
�ֲڵ��ָ�����һ���̼��������Ƶ������������������ط��䡣
������������������һ����
��֦�Ѿ�������ʮ��ǰ�Ǹ�Ұ��һ����С�������һ��������λ�������ڻ����ɷ��ũ�帾Ů��
�����������ϣ������Ǿƺȶ��ˣ���֦�����������ڻ�������
�����ĵ�һ�죬���Ϳ�����֦�ڵ��ţ��ӻ��ֱ�ɹ¿࣬���͵͵������ֱ����ҹ��ץס�����֣����Ŵ����������ߣ����Һ��㣬�Һ��㡭����
��֦��ʵ��˫������ź���İ����ڸմ�������ɢ��������
���ĸ���ƽ��������û�г���Ů�˵�֬�����⡣
��δ����ʹ���������ɷ�������ʹ����������ũ�帾Ů������˥��
�ڰ��IJַ�����Ƶ����ף����ȵĹȴ��������ڹ�֦�鷿�ϵ��������⣬��һ�ж����������p��ˮ�ʹ����յĴ���ʹʯ�������
�Dz��Ǹ���Զ��������������롣
һ��ңԶ�ĺ������ƻ�������һƬŭ����ļ����У���ô��ϸ������ô����������ײ�Ʈ����������������ꡣ
����������̱���������м䴭Ϣ��ʱ�����������ںܽ��ĵط�ͣ�¡�
һ�����˴ӿ��������µġ����ˡ��������������ϡ�
���촩�·��������������Թ�֦˵��
�����磡�����磡�������溰������
�˺ܶࡣ
�Ų����߽���
������û�ˡ���һ������˵��
���Ȳ֡�����һ���������
��֦�ƿ��ַ����š�
������Ҫ��ɶ����
������ʮ������������p����ȫ���Ĺ��ˣ�ÿ�˶�����ǹ��
��ʽ�ķ����ӵ�����ӡ�š��������ʦ��������
����һ����һ��ʻ�����ֱ�ͣ�ڲ�ͬ��ũ���ſڣ����³�Ⱥ����װ���ˡ�
����ɩ��������ͷ����ͷͷ˵���ղ�����Ȳֵľ�������
���������������ġ���
�����ǵ�������������֦�����ӵ�ס�ַ��ſڡ�
����ͷ��֪����Ѵ���Ҳû�ã���̾������
������֪�����Dz�������������һ������
���Dz��������dzԿ��ġ���
������һ��ͷ��
����������������
���Բ����ˣ���ɩ��������һ�¼����֦�����Ӳַ��ſ�������
April��13����1998
���Ҳ�������ѽ��������֦�������ҵţ����������������У���ץס����С����
�����������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