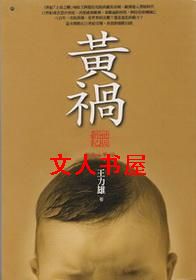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掏大粪》登性照片,“民阵”
刊物则把“人阵”领导人当年被捕后写的“认罪书”和口供全文刊载,公布由于他们的出卖而受牵连者的名单。
楼门大厅的喧嚣突然升高,听上去殴打尖叫和哭诉混成一团。
一个在“六四”之后向戒严部队做过举报的居民委员会主任被群众游街送到这里。
当年被举报的人早已处决,埋在亲人心中的深仇大恨却一点不被时间磨损。
哭诉的妻子要把奸细的舌头拔掉。
奸细的女儿跪着向群众求饶。
有人在鼓动拿奸细抵命。
这种场面近来随处可见。
今天下午的“情况通报”统计上来的被群众私刑处死的人已达十三名。
虽然看不见,石戈却能清楚地想见门厅中每一个情景。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
在一片仇恨的叫嚣中,那个声音温和但是坚定地说服群众,阻止他们的疯狂,保护奸细不被伤害。
他想象那女人应该很美,至少使多数男人有好感,因为她能让他们冷静下来,最终听从了她。
“这些人怎么了 ”那女人走到身后。
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石戈感到这声音有点熟悉。
一缕清淡的香味混在雷雨中飘来,挺好闻。
“都是群众扭送来的,还没来得及审查。”听上去陪同者对她十分尊重。
“你们是不是准备自立法庭 ”
“……我们不好打击群众积极性。”
“我以为不应当是群众带着你们,而是你们引导群众。”
陪同者没回答。
“至少别让他们用这种姿势。
……这个人怎么全身是血 ”
石戈被允许站起来。
蹲得太久,脚麻得站不住,女人伸出手扶他。
她果然很美,不是那种无可挑剔因而会显得骄横的美,却更能吸引人的目光,让人内心自然流出温柔的感应,如同她的美属于每个人。
她也许超过三十岁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
长发微微弯曲垂在胸前,一双大眼睛有点朦胧和忧郁,看不出化妆的痕迹,也没有装饰品。
淡绿色的丝绸衬衫下摆系在腰间,裤子是墨绿的,朴素,恬淡,唯一给人压迫感的是她有点高。
他瞄了一眼她的鞋跟,很平。
他觉得不仅声音熟悉,样子似惚也见过。
她也仔细端详石戈: “如果您不是在这,不是身上有这么多血,我会把您认成另外一个叫石戈的人。”
“叫石戈的不是另外一个人,身上有血而且正好就在这。”
“我叫陈盼。”
石戈没想起来。
“我在沧州找过您,为欧阳中华被捕的事。”
欧阳中华的女秘书! 她那时罩在核防护服里,大半个脸挡着防毒面具。
他当时没兴趣注意她。
公安部门介绍她除了当秘书还兼任欧阳中华的情人。
他从来讨厌这种混合角色。
但他答应了她的请求,说服公安部门释放了欧阳中华。
不管怎么样,核电站事故造成了巨大损害,领导当地居民示威不能算犯罪。
欧阳中华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写过好几本轰动全国的书,又是中国绿色拯救协会的主要领导人。
“六四”以后的政治严控时期,这个表面上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组织成了国内唯一能与政府发出不同声音的来源。
他们总是曲踞在不让政府撕破脸皮的边缘,从而保持生存并逐步有了全国性影响,受到国际瞩目。
前年的全球绿色和平奖就被授予欧阳中华。
绿色拯救协会在最近的政治大潮中只扮演了一个温和角色。
除了宣布支持为“六四”事件平反以外,没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举动,毫不介意风头被后起者抢尽,只在两个阵线冲突愈演愈烈时才出面充当了调和者。
“绿协”的威望受到各方面尊重。
刚才石戈就听见满楼人欢呼欧阳中华到来。
“我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上看到,”石戈对陈盼说。
“你从公安局把欧阳中华接出去时,他对欠了我这种人的情很不乐意,当场说过他会按同样方式还账,现在正是机会。”
陈盼笑了。
“他一定很乐意。”
陈盼离开不久,便有人把石戈带进三楼会议室。
石戈马上断定坐在邢拓宇旁边的就是欧阳中华。
一见面就能理解为什么传闻这个人拥有大批女性崇拜者。
他有芭蕾舞王子那种脸型,既有艺术家的潇洒,又有极其冷静坚毅的气质,三十五﹑六的年龄,精心的保养和锻炼使修长身材仍保持少年一般舒展匀称,配上质地高级的进口服装,把身边人全衬得黯然失色。
在场的男人只有邢拓宇跟他还算旗鼓相当。
虽然这位“人阵”的一号人物个不高,一脸伤疤,头发乱蓬蓬,看上去比欧阳中华老得多,却全身放射一种力量,让人感到燃烧的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个能压倒一切的男子汉。
他在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是工人纠察队队长,被捕后受尽折磨,然而始终坚贞不屈。
“民阵”宣扬“人阵”领导人在狱中叛卖,唯独找不到他的污点。
这使得“人阵”把他从较后名次推为一号人物,并大力宣传他,使他成为群众中有口皆碑的英雄。
邢拓宇盯着石戈。
屋里人也全都一言不发,象看一个怪物。
没人让他坐,使他有面对法庭的感觉。
他很累,两条腿感到身体重极了,身上脸上都有抢救时沾的血迹,衣服皱巴巴,一副惨兮兮的模样。
“我可以走了吗 ”他问。
邢拓宇仍是半天没说话。
“可以,”他终于开口。
“我正想见一见你是什么模样,没想到你能自己送上门来。”
“不是我自己……”
“行啦,我已经看够你了。”邢拓宇打断石戈有气无力的声音。
“放你走以前,有两句话。
第一句,刚才那根钢丝砍掉了十六个民主战士的头,而‘百字宪法社’是要砍掉整个民主运动的头,我相信你跟钢丝没关系,但你是‘百字宪法社’的幕后操纵者,你能否认这一点吗 ”
石戈没做声。
他知道否认也没有用,没有确凿的消息来源,邢拓宇是不会凭空向他提出这种问题的。
在形形色色各竖一旗的民间政治组织中,“百字宪法社”被所有组织视为共同敌人。
连“人阵”“民阵”这样激烈对立的派系,对“百字宪法社”的态度也完全一致。
这个组织专门攻击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
它从不上街,全部宣传都通过印刷品。
成吨成吨的小册子和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小报,散发到每一个角落,影响极广。
与以往官方反对民主的宣传不一样,它的观点既有理论水平,又生动引人,有说服力,紧紧抓住一般群众求安定怕动乱的心理,所以尽管不见其面,这个组织却争取到相当数量的群众,使他们远离轰轰烈烈的运动。
许多人想查清它的内幕。
它不搞募捐,无人赞助,却能进行这样大量的印刷和成本高昂的传播。
它的办公处狭小冷清,门可罗雀,只有几个守口如瓶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却能进行如此有效的组织和运转。
它的理论文章出笼速度跟印刷机那么快,不经长时间的推敲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质量,说明它肯定早就在做准备,而且班子规模必定很大。
这个“百字宪法社”宣称: 在适当时候,它将公布一个只由一百字构成的宪法,依据这一百个字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社会。
它不断渲染所谓的“百字宪法”,又不公布内容,不少人因此产生兴趣和期待。
“百字宪法社”
自己解释只有先通过对民主制的批判让人们丢掉幻想,放弃对民主制的盲目追求,才到适于公布“百字宪法”的时机。
但民主阵营一致认为这只是幌子,一味攻击民主过于赤裸,它有必要打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旗号,真正目的只在于为破坏民主运动做挡箭牌。
不少人认为它是当局的特务组织。
难怪屋里的人们都要用那种眼光看石戈。
“第二句,转告你的主子,他那一套在开明旗号下搞的诡计我们全清楚。
你们当年派女特务在国外勾引流亡者,现在把那时偷拍下的照片捅给人阵,同时又把人阵领导人当年在狱中的口供提供给民阵刊物,让我们互相搞臭,让人民厌恶我们,而你们坐等渔利。
今晚的钢丝事件也肯定是你们制造的,你们的特务此时正在到处散布谣言,企图挑起两派的武斗,给你们镇压的借口……”
石戈仍然没说话,但他的心里知道邢拓宇说得不假。
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任何一件,也不确切地知道什么,然而对他来讲,这种小伎俩无论遮掩得怎样巧妙,都是一眼就能看透的。
“……告诉你的主子,你们不会得逞! 这笔债记在你们头上,血债要用血来还,还帐的日子马上就到! ”邢拓宇是个受过太多折磨的人,又刚刚被街上那满地人头所刺激,眼光里充满仇恨。
“现在,你可以滚了! ”
欧阳中华不引人注意地对石戈晃了一下食指,像是表明了账了。
“还我出入证。”石戈说。
邢拓宇愣了一下。
“你倒是忘不了你的狗牌儿! ”
“如果我带不回这个牌儿,中央警卫局会搜遍这栋楼。”他的口气很温和。
“威胁吗 ”
“不是。”
邢拓宇轻蔑地盯他一会儿,挥了一下手。
“给他找! ”
尽管邢拓宇是个极端激烈的人,石戈在他面前并不为安全担心。
即使没有欧阳中华的“还账”,自己也不会遭扣留。
身为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哪怕稍有一点理性,也会知道扣留政府官员会惹来什么麻烦,那和扣留一个无声无息的老百姓完全不一样。
但他往外走的时候,面对的却是激愤而全然不考虑后果的普通民阵成员。
在楼梯上他还只受到推搡,这么一会儿似乎全楼都知道了他是“百字宪法社”的“黑后台”。
在二楼,一个嘴喷酒气的女人连抓带挠地剪掉了他一大块头发。
这形像可怎么站在总书记访问日本的随员行列里 从二楼到一楼他几乎是沿着楼梯滚下来的,只觉得上下左右全是拳头和脚,他护住要害部位,挺住身子不让自己倒下去,免得被人群踩扁。
然而拳头和脚停住了,陈盼站在他面前。
她头发乱了,衣服皱了,胸脯上下起伏。
他对着门上玻璃看看自己,嘴角破裂,鼻血流淌,右半个脑袋露出头皮。
给他剪头的女人说奸细就要剃“阴阳头”他用手梳理一下左半边头发,好象刚从理发馆的椅子上站起来。
从玻璃中,他看到陈盼在背后注视他。
灯光下,她被撕开的领口里皮肤雪白,跟门外的黑夜对比,不知为何让人难忘。
他没回头,径直走出“人阵”总部,没入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之中。
March 23; 1998
东京银座区
若想做一件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事,最好还是避开系统,系统永远可能出现漏洞。
这次是他第七次来这里了。
再来七次,他可能也弄不清这座地下迷宫的结构。
到处都有暗道,密门,夹层。
走在里面,只记得无数个拐弯和上上下下的小巧电梯,与上头地面那个震耳欲聋,灯红酒绿的世界相比,安静得有点让人不自在。
这次穿和服的老板亲自为他引路,仅仅是因为他每次来都不啬金钱,还是因为今晚那个“少校”终将露面 沉迪的护照是新加坡的,腋下的手枪是德国的,可他的感觉却是道地中国式的。
在那张肥肉成迭的笑脸上,他第一眼就感到老板今夜已把他当成了同路人。
“请。”在最后一条暗道尽头,老板伸出胖嘟嘟的短手,尽最大可能弯了弯球一样的腰。
一扇难以发现的门无声敞开。
一个日本姑娘跪在门口向他行礼。
姑娘身姿温顺谦恭,像个典型的日本传统女人,下身却光光的一丝不挂。
柔弱的双腿在幽暗光线下如粉脂一般细腻光滑。
这个房间沉迪以前从没进过。
很大,几乎可以在里面追逐。
矮矮的顶。
整个房间没有直角,全被软材料包着。
连冰箱﹑电视一类的设备也都改装成软表面。
进屋就像钻进一个大被窝。
加上那张能供五﹑六个人打滚的大床和满墙日本春宫画,散发出一种淫荡气息。
老板拍一下巴掌。
一个高个西方姑娘托着酒盘进来。
她只穿一件紧包臀部的黑皮短裤和一双长筒黑皮靴。
一对圆滚滚的乳房在齐胸的金发中甩动。
她向沉迪挤挤眼睛,一甩头把波动的金发撩到背后。
沉迪的模样讨人喜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皮肤滋润,穿著讲究。
一个四十出头功成业就的东南亚富佬,对女人可是一棵哗哗做响的摇钱树。
然而,沉迪对那对乳房和那双粉腿只说一句: “这里不需要人。”
老板按下一个开关。
对面一道帷幕徐徐移开,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