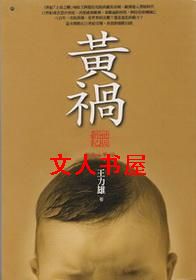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校”看得很快,再复杂的保安措施他都一目了然。
暗杀专家必然是保安专家。
他在这方面已经一通百通。
何况他刚刚在香港的图书馆坐了十好几天,所有的背景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他常做出眼神不济的老态,把放大镜举在眼前。
放大镜手柄中的照像机就无声地闪动快门。
虽然还会对底片进行深入研究,总的情况已在他脑里清晰地展现。
用他的眼光看,中国的保卫措施没有一处称得上高明,然而却最难下手。
他精心研究过近代历史中所有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除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几乎全是在公众场合进行的。
必须见到对像,然后才能瞄准。
西方领袖为了获得选票,不能不在在公众场合频繁露面。
为了那个美丽的民主程序,他们的日程甚至得公开,几点几分在哪做什么活动,经过哪条大街,参加哪个集会。
那么,即使他们的保卫工作再优秀,又如何能在那么多窗子中找出哪一个藏有枪口呢 中国领导人却不同,他们的一切都与社会隔绝──住在隔绝的大院里,坐着隔绝的汽车,开着隔绝的会议,进行着隔绝的旅行。
连他们的公开也是隔绝。
如果他们需要“和群众在一起”,他们会隔绝地出现在群众中,然后再不隔绝地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
隔绝是保卫工作最好的武器。
再平庸的保卫有了它,也近乎于万无一失。
在银座的那家妓院里,他开价五百万美元。
假如可以趁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下手,他只要三百万。
哪下手都比在中国方便。
“我给你六百万。”那个中共上校回答,一根眉毛都不动。
“但是必须在中国,必须在四十五天内,必须死。”
昨天晚上,他在香港第一次给上校留下的号码打电话。
按照约定,他要求知道旅行社的安排。
对方念了一份冗长的日程表,很精细。
当他按照上校交待的规则做了一番复杂整理,便出来一份中共总书记在未来一个月的活动安排。
现在,“中校”在脑子里把那安排反复过来过去。
中南海他肯定不想进,那里的兵几乎人挨人。
在北京伏击车队也不可能。
中共首脑在保护自己方面不惜重金。
防弹车的保险系数相当高,炸翻几个跟头也伤不着里面的人。
专列车厢也是如此,即使把它从桥上炸进河底,它也能八小时内不渗水,有氧气,与外面保持联络……不要说这些方法几乎毫无希望,哪怕有一半的成功可能他也不会用。
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中共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从未遭受过任何暗杀,警惕性长期受不到刺激就会麻痹,而这种麻痹是可能成功的唯一保障。
一旦打草惊蛇,得手的希望就趋于零。
所以不干则已,要干必成。
他把那些北京的活动一股脑甩掉,安排中只剩下将在月底开始的外出视察。
只要乌龟走起来,总比趴在窝里露头的机会多。
视察范围主要是黄泛区: 开封﹑兰考﹑徐州……黄泛区以外只去一个三峡水库,为刚刚完工的第一期大坝工程剪彩。
视察灾区必然要看望灾民。
从昨天起,“中校”一直在这点上动脑筋,但始终没有突破。
看完眼前这些材料,更觉得难以把握。
第一,他不可能准确知道总书记具体会在开封﹑兰考﹑徐州那些笼统地名中的哪个县,哪个区,哪个乡,哪个村。
那些安排都是临时确定的。
设在北京的电话即使能知道,那时他身在灾区,上哪儿打长途电话 这类事看着是细节,却是关键,可行与否全取决于这种细节。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和群众见面”都是在被封锁的场合,能接近的人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这种名义上的“公众场合”等于是中南海后院的延伸。
在无法事先制定出精细方案和安排好退路的条件下,他是不会拔枪的。
他做的是生意,生意的第一原则是保本,尤其这种本一丢了可就再也回不来。
就是为了保这个本,他要求中共上校说出他的老板姓名。
“没有这么一个名字,我怎么相信你们会履行刚才达成的协议──保证我活着离开中国呢 公布一个没有老板名字的录像不会形成任何威慑。
有几个人认识你,上校 ”
那一阵儿看上去生意马上就会吹。
“中校”要的名字必须货真价实。
欺骗没有用,他对中国的情况并不陌生。
上校激烈反对,不过争执时间一长就看出那反对更像是卖关子。
火候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上校收起反对,悠悠然开口。
“如果你得到名字,付在你名下的酬金就不该是六百万,”他打暗号似的挤了一下右眼。
“而该是八百万。”
上校把五百万说成六百万的时候,“中校”开始喜欢他,他把六百万说成八百万,“中校”就开始佩服他了。
不愧比自己军阶高一级。
“我会给你一个账号。”上校说。
“你把多出来的二百万转过去。
用句中国话说,那只是‘借花献佛’。
你将得到的名字值一个中国。
有了这个名字,你就会像被装进保险箱那么安全。”
上校的眼光亲切坦然。
钱是老板的,账号却自然是他的。
“中校”敢肯定那账号名下已经有了不止一个两个二百万。
“我一个人独吞八百万不更好吗 ”“中校”笑嘻嘻,当然是开玩笑。
不用上校暗示,他就知道对方也留下了威慑自己的“王牌”。
对这样一个人,宁可把他当成同谋,别把他当成对手。
那名字只有两个字: 一百万元是个“王”,一百万元是个“锋”。
中共总书记的视察路线在“中校”脑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流动。
怎么流动也不对劲儿,越流动越找不到契机。
他终于断定,应当反过来──“守株待兔”。
“中校”很喜欢这个中国成语。
兔子到处跑,它必然要撞上的“株”在哪呢 ……突然,“中校”把全部灾区也甩掉了。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一道白色的坝。
三峡! 白色的坝照亮了他的脑海。
“小姐,长江三峡的,大坝的,资料,有没有 ”他用生硬的汉语问女管理员。
女管理员在计算器上查找一番。
“对不起,这类工程问题的资料我们这里收得不多。”
“小野中二”刺耳地笑了一声。
“工程问题 台湾军队错了的认识,有战争,大坝十个氢弹的是。”
一个正在查找目录的台湾军官抬起头。
“先生对三峡工程有兴趣,可以去加拿大。
加国为了拿到这项工程,做了多年研究。
这方面的材料称得上世界之冠。”
“谢谢。”“小野中二”欠身致意。
“同时请先生知道,没有日本防卫厅指教,台湾军队也明白大坝对战争的作用。
至少本人就刚在加拿大研究完这个问题。”
“对不起。”“小野中二”露出肃然起敬的神情,立正鞠躬。
一小时四十三分之后,“中校”乘坐的飞机在桃源国际机场起飞,飞往加拿大。
“小野中二”
又变成了年轻快活的菲律宾旅游者。
March 30; 1998
闽粤沿海交界这次“风灾”必须有广东的联手。
台风过后天气总是晴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晒得到处冒油。
十七号,十八号,十九号三场台风几乎没有间隙,连在一块儿刮。
连续二十多天风雨交加,久别重现的太阳把人眼晃得生疼。
秘书在身后举着特制的大伞。
黄士可很想把正在一旁速记的百灵拉进伞下,和自己挨在一起。
她娇嫩的脸上渗出的香汗让他怜惜。
他生平很少有这种想把另外一个人捧在手心里护起来的冲动。
可是当着众多记者﹑随从和地方官,他昂着头发花白的硕大头颅,装出眼睛都不往姑娘那转一下。
灾情是严重的,这是他对记者们谈话的核心。
做为福建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赴灾区视察慰问团的团长,他对巨大损失表现出无比痛心。
数十名记者乘坐省里提供的专车跟随他从福州一路深入到这个地处省界的西坑镇,台风造成的破坏有目共睹。
他希望记者们如实向全国报道,宣传福建人民抗风救灾的英雄事迹。
“……我们福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灾区,夺回损失,不给国家增加任何负担,不向兄弟省市伸手。
这不是希图自力更生的名义,我们十分需要帮助。
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困难,遭受黄河水灾的兄弟省市也需要帮助。
福建自力更生是福建对国家和受灾省市所能做的最大支持。
请记者朋友们多为福建做做解释。
黄河决口时,我们正被十七号台风搞得很紧张。
十八号台风紧跟着登陆,造成大伙看到的这场大灾害。
随之而来的十九号台风又继续扩大灾情。
不是我们不支持遭受黄灾的兄弟省市,我们实在是力不从心,自救不暇啊……”
这是关键。
之所以下大气力请来这么多记者,给他们超规格的接待,送他们大包小包的礼物,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跟随视察团的流动电台上把这些解释向全国各地发出去。
遭受黄灾的省市集体发难,攻击东南沿海诸省见死不救,来势汹汹。
福建首当其冲,弄得很被动。
仅靠中央责难后临时征集的几车皮旧衣服平息不了四起的攻击,只有把福建自己的受灾状况宣传出去,才能让别人没话可说。
这是他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
每个记者身后都有人举伞遮阳。
福州的红灯绿酒,厦门的按摩女郎,石狮的走私货和餐餐生猛海鲜使他们对福建产生了不少热爱之心,很有感情地按黄士可的口径争相写稿发稿,深入进灾民家的只剩下黄士可。
诏安县县长跟在身后。
黄士可登楼时强忍着不发出肥胖者的喘息。
百灵和其它随从人员被留在外面,然而他仍觉得自己体重引起的震动会传进她耳中。
必须节食! 还要跑步! 这些天时时下这个决心。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心里突然装进一位美貌姑娘的倩影时,这种焦虑必是第一反应。
不管在别的方面多么自信,谁也逃不脱衰老肥胖和皱纹引起的沮丧。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家宅。
房主原来是个渔民,靠走私和运送难民发了财,把房子造得又昂贵又难看,非常显眼。
位置正在风口上,可房子没受任何破坏,连块玻璃也没碎,只在房檐屋角上,布景似地挂了几块塑料瓦楞板,当做被风吹掉的。
对记者讲话时,黄士可正对着这栋上上下下镶满了小镜子的蠢楼,每一眼看见它都止不住冒火。
不用多,只要有一个记者进到这里,如果又正好是个穷追猛打的家伙,精心布置的整台大戏就会露馅。
福建不但躲不过攻击,连他自己也会就此完蛋。
黄士可一走上楼顶,避开众人耳目,就冲着诏安县长的脸狠狠骂了一句最难听的闽南话。
台风损失远不如这次“视察”出来的那么严重。
三场台风连得紧,渔业和海洋运输受了影响,如此而已。
但正好碰上这个当口,适当转化也就有了必要。
坏事变好事。
开始只是应付责难,紧接着又有了更大意义,保住福建的腰包全靠这一招。
在精心的整体部署之下,十八号台风“刮断”了通讯线路。
当福建各地气象站与上级气象局重新恢复联系时,报告上去的台风数据不是从仪器上测的,而是福州通过隐秘渠道摊派下去的,与实际的差距在任何记录上也查不出来,哪怕老天爷亲自来对质。
多处地区出现局部“龙卷风”,“破坏”强度非常大。
数十个工作小组从福州赶赴“灾区”各地,指导灾情统计,制作报表,在视察团和记者团将要经过的路线上,事先统一好干部和“灾民”描述“损失”的口径,组织人员拉倒路边的树木,推倒电线杆。
在预定记者要停留的地方扒掉房顶,敲碎玻璃,扔上满地破烂。
夸大灾情虚报损失自古就是多得救济的招数,向基层布置别的事大都阻力重重,这种事却点一下就心领神会,配合默契。
黄士可很少对下面视察时能这么满意,这栋楼就更使他格外恼火。
诏安县长唯唯诺诺。
黄士可不听解释。
在从海上去日本﹑台湾﹑香港﹑印尼﹑南朝鲜──几乎是除中国以外的一切国家──寻找好日子的“难民”越来越多的时候,海边的船老大发财发得已经用皮箱装美元了。
这栋楼的主人既然能把一副名贵鹿茸送到黄士可在福州的家,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县长就更不知受了他多少好处,要不怎么那么为他说好话。
这种暴发户就是有了金山也丢不掉天生的小农意识,自己的窝连块玻璃也舍不得打,更别说扒房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