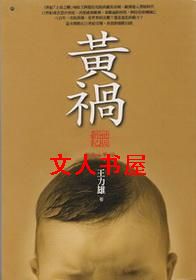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能‘流通’﹑‘交换’﹑‘增殖’。
全社会的‘美’越多,‘美’的质量越高,精神就越繁荣,社会就越进步。
‘经济规律’被‘审美规律’取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美’的生产服务……”
“我无法这样更换概念,物质产品有质量﹑形状﹑硬度﹑颜色﹑温度,‘美’只是一种感觉……”
“质量﹑形状﹑硬度﹑颜色﹑温度同样是感觉。”
“物理性质是能被测量的。”
“测量结果也得通过感觉才能被接受和认识,所以也是一种感觉。”
“……我们进入哲学范畴了。”
“那还是打住吧,那个范畴里只有各执己见。
不过我想既然你能感觉到‘美’,就不能说它‘虚’,……”
又一次中断。
伊万的肚子装不完第二盘。
他把剩下的冰激凌全部抹到了脸上。
“你怎么不往头发上抹 ”陈盼一边给他擦一边抱怨。
“幸亏盘里没有了,不然你这么一说他准往头发上抹给你看。”石戈揉一揉伊万的黄毛。
“去吧,自己看电视去,戴上架子上那个黑耳机,别捣乱。”
那天在“人阵”总部是欧阳中华第一次见石戈。
事后他打听了不少石戈的情况,不知为什么就产生了从石戈手里弄“基地”的想法。
可陈盼觉得眼前这个人完全是个务实主义者,满脑子考虑的首先是如何实施,有没有操作性等等。
他不直接反对陈盼的理论,然而张口闭口总是“环节”,似乎他的思想只有在一环扣一环的连续性上才能延伸,一个环节不清楚就决不往下前进。
这种人不是“精神人”也不是“物质人”,陈盼心里把他称为“权力人”。
他的生命力只会用于在权力机器上熟练灵活地运转,但永远脱离不了那呆板的机器框架。
无法设想一个只会解决眼前问题的权力部件有什么想象力。
哪怕派一个代表团正式请求,也难想象他是否会答应支持这样一个离“实际”十万八千里的“乌托邦”,然而她现在必须按照欧阳中华的意思,用完全“偶然的机会”和纯粹出于“自己的兴趣”向他提出建议。
“……你不能让我们凭空在脑子里把所有的环节都弄清楚。
我们需要实践,用实践检验和完善。
你给我们一个试验基地,我们就会给你全部答案。
怎么样 ”
欧阳中华一直挖空心思想弄一个以“美”为生活宗旨的社会试验基地。
那不但要搞一块飞地,还要切断外界权力的一切触角,等于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完全为所欲为地自行其是。
在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里,这算得上比登天还难的白日做梦。
“……咱们搞一个合作,”陈盼详细地描述了“基地”的设想后,又巧妙地把它和“权力机器”统一起来。
“基地算你属下的一个社会试验区──不仅是名义上的,你肯定会从中得到启发。
既然你的工作是研究和解决危机,你也应当搞些试验。
这个基地算你的试验之一。
也许最终你会发现,只有我们这个试验才能提供彻底解决危机的出路……”
一声叫嚷使他们扭转视线。
斜对面是一对吃惊的恋人。
两份刚要的冰激凌摆在桌角,其中一份不翼而飞,全部被踮着脚的伊万用手抓到了自己的头发上。
石戈和陈盼飞跑过去。
伊万眨着眼,对混乱局面十分得意。
石戈连连道歉。
恋人中那个姑娘比较厉害,白了陈盼一眼。
“当妈的也不管好! ”
石戈一边在各个兜怎么也摸不出钱,一边赶快声明: “我不是他爸。”
陈盼又好气又好笑: “你应当说我不是他妈! ”一边拿出自己的钱。
“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关系就不用赔了。”小伙子到挺大方。
“我们刚才猜了半天也猜不出。”
“对对对,我太老了。”石戈直点头,还是摸不出钱。
“少废话! ”陈盼把钱扔到桌上,揪一下石戈衣襟。
“快走。”
“他是我哥,她是阿姨! ”伊万接上了茬,伸着粘糊糊的手指头,冰激凌沿着脑瓜转圈向下淌,旁边人全大笑起来。
“我要揍你! ”石戈装出凶狠样子抱起伊万,狼狈地跟在陈盼身后逃到外边,找到一个水龙头,做出要用凉水冲伊万以行惩罚的样子,实际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他洗干净。
然后石戈半天没说话,信步在公园里走。
陈盼领着伊万跟在旁边,不让伊万打扰他。
不知为什么,刚才那场笨拙的表演倒使她多了一分信任,她觉得他不会像司空见惯的“权力人”那样精明地一口回绝,礼貌而又婉转,否则无需思考什么。
不过细节上仍然显出十足的“权力人”的精确和算计,看上去他是在信步,思考结束时却正好走到公园门口。
“你的建议或许值得一试,我听进去了,也记住了。
我的力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眼下什么都无法答应你。
容我琢磨琢磨,我会当件事来考虑的。”
等于什么都没得到。
陈盼心里却有一股暖意。
任务完成到这一步比预想的要好,没白等他这么多天。
公园门外就是天安门广场。
比起一九八九年,聚集的人少多了。
老百姓越来越不感兴趣,光顾的也只是看看热闹。
当年出现过的一切全都重演,绝食的,住帐篷的,“人阵”和“民阵”
的高音喇叭互相比赛,民主女神像也立在原来的位置。
接受以往的教训,不给当局口实,民主派动员了许多学生维持秩序和疏导交通。
长安街上跟往常一样车流不息,充斥着呛人的废气。
街对面停着一辆大卡车。
货箱上立着一面纸糊的大字牌,一字不少地写着“百字宪法”。
每个字都跟足球那么大。
刑拓宇站在字牌前演说。
离得远,加上车流噪音,只能断续听到一点。
他在怒斥逐级递选制只给人民选举“伪保长”的权利,是有史以来对特权进行最大垄断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选举制,最后,邢拓宇接过车下人点燃的一支火把,挥动着向那字牌一字挨一字地击去。
一击一个窟窿。
火焰随之沿着每个窟窿的边缘燃烧扩展。
他按顺序击穿每一个字,符号也不放过。
这字牌肯定是“人阵”制作的,专门为了进行这番焚烧表演,作为对“百字宪法社”一次算总帐的回击。
围聚的人随着每一击叫好,逐渐成为有节奏的集体吼叫。
陈盼侧脸看一眼石戈。
伊万骑在他肩头兴奋地跟着节奏喊好,小胳膊随着邢拓宇每下击打使劲挥动。
字牌的火光似乎横穿街道在石戈脸上隐隐辉映,他的神情像凝结的岩浆。
March 29; 1998
Ⅱ台北“我给你六百万,”那个共军上校回答。
“但是必须在中国,必须在四十五天之内,必须死! ”
整个台湾岛似乎只有一个人对刚刚结束的大选漠不关心。
而对全体台湾人来说,这次大选的意义超过许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表面上只是执政党的更迭。
民进党以52%的多数选票战胜国民党,取得了“中华民国”的执政权。
这种更迭在任何一个实行多党制和竞选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
然而对于台湾,其意义不仅在于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下台,民进党建党以来第一次执政,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台湾人民对台湾前途一个转折性的新选择。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击溃,退守台湾,几十年来奉行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反共复国”为基本国策。
然而某种意义上,国共好象同室操戈的哥儿俩,虽然你死我活,却有割不断的血缘,都认定自己是“室”的主人,把“家室”统一视为己任。
蒋氏政权时代,“反攻大陆”的政治目标和军事准备成为不自量力的侈谈,台湾的经济起飞却令世人瞩目,远远把大陆甩在后面。
台湾做为独立力量在国际上生存几十年,政治观念﹑文化意识,生活方式都与大陆发生了根本的歧异。
在多数人心目中,自己已无所谓中国人,而仅是台湾人。
台湾与中国彻底脱钩,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台独”运动便由此发展起来。
国民党政权曾对“台独”运动进行严厉镇压,然而随蒋经国死前实施的“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两大措施,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的民进党顺时而生,“台独”势力也蓬勃崛起。
民进党许多成员都是铁杆儿的“台独”分子,曾一度把党的从政宗旨公开放在“台独”上,后来虽然调整了策略,这个目标却一直不变,民进党只有依靠本土意识才能战胜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在台湾人口总数中已占绝大多数,隔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对他们同大多数外国一样陌生,除了那儿的市场和资源,其它方面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国民党挂在嘴上的“统一”一直被他们认为是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台湾岛虽然不大,生活起来却很美好,有什么必要和一个随时能吞掉自己的大家伙搞统一呢 不过多数台湾人也担心公开独立会招惹大陆对台湾用武,二者毕竟不成比例,台湾抵挡不住,那样独立谈不上,生存也无法保障。
对于一个工商化社会,眼前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多数台湾人也反对赤裸裸的“台独”主张和过激行为,名义不重要,只要能在实际结果上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别弄到一起去就行。
民进党接受早期操之过急的教训,实施了一种“无旗战略”──既不谈统一,也不谈独立,只要维持现状,主张与大陆一切正常化,力促两岸贸易往来,就像长大成人分家的两兄弟,互通有无,算帐清楚,其它方面则井水不犯河水。
这个正确策略逐年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意会和拥戴。
国民党后来虽也迎合台湾人之心态软化了坚持统一的立场,搞起“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但它的“大陆根”毕竟太深,难以弥合与台湾本土的歧异,最终落得这次大选的结果。
整个台湾岛都被选举结果震动,从上到下一片混乱。
各国驻台北办事机构忙得不可开交。
迟到的记者们更是像蝗虫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又把无数电波向世界各地发去。
这其中,唯有一个人置身于外。
他既不看当天的报纸,也不理睬电视和广播,对街头演说﹑两派争论全无兴趣,更不参与公共场所的议论﹑欢呼和冲突。
他在阳明山公园一片寂静的小树林里悠然欣赏着一种亚热带球状的琥珀色果实。
往日那些闲情逸致的游客,打太极拳的老人,或是谈情说爱的情侣都被外面的热闹吸引去了。
但此时若有人能从数米之外看见他的话,一定会对他的姿势感到奇怪。
他的眼睛离那串果实未免太近了,而且只盯着一串果实。
如果从两米之外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他,就会发现他原来不是在欣赏果实,而是在欣赏自己。
一枚椭圆形的小镜子挂在果实和叶子之间。
看他那副专心致志的模样,不时地抹抹嘴唇,弄弄头发,一定会让旁观者觉得他有自恋症一类的怪癖。
但是再近一些,而且是从正面观察,就会发现随着手在脸上动作,他正在逐渐从三十岁的年令变成五十岁。
仅仅几分钟,当他最后把一撇小胡子贴在嘴上,戴上一副老式金边眼镜时,他便从刚才那个轻松愉快的菲律宾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呆板博学的日本防卫厅学者。
原来的皮背包翻过来拼装成一个精致的公文皮箱。
而花里胡哨的衬衫翻过来就显得陈旧保守。
他的步伐也从轻浮的窜跳变成了军人式的端正。
招呼出租车的手势如同敬军礼。
当他在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资料馆查阅资料时,他的形像﹑语言和证件都没引起任何怀疑。
全世界有关中共政权的资料属台湾最多,台湾又属这里最多。
其它国家研究中共政权也许仅仅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或是有备无患,只有台湾是出于生死存亡,而台湾军队又是这生死存亡的首要担负者。
所以“中校”──现在叫“小野中二”──索要的资料虽然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保卫方式”这样一个极细的题目,从库房里推出来的却是满满一车。
这是几十年从不间断地从各种报刊﹑出版物﹑回忆录﹑审讯材料﹑外国人的访问见闻﹑叛逃者的描述以及潜伏在大陆的情报人员的调查一点一滴汇集而成的。
即便中共在这方面从来讳莫如深,几十年所露的蛛丝马迹拼凑在一起,整体的形像也差不多一览无余。
“中校”看得很快,再复杂的保安措施他都一目了然。
暗杀专家必然是保安专家。
他在这方面已经一通百通。
何况他刚刚在香港的图书馆坐了十好几天,所有的背景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