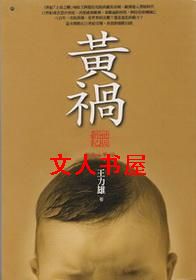黄祸-第10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边的“九—04”立刻表态; 反对临阵更换最高指挥; 几支“九级”队伍都处在以“青海”为中心的位置; 这种布署已决定中心不能转移; “青海”一路表现的指挥才能未见得比“西北”逊色。
其他火光也都表示赞成这个意见。
远处闪烁的火光静止下来; 似乎是几只明亮的眼睛看着“西北”自己怎么表态。
他本想跟他们说:“我在验证石戈的话。”可是用火光解释这一点过于复杂; 耽误时间; 于是只发了两个字:“很好”。
掀动的挡火帘把火焰煽得飘忽摇摆。
干柴爆裂出四处飞溅的火星。
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酸溜溜 脚下岩石已被火烤得发烫。
汗水在裸体上无阻挡地流淌。
那次是“绿大”四个学院加上研究院、教师院和职工院七个院长选举石戈任校长; 石戈表示当选令他高兴; 但更高兴的将是在他被罢免时。
戴着创始人的桂冠和有着总理职位; 在哪种制度下都会被推举; 难的不是这种人的当选; 而是这种人被罢免; 只有他被罢免时才最能体现逐级递选制的真正优越; 才是他做为创始人的最大光荣。
邢拓宇知道自己没有石戈那种地位; 但能被下级毫无客气地一致否决; 也已说明了一点问题。
会议主要内容是分配每支难民队伍下一步的去向。
这对每个人都是决定命运的; 几乎有点像决定投胎做法国人还是波兰人那样将导致全然不同的未来。
别说由几千万难民; 就是缩小到几百个代表也只能吵破天而什么都定不下。
“九级”会议却非常简便。
火光通讯不宜详细讨论; 没有特殊意见就由会议直接对每个议题进行表决。
多数赞成即为决议; 多数反对即被否决。
东路将是最艰苦的; 不光因为他们的终点在路途最远的寒冷北欧; 还因为一路经过的东欧和俄国既贫穷又遗留着斯大林主义的残暴; 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比别的方向更大。
负责东路先遣的“九—03”表示无法保证他的队伍能从头走到底; 一直充当为后面队伍突破国境的角色。
难民毕竟不是军队; 没到目的地前为了求生可以服从指挥; 到了适合居住的国家再让他们继续走就难了。
“九级”会议同意这个看法; 修改了决议。
每突破一个国家; 先进入的队伍先留下; 直到饱和; 后面的队伍便成为突破下一个国家的先遣队。
这样借助空间满载的自然压迫; 给后续难民走下去的动力。
这是逐级递选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则——每一层的行政领导者集体构成更高一层的立法者; 而他们推选的上级就是执行他们立法的行政领导。
这种关系远比三权分立制灵活、准确、及时和彻底; 同时仍然保持制约的能力。
邢拓宇在“九级”会议中是立法者; 制约上级“十—1”并接受其具体领导; 而面对选举他担任“九—01”的五个八级; 他就是他这个“九级”组织的行政首脑了。
“九级”会议结束后; 他们围着残火余烬接着开了“八级”会议; 布置天亮就将开始的对奥地利国境的突破。
“九级”会议所做的决议是“九级”及以下各级组织不可违背的上级法令; 但对他们这个“九—01”组织之内的事务; 则完全由“八级”会议自己决定。
这是逐级递选结构的另一个原则——每一级组织都有高度的自治权和在自己组织之内的立法权。
晨曦已经在东方泛白。
“八级”们一散会就匆忙赶回各自队伍去和“七级”们商量。
“八—103 ”用衣服包走了已被露水打湿的柴灰; 那是制造薯瓜营养液的好原料。
邢拓宇独自留在山顶。
以往他从不多愁善感; 近来却常陷入遐想。
也许是距离太近; 时间太短; 国破民亡在他心中远没有产生同等规模的悲伤和震撼; 更多的是怅惘; 掺杂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惊讶。
每当夜深人静; 就悠远地在心灵的旷野中画出问号似的白色树影; 传来一个凄长的类似哭坟的歌声; 总是同样旋律; 伴着飘忽于天际的一张纸钱。
北方是奥地利国境; 灯光雪亮; 排列着乌光闪闪的坦克和装甲车; 如同挡住国境的钢铁大坝。
欧洲军队几乎把所有军力都调到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欧共体边境。
从东方奔泄而来的黄色洪流使欧洲陷入末日般的歇斯底里。
与之对比的是在杀人武器瞄准下; 中国难民视若不见地席地而眠。
难民最前端离那道坦克大坝只有几十米。
东方的青白泛起得更多了。
一窝小鸟在近处的灌木丛里啁啾。
他想起在太白山陈盼曾分析他排斥绿色运动的心理; 不见得是他只认定红色革命更正确; 而是在他心灵深处; 那种对血与火、英雄主义和轰轰烈烈的渴望太强烈。
绿色运动是和平的; 因此对他就如同嚼蜡。
他当时反对这种分析; 现在回味却不无道理。
从刚懂事他就梦想着成为凯撒、拿破仑那样的名将。
此时他真的有了一支队伍。
一千零六十万人; 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庞大的大军! 可是既无英雄乐章和浪漫激情; 也无凯旋仪式、勋章和鲜花美酒; 只有无边的饥饿、瘟疫和死亡; 黄灰色的人流铺天盖地滚动; 如滔滔泥浆。
然而; 这支凄惨的大军难道不是正在同样横扫世界吗 天边出现红霞了; 从难以与青灰区分的暗红一点点转成越来越美丽的鲜红。
邢拓宇沿着荒草覆盖的小径下山。
他很想在山顶看到太阳光芒万丈地跃起; 但他知道明智的选择还是回到相互以体温抵御清晨寒气的人群中睡一会儿。
穿过山腰几块巨石之间的缝隙; 突然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从后面扼住他的脖子。
他用本能的反应向后猛踹一脚; 却像踹上纹丝不动的石柱。
几个人影闪到面前; 全穿着中国难民的破烂衣裳; 却在晨光中露出西方人深眼高鼻的脸。
几十米外就有成千上万的同胞; 可他一点也喊不出; 连气都透不过一丝。
正面的胖子熟练地向他腹部猛击一拳。
他只觉五腑六脏以空前未有的能量向头顶冲起; 便是翻滚着坠进无限的漆黑……失去知觉的时间似乎很短; 可天已大亮。
费了半天劲才把天边红霞和眼前穿白大褂的大夫联系在一起。
他躺在一张沙发上。
好几双眼睛身看他。
“……很抱歉……”一个蹩脚的汉语似乎从很远处飘进耳朵。
邢拓宇没学过任何一门外语; 听不出那位灰白头发的将军讲的是哪国话。
但他在训练营学会了辨认欧洲所有的旗帜; 因而从墙上的旗看出自己落在了欧洲统一军队的德意志军团手中。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他费力地坐起; 打断翻译。
将军那些冷漠的致歉不用听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打手按打正常人的力度下手; 没想到他的虚弱使昏迷时间增加了好几倍。
焦虑正挂在每张脸上。
“我赞赏直率的方式。”将军说。
“眼前也已确实没时间兜圈子。
我们请您来这里; 只希望您能让中国难民不进入欧共体边界。” 副官给邢拓宇倒了一杯酒。
他却指指桌上剩的半份早餐。
“为什么……您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他吞咽面包和煎鸡蛋。
将军没说话; 用食指点了一下他左臂袖标上的“九”字。
挨过打的空胃被食物刺激开始激烈痉挛。
“您白费力气了。”“我们可以满足您个人的一切要求。
注意; 我说的是一切; 只要您提出来。” “这不是我个人的事……” “我们可以让所有袖标符号在‘四’以上的人都成为体面的欧洲公民; 给你们房子、工作和财产。”邢拓宇试图止住胃的痉挛; 一口喝光杯中的酒。
“您认为数字越大就越管用吗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目前最大的数字就是您这位‘九’。” 邢拓宇笑了。
“我们这个数字结构不能用数学概念衡量; 数字越大越是下级; 越要被决定而不是决定; 越要服从而不是被服从。
您实际上抓了个最小的。
您若把最大的抓来并且答应他们的条件倒是能成功; 但那正是四以下的全体; 也就是所有难民; 却是您最不想要的。” “您是不是在跟我玩概念游戏 ”“我的胃他妈的疼得要命; 一点没心思跟您玩游戏。
您对逐级递选制了解得太浅薄; 我不得不给您讲点初级常识。
您尽可以试; 即使您用希特勒那套逼我按您说的办了; 我马上会被我的下级罢免; 也就成了一块对您半点没用的废料。”“我不相信您的‘马上’; 连推行了几百年民主的西方政体也不可能这么干脆; 你们一群乌合之众能有这种效率 ”“这只能说明您的‘几百年民主’不灵光。
用您的概念; 我的手下是八级。
实际他们是的我的上级; 只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想撤掉我另选一个‘九级’只是彼此议论几分钟的事。
论才智; 这五个人谁也不比我低。
如果我直接领导一千万难民; 把他们骗到别的方向去是可能的; 可领导这五个人却绝对骗不成。
您要是给这五个人的肚子也打一拳弄到这来; 他们下面还有二十八个‘七级’。
我可以把我们的组织结构毫无保留地全告诉您; 一点不必担心您的目的能得逞。
因为对逐级递选结构; 除非您把所有人全部收买; 否则怎么费尽心机也无法破坏。”“我不喜欢您这种绝对化的结论。”“这我相信。”邢拓宇看一眼表。
“您可能更不喜欢我的估计: 现在一个新的‘九级’已经被选出替代我了。”“根本没人知道您被绑架! ”将军的涵养看上去快到头了。
“我怎么失踪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新选一个‘九级’的原因在于‘九级’的工作必须有人做。
我看这像一个了望塔; 窗口那家伙应当是个望远镜。
如果您允许我用它看看; 也许我可以证明我的估计。”将军凝视他片刻。
“请。”了望塔相当高; 收入视野的面积很大。
正当盛夏; 山峰全是绿色。
然而对面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所有山谷却被一层蠕动的灰黄覆盖。
那是落满灰的黑头发和沾满泥的黄皮肤; 无穷无尽。
在高质量的德国望远镜中; 能看清很远的人脸。
只有最熟悉难民组织结构和布置的人才能在这片人海中找到目标。
当邢拓宇停止移动望远镜时; 他几乎想笑出声来。
“请。”他把位置让给将军。
望远镜已推成一个年轻男子的特写。
他正在向身边的人有条不紊地发布指示; 一边做着手势。
他的胳膊不时划出镜头; 然而每当他左臂收进画面; 就可以看到那上的袖标清晰地写着“九—01”。
跟邢拓宇预料的一样; 是“银川”; 原来的“八—103 ”。
他想过好几次。
一旦他有意外; 这是最让他放心的接替人选。
将军在望远镜前看了好久; 脸色越发阴沉。
“难道你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廉耻吗 ”他在牙缝里问。
“为什么非往别人的土地上赖呢 ”过去邢拓宇一定不会容忍这种侮辱; 现在只是收起笑容。
迁移队伍的纪律之一就是对漫骂挑衅甚或殴打都保持克制。
无论有什么理由; 迁移确实侵犯和打乱了别人的生活; 因而不能强求人家对自己尊重。
中国难民想在别人的家园扎下根去; 恰当的方式只能是用礼貌、歉意和自我约束争取同情。
“您能解答我这一个问题吗 ”邢拓宇很安详。
“据说以前的地球几十亿年没有人类; 也没有民族; 在上帝手里; 它是一个整体。
可现在; 人类只有几万年的历史; 为什么把地球弄得挤的地方那么挤; 松的地方那么松 是谁给了号称民族的人群划分地球的权力; 并把这种划分视做天经地义的呢 ”“人类生存需要秩序; 而国家主权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创造的最重要的秩序。”“依我看; 所谓主权倒更是人类灾难的来源。
回头看看; 哪一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少过它 主权本质上是一个强权概念; 国家更是一种无理的占有。
大自然无国界。
国界是用战争和军队划分的。
那么凭这么一个概念就不惜让数亿生命死亡更是不能接受的。
反过来说; 三百年前欧洲发现新大陆时; 你们又何尝尊重过印第安人的主权呢 我们只是要生存; 你们却是去屠杀和抢劫! 难道你们迁移完了; 你们的秩序就成为永恒; 别人再迁移就成了没有廉耻了吗 ”“不要忘记; 过去的已经是历史; 而我们生活在今天。”“同样别忘记; 对于未来; 今天也是历史。”将军愤怒地盯着邢拓宇; 两只手臂如同要出拳一样垂在两侧。
邢拓宇觉得逐级递选制奇妙地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人的激烈大多出于内在的紧张和压力; 逐级递选制提供了一种整体的结构保障; 无需把千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