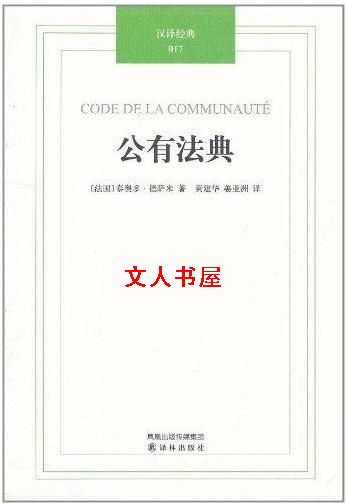公有法典-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圣西门的原则是: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这仿佛是确认基于能力和工效的新的不平等,亦即承认新的贵族。然而人们怀抱的是这么一种理想,即智慧和体力的优越,与其说是产生权利,毋宁说是产生义务,而财富的分配准则是按照实际需要而不是依照能力和工效的。”(《独立杂志》,1814年11月)
皮埃尔·勒鲁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当一切形式的贵族制度正在消灭或已经死亡的时候,哪个具有常识和良心的人会想到,要在能力的名义下或在献身精神的名义下,复活贵族制度的原则呢?至于我,我深信,不平等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归根结底,总要变成一种腐蚀人的麻疯病,成为一切腐败堕落的不竭之源的。但是,你们却想来违反社会的根本法,因为你们在想象中为自己造出了幻影。你们是多么天真啊!难道你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和成为弟兄的时候,一切其他品德我们还都会具备的。让我们首先开始深入地领会我们的原则的伟大和可靠性吧,让我们赶快形成强有力的团结一致吧。那时我们就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事业的胜利需要的话,献身精神便自然会产生出来。因为有哪一种制度会比公有制更包含潜能和力量,从而把一切美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呢!
不必担忧这种共和党人的热情只是一种虚幻的博爱。不,不会的:这种神圣的博爱每天都会进一步增长、扩展、提高和巩固。同情、友爱、公共风尚、教育,我们全部最牢固、最紧密的习惯,最后,科学的规戒,还有必要时法律的指令——所有这一切是何等强大的动力啊!由此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不仅在危难中互助和互救①,而且还要促使他们自发地采取最英勇最崇高的行动!
①我认为某些人太担心这些令人悲痛的偶然变故,它们在目前情况下,是为数如此之多而且不可避免,但却绝对不是自然规律使然。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某些人就虚构出献身精神。我敢于证明,在公有制度下,仅警察法和卫生法或许在一年之内就足以预防千百万件偶然变故和灾难,而所有宗教、一切道德戒条、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则用二十个世纪也绝对防避不了的。——原注
公有制!公有制!所有可能达到的善和美都概括在这一个名词之中了。要求社会秩序和完美性有更高表现,岂不就是陶醉于有害的幻想中,追求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吗?
我再说一遍:是的,献身精神无疑是美的,但它与我们的本性不大相符:这是一种狂热的、激烈的、不自然的状态,只能存在于危险的关头之中。
要把献身精神作为社会秩序的永恒基础,这无异于固执地从尖顶开始建造巨大的金字塔。因为,请注意,为了使献身精神成为建筑物的基础,只有几个人能献身那是不够的,必须使献身行为象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那样普通。而在这个独外、垄断、私有制和贫困的可恶的制度中,要指望这种事情是十分不明智的。因此,我们不要作这样的幻想,竟至于想在人的心灵中铲除那种如此亲切的、人们称之为个性或自爱的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是牢不可破的。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的意见,特别是马布利和卢梭的意见就是如此。
卢梭说:“一个人要装出把我的利益看得比他自己的利益还重,那是徒劳的,无论他用什么诡辩来粉饰这一谎言,我仍然肯定他是在撒谎。”
马布利说:“古代法律从未荒谬到让公民去牺牲自己,把公益看得比自己的福利更重要。古代法律仅仅是号召公民,为了总的利益,暂时忘掉自己。”
还有另外一条原因,十分有助于仔细的观察家戒备我们大部分谈论美德和献身精神的饶舌家的伪善说教,那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就有成千个把自己所装出的美好感情变成手艺和商品者。他们为献身和牺牲高设祭坛,那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要成为祭司;让我们把话直说了吧,他们为的是从受骗者那里收罗奉献的礼物。在这方面,他们使我们联想起贝尔①的祭司的故事。这些祭司一到夜间便从自己的秘密住所中出来,去偷食供献在神案前的佳肴。而这些精美菜肴就是人民出于轻信,不听那时哲学和理性的号召而供献于神像的案前的。哲学和理性号召人民说:
①贝尔(Bel)是古代美索波达米亚宗教中的主神之一。
“不要在你们的神像的祭坛上供献珍贵的祭物,
人民啊!不要把礼物送给比你们更富有的人。”
我希望,现在再没人来和我争论社会平等的原则了。假如某些民主主义者仍然敢于这样做,那他们就别再自称是卢梭和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好了。国民公会早已用下面高度简洁的格言驳斥过他们: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西哀士在其权利宣言草案的下述段落,就曾合理地阐发了这句格言:
“两个人之间可以在能力上存在不平等,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可以在权利上不平等。
“社会法律的设立,绝不是为了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以抵御强者,保障他们获得全部权利。
“力量产生作用,而并不产生义务。压迫,绝不能成为压迫者的权利,受压迫也不能成为被压迫者的义务。解放永远是一种权利,甚至还是一种紧迫的义务。
“按自然状态,人没有权利加害别人,因而也没有权利拥有剩余的东西,而使别人得不到必需的东西。
“人们需要设想一种协定、一种法律上的认可,以便能够赋予所有权一词象我们在自己的政治社会中所通常给予的全部的广泛含义。”
这个问题,卢梭已经通过《社会契约论》的下述卓越的公式加以解决了。
卢梭说:“基本契约是以道德的平等①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来代替自然界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体质上的不平等。如果说,人们也许在体力上与才能上是不平等的,那末,他们在契约上和权利上则是平等的。”
①在让·雅克笔下,“道德平等”的说法,在我看来,与匀称的观念完全符合,而共产主义者就是把这个匀称观念同社会平等这一公式联系在一起的。——原注
关于这一点,在本章已经谈够了;不平等已经败北。
至于公有制原则,它本身就概括了我们全部的根本法,当然它合乎逻辑地导源于社会平等原则,而社会平等原则只有公有制才能加以实现。对于这一点,本著作中的主体部分比我刚才的全部推论还会显示得更清楚一些。下一章我就开始写这个部分。
第三章 分配法和经济法
“纵使今天所有愿望都得到满足,在公有制未把邪恶的欲念压下去以前,明天谁也得不到幸福的。”
——贺拉斯
我在上一章已经证实,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因而在事实上也应该平等。但不是象给士兵、贫穷的病人①分配和囚犯口粮那样向公民实行定量分配的那愚蠢的卑微的平等,而是自由的、慷慨的、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提高和开阔我们的思想,密切我们的感情并使所有心灵都融会到感激和共同欢乐的永恒感情之中。然而,我们已经说过,这种真正的平等只有伴随公有制而实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使这种公有制社会和谐运转的最适当和最有效的手段。这种社会该会有一天给所有人提供唯一真正可贵的福利:健康、和平与安全,而由此必然产生道德并随之而带来幸福!
①去年12月,《独立杂志》曾把军队、收容院、监狱作为公有制组织的成分。至于我们,则竭力避免拿这种带有野蛮和不道德的印记的机构作为我们的制度的模式。公有制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迅速地完全消灭这类机构。然而这些机构本身却确凿证明我们的经济原则和我们团结一致的学说的力量。无疑,《独立杂志》就是从后一意义来论述的。——原注
为了使一切事情都在良好的秩序中进行,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把庞大的民族集团或社会集团划分成许多个公社,这些公社所拥有的土地尽可能相等、整齐和连成一起。所有这些小公社,互相联系起来,组成联合社或公社系统,依照地理状况和地区性质而定。这样,由一定数量的公社构成一个省,由一定数量的省构成一个共和国,最后,所有各个不同的共和国合起来构成一个伟大的全人类共同体。
当这一过程完成后,就要谈到向公民提供住宅的问题了。
从以上所述,读者可能以为我的主张是维持首都、省会、市镇或者乡、村等的原则,一句话,维持全部旧的地区等级。这和我的想法相距太远了。我深信,甚至不值得为此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由我们的根本法中的一项法律(平等法)所解决了。在公有制中,只能存在公社。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教育怎么能变得彻底统一呢(我是从广义的角度来了解教育一词的)?怎么能实行那种完全一致的风俗习惯,那种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苦乐与共、全部意愿相同的密切统一呢?怎么能使目前所称呼的城市人和乡下人这种名称消失呢?最后怎么能利用儿童的积极性而不致强迫他们从事所谓世袭的职业呢?
卢梭在他的著作的很多地方都曾经表示坚决反对大城市和首都;在这方面,他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费尼隆、马布利、爱尔维修等的意见是一致的。
然而,谁也不曾比尊敬的邦纳罗蒂以更大的魄力和远见来谴责这种糟糕的制度了。让我们来听听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明智的见解吧: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大城市的存在是公众不安的表征,是公民骚动的必然的前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富商大贾成为城市的核心。在此核心的周围开始集聚着许许多多靠他们为生的人,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需要,迎合他们的口味,迁就他们的任性,激发他们的恶习。
“一个城市的人口愈多,其中仆役,伤风败俗的女人、饥肠辘辘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①、谋士、演员、舞蹈家、教士、撮合人、小偷以及各种各类的丑角也愈多。
①邦纳罗蒂并非咒骂以上四种职业本身;他指的是不平等制度使这四种职业趋于腐化和堕落的情况。——原注
“豪华的宫殿、宽广的花园、富丽的陈设、华丽的车马、众多的仆役、熙熙攘攘的客厅,这些都是所谓大城市的装饰品;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受其诱惑的人们的心灵发生有害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东西加强了其拥有者的高傲心理,使他们把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都看作仇敌。因为嫉妒和贫困经常在推动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从拥有者手里夺过这一切,并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和贫困而报仇雪恨。另一方面,那些丧失了这些东西的人,或者由于贪欲和憎恨而堕落,或者竟沦为卑鄙下流的人,成了野心和暴虐的支柱。所有这一切,不论对于享受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或者对于希望得到这些东西的人来说,都成了真正的祸害。因为在某些人感受烦恼和猜疑之苦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因为渴求虚幻的财富而备受折磨;在他们看来,这些财富正由更幸运者占据着。
“在大城市里寻求享乐、奢华和荣誉的人可以不用劳动;他们已把自然赋予每个人的那份劳动推给别人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仍留在田间劳动的人的任务便超出了自然的限度。农业劳动和必需的工艺劳动对他们来说变得更加繁重和艰苦。祸害日益深重,竟至使农民和工人的地位降到几乎与苦役犯人的地位相差不多,最后,这种地位竟变成耻辱,为大家所抛弃。于是,每个农民都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大城市,一有可能就奔往那里去寻求财富,因为财富的魅力被他们的想象夸大了。既然干出了蠢事,沦落在城市中,就必须在那里生活下去。榜样是诱人的;大伙都在掩盖罪恶以逃避谴责;情欲激发了起来;从前看来令人厌恶的事情逐渐成了好风度和有本领的标志。人们很快宁要金钱和捧场而不爱义务和美德。圆滑和随机应变促使人们变成伪君子、撒谎者和骗子手。如果时来运转,人们会达到这样境地:虽然得不到幸福,但可显出幸福的样子,也就成为一大群冒失者的追求目标,这些人从失算和幻想之路迎着不幸走去。
“然而,由于财富、享乐和放荡生活的吸引,许多竞争者汇集于大城市,这些人的数目激增,以至于其中的大多数,仅靠微薄的工资度日,被荒淫无度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还拖着沉重的儿女负担,便汇聚到凡有大城市之处都可见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广大不幸者的行列中去。
“既然农业和必需的工艺是社会的真正养育者,那末,人们就自然要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地方生活,他们或是耕种土地或是给耕作者提供便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