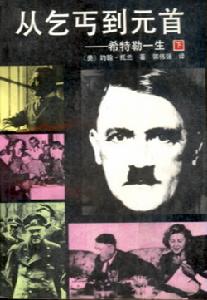从乞丐到元首-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10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6000~7000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