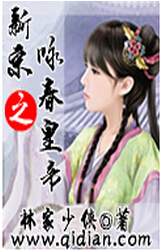新宋-第4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潭学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
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吴充有个女婿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则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遭此重创,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别人道德低下、人品败坏,但如今旧党官员徇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真叫报应不爽……而旧党官员,全都噤若寒蝉,纷纷到冯京、孙固那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想急流勇退,但皇帝病情反复,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本,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亦只能无可奈何。
而范纯仁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他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诺诺,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着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着却迟迟没有消息。
第二十八节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拙,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株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吆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谘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作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