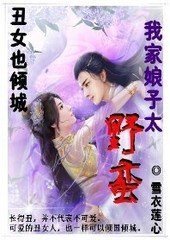红伶歌-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我与你交好,形同姐妹,将来姐姐有的,定分给妹妹。我这里有好消息告诉你,若你家主子听了,定会高兴的,以后若你高升了,可别忘了姐姐的份。”
她笑的如此假意,她以为自己即将立功,靠的是出卖。玲珑的玉手接过的是大叠的金钱。她身上有视空的影子呢。“姐姐但说无妨。”
我道:“听观仪那丫头说,我家主子其实并非有孕。他们是想诈孕,为的便是那后位。”
她眼中略过算计,转而又笑焉如花:“姐姐说的可是真的?”
我点首,道:“姐姐怎会骗你。”
她已跃跃欲试,急不可奈。长廊上,尽是她飞奔而去的脚步声,长廊那头,可是地狱深渊?
再回首,昨日我口口声声唤着妹妹的女子,踉跄着欲逃出这大殿。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将那婢女一同押入大牢!”她已被人牢牢绑住了身躯,动弹不得。双眼忿忿看向我,又似乎参合着一份悲凉。
对不住了,谁教你是南宫的人,待你死后,我会为你上香。我闭上双眸,默默祈祷,不愿看那我一手而成的惨绝人寰的场面。
南北两宫的臣人都乱作一团,南宫主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他们以开始乱了分寸,有些见风驶舵的臣子人似乎开始考虑重新投奔的方向,秦生平素的镇定消失无踪,他站在南宫坐席旁,看着这出滑稽戏码上演,却无力挽回。他定是未料我会出此一招。他忘了女人的嬗变。
秦湘郡神色复杂,站在秦生身后无措的看着萧妃惨白的脸色,她是不敢置信的,摇首如波浪鼓,然后跑出了北宫大殿渐渐被夜色湮没。
整场庆典因此而告罄。而我与江月侥幸逃过一劫。秦生再次回到他恍如隔世的自我世界,埋首灌酒,今夜的他如此反常,不似温良的七王爷。黎涧不甘的看着他,他与他之间,定有兵戎相向之日。我有预感。同是文官,却立在两个角落默默为己,如两条永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在我眼中,他们似乎又如此相象,同是如此沉默寡言,同是如此大隐于世。
中庭有寥寥数人不愿离去,秦生,黎涧,修真,江月。他们各自占据一席之地,一声不吭,神态凝重。霍太医在偏殿为萧妃把脉,我陪同一旁。我们的王徘徊在殿外,焦躁的来回踱步。夜色更深了,星辰被厚重的云层遮挡,月,半露着,让这大殿倍显苍凉。
我自萧妃衣下探出一纸包,猩红如血水,这便是此事的元凶。原是藏在她怀中的一小包染料,扎在萧妃腹部,我嘱萧妃千万小心,今夜正如我所料,淑妃因听了她贴身侍女的话,踹向她小腹。纸包破裂后,染料便流出,犹如血水。
“娘娘,这次您终于除却了您的眼中钉。”我道。
“可那婢女知晓我们的事。”她担心道。
“娘娘宽心,上次我除了给她银票,还给了她您的玉钗,到时我们说她窃了您的财物,这次她死不足惜了。”
她缓缓点着头,不再开口。
“霍太医,皇上在外等的焦急呢,您快去回禀娘娘病情吧。”
他站起身,观仪开了门,将他领出偏殿。
“皇上,娘娘流产,胎儿不保。”他下跪,道,“罪臣无能,请赐死。”
我们的王看向天,今天的夜空,到处是黑色,似一块黑色幕僚遮住了这凡世。“你退下吧。”此声何其无力,其中辛酸无人知。
我送霍太医出了殿门,中庭中的几人不约而同上前询问。
我巡过他们一眼,代太医回答:“娘娘胎儿不保,太医无能为力。”
有人欣喜有人愁。众人神色迥异,首先开口的是修真:“娘娘无恙?”
“伤了身子,现在塌上休息。她不愿有人叨扰,各位请回吧。”我回道。此话我对着修真讲。不知他是否听进了,依然巍然不动,刹有不见其人誓不罢休之态。
这将军在战场如此洒脱,为何在此却扭捏作态。不懂情为何物如我,亦不懂他对她的担心超过一切。
“本王代表南宫,向萧妃道歉。”秦生开口却震住了所有人。他第一次如此低姿态面对他人。在他的世界,怎可能知晓错字为何?
“王爷,萧妃会心领,奴婢会尽绵薄之力为淑妃求情。”我笑的坦然,似一切与我无关。
我的目光不自觉间在寻找着一抹踪影,却未果。黎涧不知何时已离去。
“那黎大人似对你有意。”他道,目光欲在我身上搜寻些什么蛛丝马迹。
“三王爷也如是说过,都是些玩笑话,奴婢怎承受得起黎大人如此厚爱。”我一笑而过,心却如此动荡不已。一半辩解,一半说服自己。
“本以为凭你之力,毫无建树,却不曾想过会为一至交论生死。”他叹道。“本王对你另眼相待了。”
江月一脸感动,紧紧牵着我的手。如果没有这七王爷,或许我们已在九泉相会了。“还得谢谢七王爷,若没有您,我们已命丧黄泉,遗臭万年,无人怜惜了。”
“本王亦是明辨是非的人。”他笑的如此超脱,让我看不真切他真意为何。
我心中一再反复,我要与他继续斗下去吗?为报那一掌之辱。
建元二年夏,萧妃登极为后,她原名陈阿娇,遂封号陈皇后,普天同庆,与民同欢。民间传说淑妃无恶不作,迫害萧妃龙子不保,百姓无不愤然。萧妃劝解王将淑妃自天牢释放,后淑妃常年独居西殿冷宫,郁郁寡欢,时常有疯癫之举。黎民百姓均为萧妃宽厚仁义形象啧啧称奇,莫不赞她为后主。
曾经无数里梦里辗转,那悬空大师的话犹言在耳:“只要你坚守时日,命中会有真龙自天而降,提携你一跃而为人上之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梦中那人站在岸边朦朦胧胧,似真似切,飘渺的风带走他的音信,那声音在岸边回荡,悠扬似拂丝弄竹。醒来后,只剩空寂的夜中我的泪水划破脸颊的声音。为何心撕裂般疼痛难忍?
四
此时
我无比期盼有朝一日能够光明正大进入南宫大殿,无论她的主人是谁,只等待有一日我不用卑微屈膝低首不得见其人,垂帘后的身姿只待王垂爱。
衣衫飘袅只为座上宾,舞姿如何妖媚仅为贵人,歌喉如天籁还待他人一笑。江月笑若莲花,醉卧于我们的王怀中,衣襟半掩,身如水蛇,游移不定,教王如何也追不到,若即若离便是如此写成。
我们的王眼神涣散,笑容只为她一人而展。此时的她,已是南宫当家,卫贵妃。自南宫主母之位空悬许久后,我们的王才注意到了这个有着婀娜身姿,多才多艺又娇小玲珑的江南女子卫子夫。待他尝尽美人恩之后,他许诺她,让她做这南宫主母之位。朝中重臣无人反对。
我们的王为她造了琼楼玉宇,楼台水榭,任凭夏天的风如何粘腻,这南宫永远一片春光,清爽如夜。
----------我是无奈的分割线------------
现在的我,已堂而皇之悠然的站在这大殿之上,与江月一起,追逐嬉戏,发疯似的叫嚣着。入宫以来第一次我们如此挥洒汗水,如此痛快畅饮,如此肆无忌惮。那些之前眼高于顶的婢女宫吏们,现在被我们任意呼来喝去,我想,此时我已满足,即使就这样死去,也无憾。
还记得那个寒冷的夜,我们坐在北宫大殿石阶之上,陪伴我们的仅是刺骨寒风呼啸而过。尽管如此依然浇不熄我们的高瞻远梦。你说:“若能腾达一次,也不枉此生。”
我气喘吁吁卧倒在软榻上,一转首,对上江月双目。我们相视而笑。凤塌如此舒适,以至于让我如踩云端之上。这里到处都是奢侈品,珠光宝器。琉璃珠帘把闺房与外界阻隔,漆红大橱内数不尽的凌罗绸缎,红木梳妆台上堆满了方才我们的王赐予的珠宝,价值连城。窗柃上的图腾巧夺天工,绘出九龙戏珠,双凤弄舞,鹊鸟朝歌。外院的水榭旁尽是夜光珠,照亮了整个南宫,穷极奢侈,仅为讨一人欢喜。
她问我:“那次你救我,你想过死么?”那次有多少曾经在她耳边软言细语,款款深情的人仍避不了的落荒而逃。情谊在此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想过。”我闭眼,我怎可能未曾考虑到面对生死?那次我奋不顾身之举现在想来仍是心有余悸。若不是秦生挺身相助。我们早已身首异处,为地下亡魂了。“可你是我至交。我们说好生死同亡。”
她竟有些哽咽,说的辞不达意:“你真是……我怎消受的起。你教我如何报答你。”
“赐我黄金万两如何?”我笑的花枝乱颤。她亦破涕为笑。
她突又想起什么,将我一把拉起……摆出一只只银盒。她打开所有盒子,无数珍宝争奇斗艳似的在我面前熠熠生辉,赤橙黄绿青蓝紫,刺的我双眼生疼生疼。“风妹妹,随便挑。”她手一摊,对我毫不保留。
我把所有东西都往前一推,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们的友谊。我不希望因这宫廷恶斗淹没了我们的友谊。”
“现我有势,我定为你找个好郎君,让你一辈子幸福。”她由衷道。
“有权有势吗?”我笑的苦涩。为权为势,谁人不是削尖了脑袋攀龙附凤,踏着他人的尸体往上爬。情深意重的郎君少之又少。当初单纯的黎涧,为仕后眼神是多么的污浊,蒙蔽双眼也不自知。
今日江月的地位何尝不是拿着遮羞布换来的。
“我好想回到过去,金陵的生活虽然清苦,却如此无忧。”那些文人骚客如何的无耻,也不及这朝廷的万分之一。小小伎俩便能报复的快感在这里再也行不通。
“我们已走至此,怎可能全身而退。殿内殿外有多少人不是想尽了办法想把我们拉下水?”
我们沉默许久,夜色渐渐深沉,直至东方吐露淡色亮光,我们依然侃侃而谈,无视劳累渗透我们的身躯。
“那南方的红色顶梁,是夫君上朝的大殿,卧龙殿呢。”她遥手直指远方。我只能迷起眼努力的看着晨雾迷蒙的那个方向,大片红色隐约可见,我却猜不透那是何处。
庭院里的夜光珠还在卑微的发出暗淡的光泽,眼看快天明。“你不睡么?”我问她。
她遥首。殷殷的看着南方。痴情女子。
----------我是无奈的分割线------------
此时我已长住南宫。江月将我自陈皇后那边要了过来。她知我们是至交,便也不为难。只道:“若念旧情,有空就来陪陪本宫。”她依然是如此柔弱的女子。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她艰难的支撑着。她不愿与人为敌,只想宁静的生活,为夫君燃起一小片亮光,脉脉相待。
昨晚我与江月通宵达旦的闲聊着,直至天际渐亮才闭眼。晌午的阳光直射入寝房,迫使我不得不睁开眼,才知窗柃已被人打开。我望向来人,才知是秦湘郡。自从淑妃入天牢至今,我们未曾见过。我不知她怎会来此。她笑意连连,猜不透她来意。此时的困顿因她的不请自来而消失殆尽。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向她跪安后,待她开口说明来意。
我们互视许久,她才道:“且风,皇上说要你嫁给我的七皇兄,问你是否愿意。”
听闻这消息后我犹如五雷轰顶般炸响了我的五脏六腑,我以为她只是一时玩笑而已。可我分明看到她的眼中有着千万个不情愿,我知她依赖他,敬仰他。却才知她如此需要他。以至失去他时她心有不甘。我与秦生并无交集,若嫁了他,一生幸福毁于一旦。我们将会相敬如宾,至死他也不会看我一眼。
我疑惑的看向她,她道:“我怎可能拿这种事来玩笑!”
我突然感慨万千,自己的终身竟要交于毫不相干的人做主。我笑。如此的身不由己。我问她:“我有选择的余地吗?”圣旨一出,我能说不吗?
她似是明了了一般,说:“皇上决定的,既出此言,决不悔改。”
她如此年轻,能知道什么叫婚姻么?并非两人日日相对便是婚姻,宫廷更是繁复,婚姻意味着笼络,意味着牵拌。他会将我看成是这桩婚姻的牺牲品,他不会怜香惜玉。
我绝望。此时殿外有太监尖锐的嗓音响起。我知我们的王已来到南宫。我与秦湘郡在门侧迎接。
他进了门,身姿挺拔,朝服还未换下,想必是与臣子商议朝事后直接来南宫的。他利落撤走所有人,包括秦湘郡。她走时心不甘情不愿,将门扉重重摔上,以示抗议。
此时屋内又安静下来,只有夏蝉叫个不停。首次与我们的王单独会面,他身上并没有沉迷酒色而残留的胭脂水粉香味,而是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