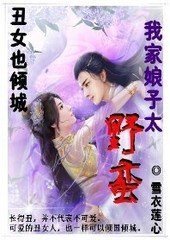美人计:倾城妃子平天下-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易乎世,不成于名。”他望着我洒脱的笑着,“我还是我,不必为世情改变自己的初衷,也不必为虚名来断送我的追求。‘勿用’不是不用,而是伺机而发,备而后用。记不记得我对你说的,当你学会了忍耐与承受,你就会成为那把最锋利的剑。”
我从心底折服于他的言论,叹道:“我明白了,欲成事者,必须学会潜藏隐忍,厚积薄发。”
他清然微笑,已轻轻松开握紧我的手,赞许地点头道:“你说的不错。如今世间战云迷乱,四星未现,紫微不出。你要学会做这水,水总是潜伏于最低处,却能承载万物;它最柔弱无骨,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却能颠覆万里九州。心如水月,百炼钢亦能化做绕指柔,这才是天下最锋利的剑。”
我不料他又将话题引向我,才知道他并不想多说自己。毕竟,他是一个才德不愿外漏的人。从小到大,除了父亲偶尔会提点我一两句,再没有人像他这么对我谆谆教导。
望着一湖澄净的碧绿,我不禁垂首陷入沉思。不错,我要像水一样,学会忍耐与承受,忍耐冰寒的乱世,承受我应负的责任。
我蓦地抬起头,对刘基说:“多谢先生指点。过几天,我想出山一趟。”
他眉头微微耸动,面上却只微笑着调侃:“刚劝你不要急,你却要走。也罢,女大不中留。”
我脸上辣红,解释道:“并不是我要走,只是,马上就是我父亲的生辰,我想在他坟前烧一炷香。不瞒您说,在他生前,我从未好好孝敬过他,甚至曾犯过大错。我心中有愧,总是不敢面对他。今日经先生一番开解,我想无论对与错,罪与责,我都必须去承担面对,而不是逃避。”
他英眉舒展,笑道:“久居山中,许久不曾在外间走动了。携美同游,想必会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只是打算自己前往,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此刻微感窘迫,低声道:“先生,先生也要去吗?”
他朗声笑道:“怎么?阿薇果真嫌弃我这个糟老头子!”
我急忙道:“不是不是!先生于我如师如友,是天底下我最敬佩的人,我怎么会……先生要去,咱们一同去便是。”
他微微一愣,复而笑道:“你如今剑锋未成,你我既然相识一场,我怎能放心让你一人独自出门闯荡。我愿意,孝孺也不会愿意。”
我感激地望着他,真切道:“多谢先生。”
“别总先生先生的叫我,听着多生分。好像我真成了一个糟老头子。”他甩了甩袖子,宽大的白色衣袖夹着菊花酒的清芬拂面而过,让人禁不住在月色中沉醉。
我不好意思,不叫先生,叫什么,难道直呼其名?还是叫他的字伯温,他比我大一辈,我又怎好这样唤他。犹豫半晌我终是为难的叫不出口,只呆呆地立在原地。
刘基见状,纵声而笑,那笑声穿过暗夜的沉寂,在飘渺的山林中回荡。
我从未听过这般爽朗的笑声,这般掩藏了深深悲切的爽朗的笑声。我几乎错疑那个夜晚最初的时候,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失神与落寞是我一厢情愿的妄加猜测。事实上,多年的潜藏与隐忍早就让他化作如水般温润又飘洒的流波,谁又会知道那澄明光洁的波痕下面掩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
有时候,经年的痛苦犹若水底招摇的水草,一面柔情地安抚你渐渐寂寥凉薄的心事,一面疯狂地痴缠着你不忍回顾的记忆。你既不忍割却,又不愿停步,只得将头探出水面,挥舞着双手伪装成迎风展露的白荷,哪怕这风的到来是为了舔舐你残存的青春念想。
他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爱笑的男子,却也是最悲哀的男子。
决绝的凄美,正是他展示给我的第一种生命之美。恍如杯盏里的菊酿再也回不了最初的柔嫩花瓣,我们也回不了最初的风华。
第二卷,水之卷:朱雀南飞 (六)野蔓有情萦枯骨,残雨何意落孤山 上
临安位于杭州路,与青田相隔不远,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宫城在城南端,斜倚凤凰山东麓,周长九里,城墙夯筑,分外巍峨厚重。
这次出山的,仅仅是我和刘基二人,小方并没有跟来,那是因为他这几日正痴迷于《春秋》里的缤纷世界。难得他如此好学,我也不愿扫了他的兴致,便不做勉强。
当我们到达临安的时候,天空中飘满了纷纷扬扬的小雨。
细细密密的雨不着痕迹地沾湿了旅人的青衫,也沾湿了眼前沧桑的老城。古老的高墙只是静默的矗立于风雨中,犹如一个久经风霜的老者,仅仅顺着细雨轻叹一声,枯荣的故事便已被他围在了前朝旧梦里。
此时正值午时,从城门口遥遥望去,里面行人车马络绎不绝。到底是历尽数朝风雨的大城市,国虽破,城犹兴。
只是,苍然的历史赋予了它与繁荣恰恰相反的萧索意味。我瞻仰着这座曾经昭示了赵氏王族所有荣耀与耻辱的古城,血液随着那些曾经的古老故事而悄然沸腾,心中升起一股难言的悲凉之意。一个城市如若没有它的灵魂,再繁荣,也只是一个浮华的躯壳。没有王族的朝阳照耀,余下的仅是凄雨傍绕的孤漠。
“我们先进城找一个歇脚处吧。”刘基的提醒让我从没落王朝的自怜自伤中迅速抽离。
我点点头,恍然发现他惯有的笑容中隐匿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而这份淡然的忧伤,在我告诉他父亲葬在临安时就已经初露端倪。
我无从想象古老的临安城与他深藏的故事究竟有何关联,但那忧伤越是淡然,就越让人觉得深入骨髓。
他仿佛极熟悉这座城市的一切,他带着我径直走向一座酒楼,名为杏雨楼。
坐在二楼窗边,望着轻灵的雨滴顺着屋檐滴滴旋落,我赞道:“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地方真是雅致,名字也极好。”
他闻言似乎也颇有触动,轻叹一声,道:“年轻时,我曾应召任职江浙儒副提举,有一次因公来临安办差,就为这里的杏雨所沉醉。”
他说着,举目遥望着楼下深深浅浅的水洼,仿佛要从中寻找他已然远逝的青葱年华。
我瞧他不觉伤感的模样,只得假作愉快地开解道:“雨景虽美,但如今毕竟是夏日。你瞧,这里哪儿还有卖杏花的丽人呢!”
“不错,”他黯然道:“哪里还有呢。”
我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他神情愈发恍惚。我正踟蹰间,一声娇叱突兀地荡漾在整座酒楼。
“刘基,你也敢来临安城!”
我不禁蛾眉微蹙,诧异地望着刘基,他的脸色倒是淡然从容,仿佛楼下那人喊的并不是他的名字。
这时,一个蒙古装束的红衣女子气冲冲地奔上楼梯,她一眼就看见了刘基,扬起手中的赤色长鞭,直指他,喝道:“方才听巴根说看到你,我还不相信。原来真是你,你倒是有脸;还带着一个女人来。”
刘基摇头叹道:“阿茹娜,你还是这样的烈脾气。”
这次因为有刘基陪在身边,我没有再着男装,没想到又惹来麻烦。我诧然地望着那女子,一朵朵愤怒之花盛开在她娇俏的鹅蛋脸上,与她的一身红衣倒是映衬。
她快步走来,愤怒地瞪着我,转而霍然一惊,呆立在原地,喃喃道:“乌兰……”
那声音极细极轻,仿若窗外纷扬的雨落,却重重击在我的心头。
我询问地望向刘基,刘基淡然道:“这位是阿薇,是我的朋友。多年不见,既然来了,就一同坐下说话吧。”
阿茹娜不说话,神情复杂地走向我,那眼光似是利刃般一道道地剜着我的血肉之躯,好像要从我的身体里挖出另一个灵魂。
我实在不适宜她这灼人的目光,微微偏过头去,看向一边。
她突然在我面前站住,茫然自顾道:“不,不是。”
“阿茹娜,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刘基脸上一贯的微笑已悄然隐匿。
她娇躯微震,转而看向他,苦涩地轻笑一声,道:“原来你是有备而来。你来做什么?”
刘基迎着她的目光,答道:“我来见一见故人。”
“故人?”她恨恨道:“我不知你口中的故人是谁,若是她,你没有资格见。若是我,更加没有见的必要。”
刘基叹息一声,却漫出沉重的意味,他道:“这么多年了,阿茹娜,你何必如此?“
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此刻尴尬至极,低头饮了一口清茶,不料这个细小的动作,在这样的时刻更显得突兀。
阿茹娜看看我又看看他,忽然道:“我何必如此?你又何必如此?真是可笑,你以为找这么一个女人,就能代替一切吗?”
我被口中的茶水生生呛着,吐也不是,咽也不是,连咳几声,那模样想必狼狈至极。
“你误会了。”刘基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道:“我认识阿薇完全是一个巧合。此刻,和她在这里也是巧合。”
“巧合?”她轻笑道,“你难道没有私心?”
刘基坦然地望着她,眸子里星辉四溢,一字一字道:“没有。”
阿茹娜闻言微微颤抖,面色黯然,刘基又道:“这么多年,我一直独居于山野。”我的心意不必向你证明,也不必向任何人证明。我知道,她知道,如此便足矣。”
她?她又是谁?我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人,他们皆是一样的肃穆悲伤,沉浸在同一件渺远而沉重的往事中。而我,只是被他们思索的眼眸排除在外的一粒尘埃。
第二卷,水之卷:朱雀南飞 (六)野蔓有情萦枯骨,残雨何意落孤山 下
阿茹娜无尽凄然地太息一声,道:“这么多年,你可是后悔了?”
刘基坚定地摇头,道:“九死而未悔。我唯一后悔的是,当年没能带她走。八年的青春,我们已经错失了整整八年。你为何还要阻挡我见她?”
阿茹娜仰天闭目,一行清泪夺眶而出,她怆然道:“见她又如何?你已经永远失去她。她像春日里一朵最美的杏花,已为你绽放出所有,而你呢?你隐居八年又如何?难道这八年你不曾做过对不起她的事?上天为何如此的不公平,活着的人永远逍遥快活,死去的人却痴心空付。”
听到这里,我惊愕难言,死去的人,莫非……
“你不懂。心若相知,无论生死,都永远同根共息,就像是两株生长在悬崖上的蔓藤,生死与共,风雨与共。就算其中一株消逝了芳华,另一株也会紧紧的攀援着她最后的温存与爱意,为她抵挡身后的每一缕炙热和严寒。直到他们一同枯萎,腐败,化作坠入深渊的一粒轻尘。只有这样,才能保留爱情最坚贞的灵魂。”
坠落,或者飞翔,这是故事必然的结局。我从未想过,原来坠落也可以如此绝美,如此荡气回肠。
我不禁抬头深深望着刘基,刘基的脸上是一种近乎诡异的淡漠,我知道那才是最刻骨铭心的爱。只有超越了生死的爱,才能如此深刻地沁入他的每一寸肌肤,每一缕灵魂和每一次平凡的呼吸。
阿茹娜亦是一脸震撼,除此之外,她的眼中还多了一分哀戚,她幽幽道:“原来,原来你们想的竟是一样的。为什么她是如此的懂你,顾虑你,从生到死?”
刘基讶然,反问道:“她一定对你说过什么,对吗?”
阿茹娜凄然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整整八年,她的魂魄没有归处,她的尸骨冰寒于霜野,她已经为了你万劫不复。”
刘基突然抓住阿茹娜的皓腕,急切道:“告诉我,她在哪?”
半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刘基失控的表情。这个看似优雅而达观的男人永远操持着最成熟潇洒的笑容,而此刻,那种恰到好处的失控是一个男人心底潜伏已久的爱情之火,盛大而炙热地焚烧着每一个多情少女的渴望。
阿茹娜漠然的抽出自己的双手,道:“好,好,我让你见。也许,你早该去看看了!”
她转身走出,刘基紧随其后,只留我一人坐在原地不知所措。
谁料阿茹娜又扭头,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叫阿薇?你也来吧,来好好看清这个人!”
我愕然的站起身,刘基仿佛才记起我,向我歉然的点头示意,我只好跟着他们走。
一路上,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不言,在这种缅怀的时刻,说什么都会显得不合时宜。不知不觉,我们已步入凤凰山中。黄昏,隔一程烟雨去看山上的丛林,不过是一片繁华背后的孤寂。
我们顺着山径而上,周围是深邃幽静的世界,犹如这世间千千万万的人心。众树依着自己的性情,或占据峰顶,或落籍于深林,彼此相安无事。我突然有些羡慕这些树,如果人活着也能像它们一般随性,那该多好。
眼前豁然开朗,崖风拍岸,卷来阵阵青蔓特有的洁净芬芳。
我不禁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叹不已,在山雾漫散的崖边,有一条细茎的蔓藤,小心翼翼地匍匐着向另一株已然枯黄的老树缠绕爱抚。它通身挂满葱绿的叶子,以一种三跪九叩的姿态虔诚地深入枯树的每一寸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