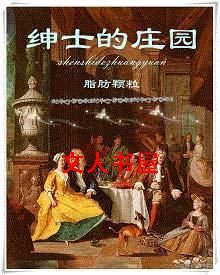高老庄-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所长走,西夏瞧见路上有一摊稀乎乎的牛粪,晨堂就踩上去,臭气哄地散开,苍蝇也飞了来,两个警察就放开了晨堂,让他自个儿走。土场上,站着了许多面如土色的人,在他们的身边是一大堆横七竖八的木头。西夏看见了有秃子叔,有狗锁和他的婆娘竹青,有来正,还有牛坤和庆来,庆来拿着一片子锅盔在吃。朱所长在大声训话,夹杂着十分难听的骂,然后喝问谁还砍伐过林子,是自动交出来还是让挨家挨户去搜,如果不自动交出来而被搜出来,那么就轻者罚三百元重者刑事拘留。便有人回家去把藏在家里的木头扛来了,除过银秀的那个男人领了警察去那孔废弃的砖瓦窑里抬出了一棵大树,又叫嚷他是藏了两棵的怎么成了一棵,另一棵是哪一个不要脸的又偷走了,西夏没有想到的是,主动交出木头的多是些老头和孩子,又都是一些细椽,碾杆一类的小木头,三婶也把那根做檐笸用的小树干扛来了。迷胡叔是坐在木头堆前大声地哭,拿他的头在木头上撞,他检讨着自己贪嘴,在蔡老黑家喝醉了,没能守住林子,如果他守在林子边,谁也不敢来的,为了集体的林业资源,他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竹青却说:“迷胡叔你多亏喝醉了酒,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着什么,恐怕你被捆在树上,狼吃不了你,蚊子也把你一夜叮死了!”迷胡叔说:“我死了也是为革命死的,死得重如泰山!”众人忍不住笑了一下,脸又铁青着,狗锁就啪地搧了竹青一个嘴巴,骂道:“你话这么多,不说话别人以为你是哑巴?!”竹青的脸立时起了五道红印,她愣住了,众人连同警察也愣住了,但她饿狼一样扑着了狗锁,两人撕打开来,谁都想一下子把对方治服,却治不服,突然间狗锁就倒在地上,捂着交挡哎哟。众人一时骚乱叫道:“抓着X蛋了!”朱所长大吼了一声,土场上立即安静下来,他要人们供出谁是这次哄抢事件的带头人,如果都不开口,就谁也不能走!迷胡叔就说:“一定是顺善起的头,他是党员!”朱所长说:“你住嘴!”迷胡叔噎住了,却又说:“不是顺善起头又是谁,他要陷害我哩!”又扑倒在木头上哭起来。
一个警察已经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各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下列清了砍伐的树木的大小粗细和件数,然后挨着让蘸了红油泥去按指印,他们大概觉得事情真有了严重性,先是说看见蝎子腰的人去砍伐了他们才去的,后来就说看见了你去我也才去的,你又说看见他去才去的,争争吵吵,末了就对骂开来。而朱所长却坐了下来,开始把手枪部件拆开,又组装,再拆开,再组装,天太热了,大盖帽卸下来放在了木头上。西夏决意要离开土场,她拍打着屁股上的土,从朱所长的面前走过,朱所长看了看她,她也看了看朱所长,一步跨过了另一堆牛粪,回家去了。
石头坐在了院门的门槛上,他对着西夏灿烂地笑。自西夏回到高老庄,石头还没有这么微笑着对待她,西夏立即就回报了微笑,石头说:“姨,这树上有蛇吃过鸟哩!”西夏说:“你叫我姨?!”立即俯下身抱住了石头,眼里几乎要有泪水了,说:“哪棵树,蛇在哪儿?”石头指着门。孩子把门不叫门,叫树,孩子看到的是根本的东西,但做门的这棵树怎么就能看出曾经爬过蛇,而且蛇吃过小鸟,西夏觉得离奇不已。在高老庄,西夏也是遇到了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怪事,是因为也受到了石头的什么影响呢,还是这一块土地使她发生了变化?西夏说:“怎么看见门上是有过蛇呢?”但石头却并没回答她,手脚并用地从门槛上往院里爬,那棵樱桃树梢上静落着一只白粉蝶,树亭亭临风如人,像是车站上遇见的王文龙的前妻。
第三十一章
这一天里,派出所共抓去了二十人,关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小平屋里,无法睡下也没法坐下就那么面对面地站着,我呼出的热气你吸,你呼出的热气我吸,汗臭脚臭口臭屁臭,臭气熏天。小平屋里不送饭和水,小便就轮换着到前边门缝,尿水如小溪一样一直在流,大便就苦了,先是有人掏出纸或手巾铺在那里,大便在上边了,提着纸和手巾的四个角儿从门缝扔出去,后来没有了纸和手巾,就撕自己的衣服,但门缝外的屎尿却堵起来,空气越发恶臭,有人就歇斯底里地呐喊,用头撞墙。镇政府召开着会议,以朱所长的主意,立即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将这些人送往县公安局收审,但吴镇长却宽大为怀了,说:“朱所长,派出所的经费不是特别紧张吗,每人罚上三百元,怎么样?”朱所长有些吃惊,因为天未明是镇长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责令他立即到太阳坡去制止毁林事件,严惩不法农民的,现在人犯抓起来了,仅仅是罚个款就了事了?朱所长说:“你的意思?”吴镇长的意思是他绝没有想到太阳坡的林子被毁得如此严重,也没有想到参与毁林的人如此多,这样恶性事件的发生,虽然与镇政府没直接关系,却也极大危害了镇政府的政绩,县上正筹备着召开人大会议,他吴镇长已内定为七个副县长候选人之一,若将事件呈报上去,必然震动全县,那么他在参选时还能被选举上吗?吴镇长的意思当然不能讲的,他说:“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嘛,发生这样的事件说到底还是农民穷么,如果把他们判刑坐牢,那二十个家庭就更贫困不堪了,咱们做地方领导的,其实也就是土地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他讲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一个道理,开始为在基层做领导的难处发牢骚,他举中国的戏剧里县官的形象总是丑角,为什么是丑角,因为他们与老百姓近么,做好事是他们,做坏事也是他们,老百姓要骂皇帝是骂不上的,骂州官也是骂不上的,所以什么事要骂就骂县官。但现在县官已不是最基层的官了,乡镇一级的领导在第一线,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他们屙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坐天下,那些国民党政府做大官的人可以安全无恙,还能继续在共产党政府里做官,国民党政府里那些乡长镇长呢,一半却被杀头了,一半没有被镇压的却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为什么?他们民愤大呣!吴镇长说:“为什么他们的民愤大呢?”他提问那儿位副镇长,提问朱所长。副镇长和朱所长没有回答,因为一是他们明白吴镇长说话的含义而又用口无法说出,二是吴镇长的讲话有自问自答的习惯,但吴镇长一挥手却说:“不说了。”朱所长的年龄并不大,但上腭的四个牙却是装了假的,他用舌头把假牙套顶下来,又用舌头顶着装上去,又顶下来,再一次装上去,说:“我同意吴镇长的意见。”几个副镇长也就说:“同意。”镇党委副书记是个老者,他没有表态。吴镇长说:“老袁,你说呢?”老袁说:“你是党政一把手,我听你的,只是咱要考虑……”朱所长却说:“吴镇长,你是说过了的,派出所的经费确实紧张,罚款的钱政府就不要再抽去一部分。”吴镇长说:“好吧好吧,你们吃肉就看着我们喝汤吧!老袁你说要考虑的是什么?”老袁说:“如果咱们不上报,这么大的事情一时是可以捂住,日子一长,难免不会被人捅出去,如果被捅出去,有些人会不会借题发挥呢?你是镇长,又是党委书记……”吴镇长勾了头沉思了从口袋掏出个小铁夹子,在下巴上拔胡子,拔一根粘在桌面上,又拔一根粘在桌面上,粘到第四根了,他决定立即去把蝎子尾村,蝎子腰村,蝎子南北二夹村的村委会负责人和一些有威望的老者叫来开会,群策群力,集体解决。
顺善自然是被请之人,他果然老谋深算,建议道:要让事情没有后遗症,不如将这片林子以自留山的形式分给各村,各村再分给各户,原本实施责任制的时候这片林子应该分的,但因当时林子面积大,树木还小,担心分掉后被毁才以集体的名义留下来的,如今林子已经毁了,从档案里抽出当初的决议,分给各家各户,即使有人追究,那是私人的林子任私人处理,谁也怪不上村委会和镇政府了。顺善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关在派出所平房里的二十人就释放了。这些人一出来,立即扑向了派出所院中的水管前,咕嘟咕嘟只是喝水,秃子叔喊:“喝慢些,喝慢些!小心把心激炸了!”他端起了一盆水照每个人头上身上泼,但扑到水管前的人喝个没完,扑不到水管前的就日娘捣老子骂。晨堂在屋角里靠墙睡着了,跑出来迟,见挤不到水管前去,竟端起了朱所长宿舍台阶上的一盆洗过脸的水就喝起来,直喝得肚子像气虾蟆,才哐啷丢了盆子,四脚拉叉地躺在那里,说:“来正,来正,你说世上啥最受活?”来正没有喝上水,却被秃子叔浇得头湿湿的,以为晨堂想他的竹叶婆娘了,说:“XX最受活!”晨堂说:“还有呢?”来正说:〃X毕了,歇一会儿再X!”晨堂气得坐起来说:“你都渴死了还有劲干那事?!”
在南驴伯的坟上,工匠是茶坊镇的人,也有高老庄的人,但帮工全部是高老庄的,庆来被抓去关了一天,子路只好在那里招呼。高老庄的工匠和帮工很庆幸他们没有参与毁林事件,估计着被抓去的人谁可能判三年,谁可能判一年,谁可能监外执行,这多半天里都很卖力,吸烟的时候就把烟吸得一点不从口里鼻里漏,唠叨坐牢是不怕的,最怕是坐了牢不能吸烟。但半下午被抓去的人突然放了,他们似乎觉得有些遗憾,议论着谁谁并没有把砍伐的木头全部交出来,就埋怨他们来修墓了错过了一场好事,干活也不大出力了。直到天黑回来吃饭,庆来来了,子路叙说了坟上的议论,庆来说:“你明日歇着,我去招呼,咱是掏钱雇工的又不是请爷哩,谁不好好干重换人么,能出力的人有的是!”子路忙劝他不要发火,乡里乡亲的别伤了和气。庆来说:“我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哩!”他就端了饭碗过去说:“石祥,你以为错过了一场好事吗,我坐了多半天黑房子,还得罚三百元,你小子沾了我伯的光了,要是不修墓,这二十人中有你就没有我,听说你好吃好喝着还撂风凉话呢?”那个叫石祥的赶忙说:“哪里说风凉话了?给南驴伯修墓哩,甭说罚三百元,就是去白领三百元我也是不去的!”庆来说:“那好,明日墓上还缺几百砖,一早起来你和我一块儿去窑上往回担!”石祥说:“雇一辆拖拉机拉么。”庆来说:“几百块砖用得着拖拉机,咱担!”石祥说:“那墓修好了,我睡进去得了!”众人就笑,说:“累不死你的!”石祥说:“要是累不死也得多吃些饭吧,那我就去盛第三碗面啊!”
第二天,墓地里将砖墓全拱了起来,只剩下修饰墓门面了。这一天,太阳坡划分给了各村各户,残留下来的小树被主人们点了数,在这家与那家的地畔上,又分别在树上系了红绳儿或刮出一点儿皮用红油漆标了号。迷胡叔自然是失业了,自然再也拿不上那每月十几元的护林费了,他夹着胡琴来到了墓地,说他也为南驴伯的新屋建设出点儿力呀,就坐在墓边拉胡琴,咿咿呀呀唱那“黑山哟白云湫,河水哟往西流……”唱着唱着就骂顺善是他的敌人,给子路诉冤枉。
晚上吃毕了饭,商量明日墓上的事,修饰墓门面只能留下能画的张师傅,别的工匠和帮工就得辞退,庆来因要陪张师傅去镇上商店去买颜料先走了,子路就给那些辞退的人算工钱。但这些人却要求加钱,理由是施工中赶得紧,原本是七天的活四天就完了,人出了多大的力,而茶饭不好,烟供得少,酒也只喝了三次。子路就生气了,说你们在家都吃什么了,顿顿米饭蒸馍又炒四个菜还不可以吗?那个摔断木尺的工匠就说墓穴的风水硬,把他的木尺都摔断了,风水硬肯定对修墓人不好,这些自认倒霉,但总得赔偿他的木尺呀!子路觉得这有些欺负人,偏不给赔偿,工匠们就红脸吵起来,还是西夏来掏出二十元钱交给了那人,西夏说:“尺子值多少钱你不用找了!”那工匠偏从口袋掏出二角钱来放在地上,说:“我是穷人,可我不多要你们一分的!”为这事,子路着了一口闷气,回到家叫喊心口疼。西夏就数落他太小气,一个大教授了为那二十元钱吵吵嚷嚷值不值?子路说:“你不了解农民!”西夏说:“我了解你!”两人也恼起来。
这天夜里,天快亮的时候,西夏又做了一个梦,醒来还清楚地记得,她吃惊的是梦见了石头的舅舅背梁,背梁是辱骂过她的,但背梁在梦里却向她赔不是,她看见背梁猥猥琐琐的样子,一边擦鼻涕一边说:“我要死了,你原谅我吧,我拿钱赎我的错。就从身上掏出十二元三角四分钱要给她,她说不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