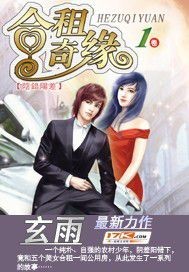镜花缘-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人匆匆出了小巷,来至大街。林之洋见他二人举动怆惶,面色如土,不觉诧异道:“俺看你们这等惊慌,必定古怪。毕竟为著甚事?”二人略略喘息,将神定了一定,把汗揩了,慢慢走著,多九公把前后各话,略略告诉一遍。唐敖道:“小弟从来见过世上竟有这等渊博才女!而且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多九公道:“渊博倒也罢了,可恨他丝毫不肯放松,竟将老夫骂的要死。这个亏吃的不小!老夫活了八十多岁,今日这个闷气却是头一次!此时想起,惟有怨恨自己!”林之洋道:“九公:你恨甚么?”多九公道:“恨老夫从前少读十年书;又恨自己既知学问未深,不该冒昧同人谈文。”
唐敖道:“若非舅兄前去相救,竟有走不出门之苦。不知舅兄何以不约而同,也到他家?”林之洋道:“刚才你们要来游玩,俺也打算上来卖货,奈这地方从未做过交易,不知那样得利。后来俺因他们脸上比炭还黑,俺就带了脂粉上来。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觉丑陋,都不肯买,倒是要买书的甚多。俺因女人不买脂粉,倒要买书,不知甚意。细细打听,才知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唐敖道:“这是何故?”林之洋道:“他们风俗,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才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他配婚。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闻得明年国母又有甚么女试大典,这些女子得了这个信息,都想中个才女,更要买书。俺听这话,原知货物不能出脱,正要回船,因从女学馆经过,又想进去碰碰财气,那知凑巧遇见你们二位。俺进去话未说得一句,茶未喝得一口,就被你们拉出,原来二位却被两个黑女难住。”唐敖道:“小弟约九公上来,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
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去了!”多九公道:“起初如果只作门外汉,随他谈甚么,也不至出丑,无奈我们过于大意,一进门去,就充文人,以致露出马脚,补救无及,偏偏他的先生又是聋子,不然,拿这老秀才出出气,也可解嘲。”唐敖道:“据小弟看来:幸而老者是个聋子。他若不聋,只怕我们更要吃亏。你只看他小小学生尚且如此,何况先生!固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究竟是他受业之师,况紫衣女子又是他女,学问岂能悬殊?若以寻常老秀才看待,又是‘以貌取人’了。
世人只知‘纱帽底下好题诗’,那里晓得草野中每每埋没许多鸿儒!大约这位老翁就是榜样。”
多九公道:“刚才那女子以‘衣轻裘’之‘衣’读作平声,其言似觉近理。若果如此,那当日解作去声的,其书岂不该废么?”唐敖道:“九公此话未免罪过!小弟闻得这位解作去声的乃彼时大儒,祖居新安。其书阐发孔、孟大旨,殚尽心力,折衷旧解,有近旨远,文简义明,一经诵习,圣贤之道,莫不灿然在目。汉、晋以来,注解各家,莫此为善,实有功于圣门,有益于后学的,岂可妄加评论。即偶有一二注解错误,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即如《孟子》‘诛一夫’及‘视君如寇仇’之说,后人虽多评论,但以其书体要而论,昔人有云:‘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当日孔子既没,儒分为八;其他纵横捭阖,波谲云诡。惟孟子挺命世之才,距杨、墨,放淫辞:明王政之易行,以求时弊;阐性善之本量,以断群疑;致孔子之教,独尊千古。是有功圣门,莫如孟子,学者岂可訾议。况孟子‘闻诛一夫’之言,亦固当时之君,惟知战斗,不务修德,故以此语警戒,至‘寇仇’之言,亦是劝勉宣王,待臣宜加恩礼:都为要求时弊起见。时当战国,邪说横行,不知仁义为何物,若单讲道学,徒费唇舌;必须喻之利害,方能动听,故不觉言之过当。读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自得其义。总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实出孟子之力;阐发孔、孟之学,却是新安之功。小弟愚见如此,九公以为何如?”多九公听了,不觉连连点头。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
话说多九公闻唐敖之言,不觉点头道:“唐兄此言,至公至当,可为千载定论。老夫适才所说,乃就事论事,未将全体看明,不无执著一偏。即如左思《三都赋》序,他说扬雄《甘泉赋》‘玉树青葱’,非本土所出,以为误用。谁知那个玉树,却是汉武帝以众宝做成,并非地土所产。诸如此类,若不看他全赋,止就此序而论,必定说他如此小事尚且考究未精,何况其余。那知他的好处甚多,全不在此。所以当时争著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以此看来,若只就事论事,未免将他好处都埋没了。”
说话间,又到人烟辏集处。庸敖道:“刚才小弟因这国人过黑,未将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时一路看来,只觉个个美貌无比。而且无论男妇,都是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光景,倒象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来的。细细看去,不但面上这股黑气万不可少,并且回想那些胭粉之流,反觉其丑。小弟看来看去,只觉自惭形秽。如今我们杂在众人中,被这书卷秀气四面一衬,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与其教他们看著耻笑,莫若趁早走罢!”三人于是躲躲闪闪,联步而行。一面走著,看那国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觉无穷丑态。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紧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紧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
只好叠著精神,稳著步儿,探著腰见,挺著胸儿,直著颈儿,一步一趋,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这才把腰伸了一伸,颈项摇了两摇,嘘了一口气,略为松动松动。林之洋道:“刚才被妹夫说破,细看他们,果都大大方方,见那样子,不怕你不好好行走。俺素日散诞惯了,今被二位拘住,少不得也装斯文混充儒雅。谁知只顾拿架子,腰也酸了,腿也直了,颈也痛了,脚也麻了,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舌也燥了,口也干了,受也受不得了,支也支不住了。再要拿架子,俺就瘫了!快逃命罢!此时走的只觉发热。原来九公却带著扇子。借俺扇扇,俺今日也出汗了!”
多九公听了,这才想起老者那把扇子还在手中,随即站住,打开一开观看。只见一面写著曹大家七篇《女诫》,一面写著苏若兰《漩饥全玑》,都是蝇头小楷,绝精细字。两面俱落名款:一面写著“墨溪夫子大人命书”,下写“女弟子红红谨录”;一面写著“女亭亭谨录”。下面还有两方图章:“红红”之下是“黎氏红薇”,“亭亭”之下是“卢氏紫萱”。
唐敖道:“据这图章,大约红红、亭亭是他乳名,红薇、紫萱方是学名。”多九公道:“两个黑女既如此善书而又能文,馆中自然该是诗书满架,为何却自寥寥?不意腹中虽然渊博,案上倒是空疏,竟与别处不同。他们如果诗书满架,我们见了,自然另有准备,岂肯冒味,自讨苦吃?”林之洋接过扇子扇著道:“这样说,日后回家,俺要多买几担书摆在桌上作陈设了。”唐敖道:“奉劝舅兄:断断不要竖这文人招牌!请看我们今日背景,就是榜样。小弟足足够了!今日过了黑齿,将来所到各国,不知那几处文风最盛?倒要请教,好作准备,免得又去‘太岁头上动土’。”林之洋道:“俺们向日来往,只知卖货,那里管他文风、武风。据俺看来:将来路过的,如靖人、囗跂踵、长人、穿胸、厌火各国,大约同俺一样,都是文墨不通;就只可怕的前面有个白民国,倒象有些道理;还有两面、轩辕各国,出来人物,也就不凡。这几处才学好丑,想来九公必知,妹夫问他就知道了。”唐敖道:“请教九公:……”说了一句,再回头一看,不觉诧异道:“怎么九公不见?到何处去了?”林之洋道:“俺们只顾说话,那知他又跑开。莫非九公恨那黑女,又去同他讲理么?俺们且等一等,少不得就要回来。”二人闲谈,候了多时,只见多九公从城内走来道:“唐兄,你道他们案上并无多书,却是为何?其中有个缘故。”唐敖笑道:“原来九公为这小事又去打听。如此高年,还是这等兴致,可见遇事留心,自然无所不知。我们慢慢走著,请九公把这缘故谈谈。”多九公举步道:“老夫才去问问风俗,原来此地读书人虽多,书籍甚少。历年天朝虽有人贩卖,无如刚到君子、大人境内,就彼二国买去。此地之书,大约都从彼二国以重价买的。至于古书,往往出了重价,亦不可得,惟访亲友家,如有此书,方能借来抄写。要求一书,真是种种费事。并且无论男妇,都是绝顶聪明,日读万言的不计其数,因此,那书更不够他读了。本地向无盗贼,从不偷窃,就是遗金在地,也无拾取之人。他们见了无义之财,叫作‘临财毋苟得’。就只有个毛病:若见了书籍,登时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在九霄云外,不是借去不还,就是设法偷骗,那作贼的心肠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此地把窃物之人则作‘偷儿’,把偷书之人却叫作‘窃儿’;借物不还的叫作‘拐儿’,借书不还的叫作‘骗儿’。因有这些名号,那藏书之家,见了这些窃儿、骗儿,莫不害怕,都将书籍深藏内室,非至亲好友,不能借观。家家如此。我们只知以他案上之书定他腹中学问,无怪要受累了。”
说话间,不觉来到船上。林之洋道:“俺们快逃罢!”分付水手,起锚扬帆。唐敖因那扇子写的甚好,来到后面,向多九公讨了。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见面,曾说‘识荆’二字,是何出处?”唐敖道:“再过几十年,九公就看见了。小弟才想紫衣女子所说‘吴郡大老倚闾满盈’那句话,再也不解。九公久惯江湖,自然晓得这句乡谈了?”多九公道:“老大细细参详,也解不出。我们何不问问林兄?”唐敖随把林之洋找来,林之洋也回不知。唐敖道:“若说这句隐著骂话,以字义推求,又无深奥之处。据小弟愚见:其中必定含著机关。大家必须细细猜详,就如猜谜光景,务必把他猜出。若不猜出,被他骂了还不知哩!”林之洋道:“这话当时为甚起的?二位先把来路说说。看来,这事惟有俺林之洋还能猜,你们猜不出的。”唐敖道:“何以见得?”林之洋道:“二位老兄才被他们考的胆战心惊,如今怕还怕不来,那里还敢乱猜!若猜的不是,被黑女听见,岂不又要吃苦出汗么?”
多九公道:“林兄且慢取笑。我把来路说说:当时谈论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们不知反切,向红衣女子轻轻笑道:‘若以本题而论,岂非“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么?’那红衣女子听了,也笑一笑。这就是当时说话光景。”林之洋道:“这话既是谈记反切起的,据俺看来:他这本题两字自然就是甚么反切。你们只管向这反切书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们被这女子骂了!按反切而论:‘吴郡’是个‘问’字,‘大老’是个‘道’字,‘倚闾’是个‘于’字,‘满盈’是个‘盲’字。他因请教反切,我们都回不知,所以他说:‘岂非“问道于盲”么!’”林之洋道:“你们都是双目炯炯,为甚比作瞽目?大约彼时因他年轻,不将他们放在眼里,未免旁若无人,因此把你比作瞽目,却也凑巧。
”多九公道:“为何凑巧?”林之洋道:“那‘旁若无人’者,就如两旁明明有人,他却如未看见。既未看见,岂非瞽目么?此话将来可作‘旁若无人’的批语。海外女子这等淘气,将来到了女儿国,他们成群打伙,聚在一处,更不知怎样利害。好在俺从来不会谈文;他要同俺论文,俺有绝好主意,只得南方话一句,一概给他‘弗得知’。任他说得天花乱坠,俺总是弗得知,他又其奈俺何!”多九公笑道:“倘女儿国执意要你谈文,你不同他谈文,把你留在国中,看你怎样?”林之洋道:“把俺留下,俺也给他一概弗得知。你们今日被那黑女难住,走也走不出,若非俺去相救,怎出他门?这样大情,二位怎样报俺?”唐敖道:“九公才说恐女儿国将舅兄留下,日后倘有此事,我们就去救你出来,也算‘以德报德’了。
”多九公道:“据老夫看来:这不是‘以德报德’,倒是‘以怨报德’。”唐敖道:“此话怎讲?”多九公道:“林兄如被女儿国留下,他在那里,何等有趣,你却把他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