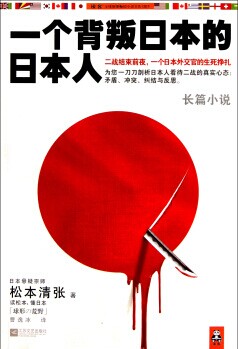忠诚与背叛-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看完第一章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异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红岩”的整个故事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要讲《挺进报》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庆为什么有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得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段历史讲起:
当时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此刻的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重庆那是还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都在那里。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毛泽东在那里,留下了光辉的《念奴娇》。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安全回到延安后,立即警告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国民党军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同志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同志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组织想继续在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他们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尤其是对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更是残酷。我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甚至常常是在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地在与疯狂而强大的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对蒋管区的党建工作有四句话:“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地下党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随时可能被捕和被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共产党员们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战斗责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的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有过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赓续,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担任为《彷徨》写“书评”的工作,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则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来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镕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联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于《彷徨》同党的《新华日报》有秘密的关系,更在于这个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红心”的内容,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原因是,自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共产党员们,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苦闷焦虑,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针对上面的种种情况,陈然等几位办刊人大声疾呼:越在此等形势下,更要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经过几天讨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