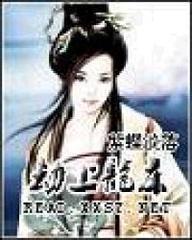龙床-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寡妇曰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古诗历来最寻常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从不曾出事,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却落得个溺死的下场。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不是宝石】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与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都不肯为善耶?”留罪之而不善终。{34}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35}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寺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心情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对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36}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被认为是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深受历代文人景仰,张信大约也是对杜诗心慕手追的一个,所以很自然地将他喜欢的一首杜诗写下来作为字帖。那确是好诗: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
此诗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语接”。张信少年得志,二十岁做了状元,正是一帆风顺之际,他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纯唯美的,而其中的忧患滋味恐怕未必领会得。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警示】经生【儒生】。{37}张信并非唯一死于腰斩这一酷刑之下的文人,还有一个受害者,名气远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坛“四杰”之一的高启。《明史》记其事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怀恨】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38}“观以改修府治,获谴”,指苏州知府魏观以原张士诚王宫旧址重建“市府大厦”,这行为本身就有引火烧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启凑热闹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内有“龙蟠虎踞”之语。这还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么人可称“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断定魏观和高启“有异图”,置于“极典”——据说,高启所受腰斩还不是一斩了之,而是“被截为八段”{39}。高启被杀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问题,其实不然。《明史》说得甚明:“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换言之,对这个大诗人,朱皇帝早已心怀不满,但不知何故暂时隐忍未发。史家多认为,“有所讽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发”的诗作,是高启的一首《题宫女图》。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此诗写了后宫某妃嫔的剪影,叙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毕由女仆扶醉而归,候至深夜,唯闻犬声的孤寂情怀。这类诗是所谓“宫怨诗”,唐以来不计其数,若论写得哀伤、凄绝的,较之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顾况等,却从不曾听说有谁掉过一根汗毛。高启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时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谈”式的宫怨诗,“触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观)之狱”。{40}清人朱彝尊的《静志居诗》甚至考证说,《题宫女图》是讥讽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启就简直“冤大发”了。
高启之外,又有名叫张尚礼的监察御史,同样因宫怨诗得罪。跟《题宫女图》比,张尚礼这首诗写得颇有些“直奔主题”:
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该诗显然化用了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是情境更为露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如此春情难耐的并非民间少妇,而是宫中某个寂寞的女人。据说,朱元璋读此诗后,深感这位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也就是说,写得实在太逼真了,就像钻到宫女心腹里去一般——对这种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蚕室死。”{41}所谓“蚕室”,宫刑、腐刑之别称;盖受宫刑者,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在蚕室似的密处,百日不遇风,方能愈合。显然,张尚礼下了“蚕室”后,没能挺过去,伤口感染而死。
“你不是操心宫女的性生活吗?我就阉了你!”这,就是朱元璋给一位宫怨诗作者的答复。旧文人赋诗为文,无非是要么谈谈政治,要么谈谈风月,谈不成政治就谈风月——这宫怨诗,其实就是风月的一种,之所以代代不绝地延传着写下来,对于士子们来说并不是抱有“妇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连给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没有,实在只是借此玩一点小感伤,扮一扮“怜香惜玉”态。这酸溜溜的小风雅、小情调、小卖弄,大家从来心知肚明,也从来没被看得太重。唯独到朱元璋这儿,作宫怨诗就会换来腰斩、割生殖器的恶果,搞得剑拔弩张,一点没有趣味和幽默感。
这里,姑且不谈专制不专制,朱元璋的反应和处置方式,确实表明他是历来帝王中少有的一个对文人文化、文人传统一无所知的粗鄙之辈。像宫怨诗这种历史悠久的创作题材,早已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而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性写作,一种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对这种心态全然陌生,竟对本来近乎无病呻吟的东西认了真,动用国家机器,大刑伺候。双方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让人哭笑不得。估计明初的文人雅士们惊愕之余,还不免一头雾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谈,但怎么风月也谈不得了呢?
一直说到这儿,我发现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与历史上其他钳制言论、烧书罪文的专制暴君,有一个本质不同: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权威,让读书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来思考和说话。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毫无建树,完全仰仗儒家政治伦理。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跟许多推行文化专制的统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还是有所不同。
朱的滥杀,主要出于自卑。表面上,他杀人,他是强者;潜入深层看,倒是他才处于弱势。这弱势的实质即是,由于特殊出身他尽管做了皇帝,却完全不掌握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那个“皇帝”,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来定义的,可对这套话语系统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释权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有一整套的语汇、语法,暗语、转义、借典、反讽、潜喻、异趣……不一而足;他们运用自如,如鱼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怜,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时常对不上话、接不上碴儿。他恼怒、羞愤、着急,怎么办?杀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强者姿态、摆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条狗,叫得越凶、情态越躁,越表明它陷于恐惧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这两个人都以多疑滥杀著称,但显然地,曹操的多疑来自于自负才高,“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强悍,朱元璋的多疑却来自于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随时在担心被文化人戏耍和瞒辱;所以,为曹操所杀者,俱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杀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写表笺的地方府学教官们。
不过,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专制主义。这件事情的进攻目标和打击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亚圣”的孟子。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这倒不是当年孟子那句“士,诚小人也”,曾让他出过大洋相。
孟子是为暴君发明“独夫民贼”这种称呼的人,他也第一个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体——民贵君轻,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这样评论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纣王这件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42}说,我只听说过人民起来诛灭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弑君的事情。谋逆杀死君主曰“弑”,“弑君”一词本身就明确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责,但孟子在纣王灭亡这件事上,根本不承认这个词。他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事都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可以作为正义而永远加以效仿。他还讲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无非两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43}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迹,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就让他下台;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迹,也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
朱元璋是什么人呢?我们对他,虽不能简单地称为暴君,但他却是把君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的人,本来就独尊独大的中国式君主霸权(试比较一下欧洲古代君权,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君权是多么彻底:在欧洲,且不说还有教权与君权分庭抗礼,即便贵族骑士阶层也能在君权之下保持某种荣誉上的独立性),在他手中发展到垄断一切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人,与孟子的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天生对立的。反过来看,孟子力倡反对“独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处吗?
以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论,他千百年来居然被专制君主们尊为圣人,里头绝对有大虚伪。在专制君主那里,他理该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该是不受欢迎的思想。我的朋友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里说,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但独对孟子坚决加以排斥,因为孟子对君主的轻视与不敬,有损天皇的权威。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君主们,虽然一定很讨厌孟子,却还是假惺惺地赞美他的思想。至少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比较坦诚,不那么虚伪。他是唯一不加掩饰、大大方方将对孟子的嫌恶表达出来的皇帝。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载: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之丁日,各有一次祭孔,称为“丁祭”】,遂命罢配享【旧以孔子门徒及其他儒家先哲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44}
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代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