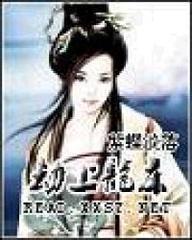龙床-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例子,是因撰写了《酌中志》而名气很大的天启、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一直蓄有胡须,《旧京遗事》记曰:“若愚阉而髯,以此自异【得意】。”{50}依理,去势之人不再分泌雄性激素,作为副性征的胡须是不会生长的了,但刘若愚却一直长有胡须,且颇茂盛,以至于“髯”,难怪他会“以此自异”。更有手术做得不彻底,而在体内留了“根”的,据说魏忠贤正是如此——“虽腐余,势未尽。”{51}怎么一种“未尽”法?想必是生殖器没了,但从身体到态度仍剩余一些男人特点,以至于进宫之后魏忠贤还有嫖妓的经历{52}。
我们探讨以上几种可能性,作为太监辈仍有兴趣发展自己的“性关系”的解释。不管出于何种情形,也不管这种关系或生活与健全人有多大区别,太监存在性需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十分普遍,这也不单明代独然,至少自汉代起,就有记载。《万历野获编》“对食”一条,综述甚详。它提到三种表现:“中贵【宦官】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归者,至于配耦【偶】宫人【宫女】,则无人不然。”或者在外娶妻,或者与妓女交往,或者在宫内与某个宫女结对——最后一种尤普通,“无人不然”,谁长久找不到对象,还被人看不起、笑话(“苟久而无匹,则女伴姗笑之。”)。还解释说,这种情形在汉代叫“对食”,在明代叫“菜户”,都是双方一起过日子的意思。此实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种婚姻”,虽然就像沈德符所说“不知作何状矣”,外人对其细节,诚无从设想,但重要的是,太监、宫女之间对“对食”的态度,其正式程度,与外界夫妇毫无不同。“当其讲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结合之后,彼此依存而至终老,甚至发展出极深的感情。沈德符曾在某寺亲见一位太监为其已故“对食”对象所设牌位,“一日,其【该太监】耦【偶】以忌日来致奠,擗踊号恸,情逾伉俪”。
如果魏忠贤当真“势未尽”,则大约使他在同侪之中,有相当的优势;何况他对房中术还颇有心得{53}——因为他属于“半路出家”,自宫而成阉人之时已年逾二十,有足够时间去学一肚皮男盗女娼,这是那些自幼净身入宫的太监们望尘莫及的。客氏与他结识,缘于魏忠贤给王才人——朱由校生母——“办膳”之时。一个是奶妈,一个是厨工,工作关系很近。不过,客氏已经名花有主,“对食”对象名叫魏朝,是大太监王安的亲信,负责照顾小朱由校的一切事宜,也就是客氏的顶头上司。而魏忠贤与魏朝是铁哥儿们,拜过把子。据刘若愚讲,魏朝忙于应付差事,“多不暇,而贤【魏忠贤】遂乘间亦暗与客氏相厚,分【魏】朝爱焉”{54}。在魏忠贤,是第三者插足;在魏朝,则是引狼入室。当时魏朝是小负责人,魏忠贤的身份地位远远不及,而客氏暗渐移情前者,应该不是要另攀高枝。魏忠贤的本钱是“身体好”,客氏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刘若愚对二魏的形容分别是:魏朝“佻而疏”,魏忠贤“憨而壮”。两相比较,魏忠贤更显雄性。再加上通晓房中术,一试之下,客氏于此在二人间立分出高低。对客氏一类女人来说,这比什么都实惠。
总之,客氏死心塌地转投魏忠贤的怀抱。二魏之间,则龃龉益重,经常“醉骂相嚷”。一次,已是丙夜(三更)时分,又闹起来,而且很严重,惊动了朱由校。这时朱由校刚登基不久。他把二魏以及七八个大太监召到跟前,“并跪御前听处分【处理】”。旁人都知道原委,对朱由校说:“愤争由客氏起也。”朱由校于是问客氏:“客,尔只说,尔处心要著【让、派、委托】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当即表示,愿意魏忠贤替她“管事”。这样,朱由校当众下达“行政命令”,魏忠贤“始得专管客氏事,从此无避忌矣”{55}。
不少人把这件事理解为朱由校将客氏“许配”给魏忠贤。这不可能。他询问客氏时用词很清晰,是“管事”。盖因宫中女人,有诸多事情自己无法办或不便办,需要托付给某个太监,实即类似找一个保护人。所谓“管事”,当系这种意思。朱由校想必知道存在这种惯例,他所做出的决定,也只是将来客氏之事,交给谁办。如果把这决定,理解成替客魏做媒,一是违反祖制,朱由校断然不敢,二来也与他跟客氏之间隐秘奇特的关系相矛盾。
种种迹象表明,朱由校与其奶妈之间,存在秘密。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直指其事曰:
传谓上甫出幼,客先邀上淫宠矣。{56}
这句话说,朱由校刚刚进入少年,亦即性方面刚刚开始发育,客氏便引诱或教习他学会男女之事。换种说法:客氏是朱由校的第一个女人。
抱阳生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士。明季史料,因为清初统治者的查禁,多有焚毁、窜改和破坏,到清中期,文网稍弛,一些劫后幸存、复壁深藏的材料,才得再见天日。《甲申朝事小纪》,就是专门搜集、整理明清之际野史文献的成果。{57}关于朱由校与客氏是否有私情,以往的叙述藏头露尾、语焉不详,这里头一次完全说破。不过,作者还是实事求是地注明了得自于传说。
真相如何,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把握。然而,有很多侧面的依据。
首先,除开未成年而做了皇帝,否则,皇帝极少有在大婚之前保持处男之身的。事实上对此没有禁令,一般来说,脱离童年后皇家继承人可以在自己宫内的范围,任意与感兴趣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这被视为将来婚育的启蒙和必要的准备。清代甚至规定,大婚之前,从宫女中选年龄稍长者八名“进御”,作为婚后性生活的实习。虽然后妃必须是处女,但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却不必是后妃。具体到客氏与朱由校的私情,这件事从制度上是允许的,虽然客氏年长朱由校二十来岁,但只要朱由校愿意,他俩私行云雨之事,完全谈不上犯忌,但也没必要张扬,这是皇家继承人有权保守的秘密。
其次,朱由校本人的反常表现。
天启元年四月,朱由校大婚。对帝王来说,大婚的意义不只是娶妻,它还意味着宫廷秩序的新建与调整。对外,皇后母仪天下,对内,则皇宫从此有了“内当家”,她负有关怀皇帝从身体健康到饮食起居的全部责任;皇帝将全面开始新生活,过去的习惯和形态应该宣告结束。简言之,大婚后,奶妈客氏不可以继续留在宫里,否则就是笑话。群臣一直在等待下诏客氏离宫的消息,然而悄无声息。
两个月后,大家看不下去了。六月二十四日,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上疏要求客氏离宫。毕佐周这道奏折,并非孤立和偶然,恐怕事先许多朝臣就此有所沟通协调,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由大学士刘一燝领衔,也递上同主题的疏文。刘一燝等没有把话讲得太刻薄,但仍写下关键的一句:“【对客氏应该】厚其始终而全其名誉。”{58}改成大白话,即:客氏应该退休,为此怎么厚赐她,给她物质上多大的好处,全没关系;重要的是,保住她的名声。虽然说得比较含蓄,聪明人也都能体会到,话里有话。
朱由校没文化,但人不笨,不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可是他仍然“顶住压力”,不肯送客氏出宫。他找了个借口,推说父亲丧事尚未料理完毕,而“三宫年幼”,颇需客氏的协助;等丧事结束,“择日出去”。{59}
用这借口,又拖了两个多月。九月中旬,光宗丧事彻底结束。刘一燝旧事重提,请皇帝信守诺言,送客氏出宫。不得已,客氏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宫。是日,朱由校丢魂落魄,食不甘味,以至饮泣。第二天,他宁肯牺牲皇帝的尊严,传旨:“客氏时常进内,以宽朕怀,外廷【朝臣方面】不得烦激。”{60}
御史周宗建,对朱由校的举动做出如下评价:“不过一夜,复命再入,两日之间,乍出乍入,天子成言,有同儿戏。”{61}侍郎陈邦瞻、御史徐杨先,吏科三位给事中候震旸、倪思辉、朱钦相也各自上疏。朱由校大怒,将倪、朱降三级、调外任。刘一燝、周嘉谟、王心一等纷纷谏阻,不听,反将王心一与倪、朱列同为罪。朝臣群起抗争,朱由校再拿御史马鸣起、刘宗周开刀,分别罚俸一年、半年。总之铁了心,谁再提客氏离宫之事,我就砸谁的饭碗。
可以说,朱由校是不惜一切,捍卫客氏自由出入宫禁的权利。他自己打出的旗号,是思念乳母,但实际要给予客氏的特权远超出这样的需要。如果出于思念,隔一段时间宣召她进宫见上一面,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反对;群臣想制止的,是客氏不受任何限制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反过来,朱由校不顾脸面、坚决打压舆论,说穿了,也不是出于慰己对乳母的思念之意,同样是想达到让客氏不受约束地随意出入宫禁的目的。他深知,这是不能退让的,一旦退让,他和客氏之间果真就只剩下思念了。
他已十七岁,早非离不开妈妈怀抱的吃奶的孩子。即便用“母子情深”来解释,似乎也大大超出了一个孩子正常的对母亲的依恋。我们很少听说一个人会以“朝朝暮暮”的表现与方式,去爱自己的母亲,倒是屡屡在热恋中的情侣身上才看见这种情态。
第三,外界的反应和解读。
朱由校与客氏的所谓“母子情深”,外界一致感到无从理解,越于情理以外。喜、怒、哀、乐、忧、惧,弗学而能。人在基本情感上,是相通的;如果是正常的情感,不会找不到理解的途径。但朱由校对客氏的情感,显然脱离了他所声称的那种范围。既然情感特质与口头标称的不一致,大家自然会依据经验对其真实性,做出自己的分辨和判断。
毕佐周敦促客氏离宫时,话就说得很不好听:
今中宫【皇后】立矣,且三宫【指一后二妃,即张皇后和良妃、纯妃】并立矣,于以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家里已经有女主人了也】,客氏欲不乞告【引退】将置身何地乎?皇上试诰问诸廷臣,皇祖【指朱由校祖父万历皇帝】册立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之后,有保姆在侧否?法祖揆今,皇上宜断然决矣。……若使其依违宫掖,日复一日,冒擅权揽势之疑,开睥睨窥伺之隙,恐非客氏之自为善后计,亦非皇上之为客氏善后计矣。{62}
话不好听,不在于“有保姆在侧否”这一句所含的讥讽之意,而在“开睥睨窥伺之隙”所暗示的东西。“睥睨”,侧目而视,有厌恶或高傲之意;“窥伺”,偷觑、暗中察看和等候。什么事情能够引起并值得外界这样?当然不是“长这么大了,还离不开保姆”——仅此不足以引起这种反应——而必是更隐秘更不足道的事。对此,毕佐周虽不着一字,但上下文语意甚明。“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宫中妇女界的秩序已经确立,陛下的身体明明有人名正言顺地来负责。这话,一下子把客氏问题提升到“谁主后宫”的高度来议论,所指系何,难道还不清楚?奶妈陪皇帝睡过觉不算什么,可一旦把这么卑贱的人摆到后宫女主人的位置上,众人可就一定是会“睥睨”和“窥伺”的。
朱钦相索性斥客氏为“女祸”,把客氏与关外女真并论,列为当朝两大威胁。他喊出口号:
欲净奴【指女真人】氛,先除女戎【戎,这里作敌寇讲,意谓客氏与女真人同为朝廷两大敌】!{63}
他称客氏的存在,“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批评朱由校“忧东奴而忘目前之女戎,所谓明不能见目睫也”,就像睫毛离眼睛最近,眼睛却根本看不到它。“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是什么意思,相信没有不明白的,所以朱由校览章也羞恼无地,斥责朱钦相“逞臆姑【沽】名”。
客观地讲,朱钦相恐怕的确属于“逞臆”,因为他不可能掌握事实;但他的猜度,仍旧符合一般人对这种情形的基本判断。刘若愚也在《酌中志》里提到,当时人们对朱由校、客氏的神秘关系,普遍存在质疑,谣言纷纷:“倏入倏出,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64}何为“非臣子之所忍言者”?无非“那种事”罢了。有人在诗里写道:“纱盖轻舆来往路,几人错认是宫嫔?”语涉讥讽,形容客氏在紫禁城的待遇和风光程度,路人遇之,几乎忘了来者是老妈子,还以为是皇帝所爱的哪个小美人呢。
《越缦堂读书记》转述的一个故事,更精彩。道是有段时间客氏跟大学士沈潅相好,为此经常出宫回到私宅与之幽会,颇冷落了魏忠贤。魏忠贤怎么办呢?也有高招。“归未旬日,忠贤必矫旨召入。”{65}列位看仔细了——魏忠贤拆散客氏与其情敌的办法,是假传朱由校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