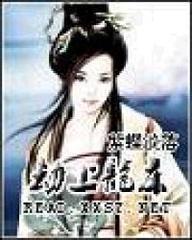龙床-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无论从经历、建树、威望、地位和实力任何一方面看,朱元璋均是千百年少见的强势君主。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起于最底层,拥有对残酷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由此磨炼出来的心理性格。
每个看过朱元璋画像{25}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张脸——《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真会说话,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它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上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它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只狠霸的大猩猩。这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盛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莫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传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坎坷下等的出身和遭际,尽管贵为人君,无情岁月的痕迹也许可以从宫廷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
前文我提到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政治的一个评价,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森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在展开下文以前,我重申孟森先生的这个观点,并再次强调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盖所谓暴君者,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得上这称号。不论朱元璋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是得利受惠的。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无论在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朱元璋如此严厉地打压官吏,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肃清吏治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疯狂的阶级报复”?因为在他的做法里头,许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夹杂着强烈个人情绪,是恨,以及伴着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宽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当忆及父母双亡、无地可葬的凄惨时刻时,他亲笔描画了使他深受伤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这记忆,有没有暗中左右着朱皇帝的心神,又如何影响了他为政?
揪出与打倒
细玩朱元璋的暴力驭吏,深感此人乃是一位天生的权术大师,他通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不可告人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惩治污吏或不法之臣只是由头,被朱元璋借题发挥,搞扩大化,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朱元璋集团”,其中,胡惟庸、蓝玉两案分别都连引至数万人。
整个明代只有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胡案后,朱元璋废相,古老的相制就此终结(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而仅有的这四位丞相,除徐达外,另三位居然全在胡案中被一网打尽,可知此案之巨,亘古未有。
胡惟庸得罪朱元璋的直接缘由,据说是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属越南)使者来贡,胡惟庸自行接见而未奏闻,然而,占城贡使却被一个太监遇见了,朱元璋由是知此事,大怒,敕责,胡惟庸等惶恐之下将责任推诿于礼部,说是他们处理不当,礼部岂能甘做冤大头,反过来坚诉与己无关。推来推去,惹朱元璋益怒,一股脑儿将中书省、礼部诸臣统统下狱,审讯谁是主使。很快,首先将汪广洋(时汪为右丞相,胡为左丞相)赐死。汪死之时,其妾陈氏自愿从死。朱元璋听说此事,命查陈氏来历,得报告说陈氏乃是某罪臣之女,其父没官后充汪妾,朱元璋再次发作,说:“没官之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竟以这个理由判胡惟庸及部臣等“咸当坐罪”。恰在此时,有两个与胡惟庸过从甚密的官员告发胡阴结武臣谋反,胡当然被诛。
然而,胡案奇就奇在,事情并不因胡惟庸死而结束,从洪武十三年诛胡,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案就像一座储量巨大的富矿,一再被深掘潜采,猛料迭爆,不断有“新发现”。先后查出胡惟庸与东瀛倭国和逃到沙漠的旧元君臣相交通,是个“里通外国”的汉奸、特务、卖国贼。洪武十八年,胡案再挖出一条“毒蛇”——李善长之弟李存义,这李存义与胡惟庸是亲家,其子李佑娶胡女为妻,举报者说李存义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计划,奇怪的是,李存义不仅没有被处死,而且得到的只是流放崇明岛这样简直应该说很轻的处罚。这种反常的处置似乎意味着什么,果不其然,又过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最后、最关键、最大的首要分子被揪出来了,那就是位列开国元勋头把交椅的李善长。李善长的揪出,真正宣告了胡惟庸“反皇叛国集团”彻底覆灭:李家“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同时有九位侯爵被打成共谋不轨的“逆党”。至此,胡案迁延十载,最终以李善长倒台及三万余人被杀而落下帷幕。
李善长,定远人,朱元璋初起时他在滁县加入朱军,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头号智囊,“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明建国,李善长更是国家体制、法律、礼仪的主要制定者。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一共只封了六人为公爵,李善长是文臣中唯一被封者,且排第一,位居徐达、常遇春等赫赫名将之前,朱元璋在所颁制词里将李直接比做汉相萧何。后为示恩宠,又将临安公主许配善长之子李祺,一时间,李善长荣耀达到顶峰,史书上说“光宠赫奕,时人艳之”{26}。
然而,这位“明代萧何”终于在他七十七岁、没几天活头的时候,被朱元璋以意欲辅佐胡惟庸谋取皇位为由除掉。李被杀的第二年,一个低级官员王国用上书朱元璋,就此事提出质疑,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如果说李本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事情还另当别论,“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27}这个推理十分有力,没有犯罪动机,何来犯罪行为?这是朱元璋无法回答的。极为蹊跷的是,狠狠将了朱元璋一军的王国用居然平安无事,朱元璋给他来了个既不作答也不加罪——莫非朱元璋有意以此方式默认某种事实?回顾胡案十年,我们发现整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巧为布置的痕迹,几乎每一次重大关节、演化,都由微细琐事而逐渐被放大,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由头,生拉硬扯,顺藤摸瓜,株连蔓引,直至搞到李善长那里方才罢休。也许存在胡惟庸试图谋反的事实,但这案情绝对被朱元璋利用了,可能胡案事发之日,朱元璋便意识到此乃剪除李善长及其势力的良机;他以惊人的耐心,不慌不忙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件钝刀杀人的杰作。
李善长被杀后三年,另一大案爆发,主人公是蓝玉。两个接踵而至的大案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一个是“老一辈政治家代表人物”,一个是“晚生代军方精英领袖”;一个被前后花了十年功夫慢慢扳倒,一个却被速战速决、突然发力瞬间击倒……朱元璋对李蓝二人所用手法,真的是无不妙到巅毫。
蓝玉崭露头角是在明建国后。洪武四年、五年,他先后作为老元戎傅友德、徐达的副手,征定西南、北漠,迅速显示其军事奇才。洪武十一年,他和另一位新生代领军人物沐英联袂出击西北,“拓地数千里”,班师封侯。洪武十四年,他以征南左副将军从傅友德出师云南,“滇地悉平,玉功为多”。此后声誉鹊起,洪武二十年,终于取代老一辈的冯胜“拜为大将军”,总领军事。蓝玉虽非开国元勋,但对明建国后武力扩张和靖宁四远居功至伟,从南到北,川滇、陕甘、塞北……明帝国最后版图的确立,与蓝玉有直接关系。《明史》说其“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徐达、常遇春之后,军方头号人物无疑就是蓝玉。
取代冯胜为大将军后到洪武二十六年被处死,是蓝玉军旅生涯最辉煌的五年,其间他率十数万大军,于捕鱼儿海大败元军,捕获元主次子、公主、诸王、平章及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讨平施南、忠建宣抚司、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等部(今贵州一带)叛乱;坐镇西部,略西番、罕东之地(今甘肃、新疆一带),击退土酋,降服其众。
就像任何能征惯战的军人一样,雄心万丈的蓝玉有些收不住手。但他没有料到,当他奏请“籍民为兵”、计划扩充军力,前去征讨朵甘、百夷(今青藏、滇西北一带)时,朱元璋却下达命令:班师回朝!蓝玉闷闷不乐地回到京师。朱元璋似乎有意在刺激他,两年前原拟晋封蓝玉梁国公,却临时改封凉国公,有一种降格的意味;西征还京后,蓝玉自忖按功他可加为太子太师,但朱元璋只给了他次一等的太子太傅衔;在朝奏事,他的意见也几乎不被采纳。这边血气方刚,正怏怏不快,那边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撩其情绪,骄傲的将军终于被弄得举止浮躁,这时,专事侦探大臣言行的锦衣卫恰到好处地向皇帝提出蓝玉有谋反企图的指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迅速结案:蓝玉灭族,“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案涉“一公、十三侯、二伯”,一万五千人被杀,《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政治集团”,洪武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军事集团”——此距朱元璋辞世仅仅五年,相信这会使他阖上双目时比较踏实。蓝玉一案的内幕究竟怎样,无人得知,他要谋反的说法来源于朱元璋的御用特务机构,定罪过程也处在封闭、秘密的刑讯状态之中,但后人显然存有疑问,例如由清代官方修订的《明史》便只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没有把蓝玉列在其中,从而以这种方式表达了看法。
我曾在明中叶王锜所撰笔记《寓圃杂记》中,读到对蓝玉其人的间接描述,似乎在婉转地为蓝玉鸣冤。
作者回忆他祖上在洪武年间认识的一个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当时,他决心去京城(南京)闯荡,有友人因“时太祖造邦【建国初期】,法制严峻”而“坚阻之”,“【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后他以教书为业,住处与蓝府相邻,所收学生中因此就有蓝府仆人的子弟。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对他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见这位老师。当朝大将军、贵为公爵的蓝玉,肯结交一个教书先生,这令王行非常吃惊。见面后两人纵论韬略,神飞兴逸,十分过瘾。蓝玉敬重王行的才具,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将王请入府中居住,以师礼事之。不久,蓝玉事发被捕,有人就劝王行速逃,免受牵连,王断然答道:“临难无苟免。”留下来等死。在狱中,面对审问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竟故作愤世语,以请死姿态来抗议蓝玉蒙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
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