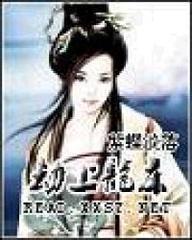龙床-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慕艹龃恚俺ど碲W【红】面,饶【富于】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死,通殁】,数总大军,多立功”。{5}其英名早成,神勇如吕布再世,是朱元璋晚年有计划逐一构害的军事奇才中的最后一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朱元璋帐下良将云集的情形,但我们不难想象,两军对垒之际,敌方统帅投向这支将星争耀的军队时,会是怎样一种嫉妒的眼神!
当然,敌方统帅或许最应该首先打量一下自己的那副尊容——我们来看看朱元璋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乃何等样人。
张士诚,盐贩出身。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据吴地,进而再得浙西,拥江南富庶之地,于是心满意足,唯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起大军来取应天(南京),约士诚合而攻之。士诚竟以其“一亩三分田”为自足,不予呼应。其于元室同样以苟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终逃不脱小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业已击败陈友谅的朱元璋,得以腾出手收拾张士诚;是年九月,徐达破平江(苏州),士诚自缢死。
陈友谅,渔夫出身。原为徐寿辉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阴谋发动兵变,挟寿辉,而自立为汉王;不久,在采石矶(马鞍山)以铁挝击杀徐寿辉。时诸强中,友谅广有江西、湖广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骄横万分,锐意扩张,即兴兵东犯。旌旗蔽日,舳舻拥江,顺流扬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却被朱元璋用诱敌深入之计,大败于南京城外。两年后,双方再大战于鄱阳湖;此番,友谅尽出其精锐之师——当时天下无出其右的巨型舰队,“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军极弱,双方实力悬殊。但陈友谅一味恃强,朱元璋再次用计,以火攻大破陈氏巨型舰队,战局逆转,八月,友谅中流矢毙命。
张陈二人,一个当时最富,一个当时最强。以势而论,元室衰微之际,他们谁都比朱元璋更有资格成就霸业,一统天下。但士诚其人,永远只看得见眼前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本性如此,毫无办法。陈友谅骄狠雄猜,心黑手辣,虽非张士诚那种贪得无厌之徒,怎奈量小气狭、器局逼仄——仅从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阳之战,友谅势蹙之际,居然“尽杀所获将士”以泄愤,“而太祖则悉还所俘”——同样也是本性如此,毫无办法。
在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面前,朱元璋尽处下风,当初陈友谅搞扩张,先对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有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肯定发现搞错了人,至于鄱阳湖决战他“矢贯其颅及睛而死”之际,只怕会感到平生最为后悔的一桩事,就是在没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样一个角色之前,贸然对其出手。然平心而论,陈友谅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于情于理都很说得过去。姓朱的算什么?一个小要饭的,一个窝囊到剃了光头委身破庙靠做勤杂工混口饭吃的可怜虫,要说面相,此人歪瓜裂枣,怎么看都是命贱运晦、毫无福分的人。
深入了解朱元璋生平后,我也大感困惑,甚至觉得历来人才学家所论述的成才规律有统统失效之虞。他生在一个无论古往今来都绝对是最最底层的家庭。父亲朱五四是佃户,靠租地主的田地过活,生了三男两女一共五个孩子,日子之惨淡可想而知。至正四年,一场大饥荒席卷而来,旬日之内,朱家成饿殍者三人,老父老母及长兄走马灯般撒手人寰,家里穷得不要说置备棺木,就连下葬的土地也没有,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日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回忆此时情景,犹辛酸无比地写道:“殡无棺槨【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没有饮食作为祭奠】!”{6}十五岁即成孤儿的元璋,只好托身寺院,做个行童——实际就是庙里管饭的童工。呆了不及两月,饥荒益重,庙里亦难维持,元璋即被打发到外面做“游方僧”,说得不好听,无非是一个和尚装束的乞丐。他要了三年饭回到家乡,也不知日后作何营生,此时天下方乱,先已投了郭子兴的汤和有信来招,元璋正愁生计无着,想了想,也就去了。——这就是朱元璋“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的简要履历。
由这履历,你找不到朱元璋以后从帐下亲兵而头领,由头领而统帅,由统帅而称王,由称王而尽得天下的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一个久沉泥淖、困于人生的贫家子、孤儿、乡巴佬,休说受什么良好教育,即便粗粗识得几个字,也是在寺中才学会的本事{7}。然而,此人的头脑,此人的器局,此人的见识,此人的作为,完全不应该是他这种身世背景的人所能有的。
跟历来的“草寇”截然不同,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戒杀戒抢,每次攻城,必叮嘱领军诸将:“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毋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8}又说:“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可见他出身虽粗鄙,头脑一点不粗鄙。在他做吴王时,浙江方国珍为了讨好他,以纯金玉饰马鞍来献,他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他命将宝鞍原物退回。击败陈友谅后,战利品中有一张陈友谅所用的极尽奢华的镂金床,朱元璋见了指着说:“此与孟昶{9}七宝溺器何异?”当即下令销毁。也是在他做吴王时,有官员奏闻,说街上有人遇见一老者,自称太白神,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官员大约以为这话主公很爱听,岂知朱元璋断然道:“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有一次,他在同手下那群爱将们闲聊中说了这样一番话:“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10}这种话,可能才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辈,以及一切终不能改变“草寇”、“盗贼”命运的农民起义首领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前面讲,朱元璋是皇帝中的另类,其实还应加上一句:在成为这个另类之前,他首先成了古来“草寇”中的另类——他是一个双重的另类。他之脱颖而出,做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就是因为他对“草寇”有一种明确的叛逆意识。碌碌如陈友谅、张士诚岂能望其项背?就是层次再高一些的李自成、洪秀全也远未达到朱元璋的觉悟。后二者与朱元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性,但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怎么也上不去了;李自成打下北京、洪秀全打下南京后,分别迅速腐化堕落,从内部土崩瓦解。
这似乎扯得有些远了。回到朱元璋的时代,我断定陈友谅、张士诚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而弱小的竞争者有一种特殊的禀赋。他们本该自惭形秽,或至少有所警觉,但没有,结果都输得很惨。
关键中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我所谓“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将领善战、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证,但不足以得天下。从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就差在知识分子队伍建设这个环节。匹夫起事,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没纲领、缺宏图、少指针,盲人摸象,误打误撞,难成大事。
这种经验教训,样板戏《杜鹃山》总结得其实是对的:“井冈山派来了党代表。”一堆五大三粗、使刀耍棍的绿林爷儿们中间,忽然塞进来一个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女秀才,从此,三起三落的杜鹃山农民起义军便“节节胜利”、“涓涓细水入长江”了。
朱元璋对这问题的认识深度,不逊于《杜鹃山》。他自己虽是大老粗,难得而且令人称奇的是他非常了解“文化人”的价值,并十分坚决地接纳和倚靠“文化人”。明代解缙谈及此时曾这样评论道:
帝性神开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11}
尽管是“歌功颂德”,但都有史为据。《翦胜野闻》载:
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12}
——这么自吹自擂似乎有点厚脸皮,不过,从中倒可见他以读书为善美、崇文尚学的态度。
几乎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礼聘知识分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朱元璋在整体战略上深受启发。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也很急切地征询陶安的政治见解,陶告诉朱元璋:现今群雄并起,但他们所想所要都“不过子女玉帛”,他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闻言大为感奋,赞道:“好!”(《国初事迹》)《明通鉴》也记述有朱元璋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看来这种故事发生颇多。访贤问士的结果,使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眼界和心志大为提高,也深深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他成就王业的战略意义。据说,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13}此语足见朱元璋看重“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是摆姿弄态的政治作秀,亦不仅仅是因为一时一事倚用其谋策,而是出于“取天下”这一长远战略。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一个绝对超一流的朱氏智囊团。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制订和确立了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评家回顾说: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14},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15}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16}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17}之智计埒【等同,并立】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18}
这的确说到了点子上。
近代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的独特意义,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有大量制度创新,开启中国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19}这三条,都突出了“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当中“人”的因素,除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永恒、绝对之真理外,最能显出明代立国具体实践特色的,是明太祖在战争阶段就有意识地积极地构筑其“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新政权一建立就形成完备而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他不说,单“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足使明之立国成为中国史划时代的事件。“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20}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角度看,它解决了流动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角度看,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角度看,它大大强化了集权政体,影响跨越数百年而直到现代。“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的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21},孟森对此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22}此外毫无疑问,鱼鳞册编造也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
所以,明朝的建立,不像中国许多朝代制度因循,只是权力从某姓易手于某姓。明朝是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