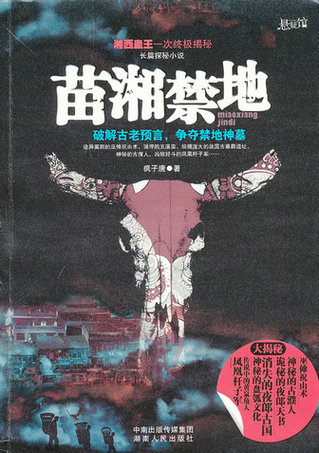弗洛伊德禁地 心理悬疑-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飧龇⑾址獯媪似鹄矗涝侗J卣飧雒孛堋?墒且话倌旰螅钟腥舜蚩怂薄 罢飧颐还叵担 崩芍芫纸患蠛啊! 坝泄叵担蛭蚩娜司褪悄愕母盖谆棋憔褪谴诱飧鼋刂械隼吹摹!薄 安唬弧!崩芍苈反蠛梗拔叶哉飧鼋夭桓行巳ぃ抑幌胝业轿腋盖住!薄 拔腋嫠吣愀盖自谀睦铩!鄙砗蟮娜怂怠! 霸谀睦铮俊崩芍芗泵ψ肺省! 熬驮谀隳谛牡母ヂ逡恋陆亍!鄙砗蟮娜怂担拔铱梢晕闳〕隼础!薄±芍艿难劬ι戏酵蝗怀鱿至艘唤厥直郏直矍笆且恢皇莨轻揍镜氖终疲终粕衔兆乓话驯涞氖质醯丁@芍芫值卣龃罅搜劬Γ蝗凰挡怀龌袄矗迥谒坪跤兄智坑辛Φ亩髟谌涠⒄踉氪铀奶迩荒诩烦隼础J质醯侗涞暮庥成狭怂慕廾芍艿难劬Φ傻眉负跻眩疵惚茏怕逑吕吹牡斗妗 班汀!钡斗媲坑辛Φ厍薪怂亩钔罚恃坏蔚瘟髁顺隼矗缓蟮斗嬉换袼嚎徽疟”〉牟葜剑铀钔芬恢备畹蕉瞧辍@芍苷獠欧⒕踝约旱纳硖寰谷皇浅嗦懵愕摹K竦赝抛约盒馗共康牡犊冢堑犊谝蚱し舻氖账趿Χ杆倮┐螅は轮竞妥橹砹松侠矗迩荒谝恢制婀值纳迤呤职私畔裾掠阋谎炅顺隼础⊥保砗竽歉鋈说拿婵壮鱿衷诹怂氖酉吣凇@芍芏偈本袅耍侨司谷皇恰 拔恕敝卮镂灏俣喽值目湛虯330客机在维也纳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重重一震,郎周猛然惊醒,手里的书掉了下来,这才发现已经从亚欧大陆的东端到了西端。刚才,自己居然在飞机上做了个可怕的噩梦。他呆怔了一会儿,仔细回想梦中的场景,所有的细节都历历在目,可是最后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个人却模糊不清。他到底是谁呢? 郎周弯腰捡起书,这是一本《弗洛伊德自传》。这才明白刚才的噩梦从何而来。从下龙岩的登高山开始,他一直在思考父亲信中的那个谜语,他有种感觉,那个谜语所有的线索都跟弗洛伊德有关。为了了解弗洛伊德,他在广州购买了好几本有关弗洛伊德的著作,仅仅弗洛伊德的传记就有弗氏本人的自传版本、欧文?斯通的小说版本、彼得?盖伊的学术版本以及几个中国作者的版本。还有一些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学引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图腾与禁忌》、《文明极其不满》等等,他一时也看不了这么多,就弄个背包装起来。
第57节:8 弗洛伊德故居(2)
“嗨,先生,您是记者吗?”一个经过他身边的奥地利女孩好奇地看着书的封面问道。她的中文居然说得很不错。 郎周愣了愣:“为什么这么说?” 那奥地利女孩笑了笑:“如果不是为了采访纪念活动写稿子,平时没有多少人看弗洛伊德的。” “采访纪念活动?”郎周不解地问,“我不是记者。什么纪念活动?” 那奥地利女孩“哦”了一声:“原来你还不知道。今年是弗洛伊德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他出生于1856年。”她从飞机座位后的报刊袋里抽出一份报纸,“这是维也纳的《信使报》,你看看吧。再见。”那女孩朝他笑了笑,拉着皮箱走过过道,下飞机去了。 郎周疑惑地接过来,把《弗洛伊德自传》装进背包,边下飞机边看那份报纸。 这份维也纳《信使报》的头版有两个人像,左边是个年轻俊秀的欧洲人,手里握着一把小提琴;右边是个欧洲老人的头像,一把雪白的大胡子,眼睛像鹰隼一般锐利,额头半秃,整齐的西装,手里夹着支大雪茄。 “这个老头儿好像有些面熟。”郎周想,他仔细看了看,心里一跳:“这是……这是弗洛伊德。” 郎周急忙往前跑去找那个懂中文的奥地利女孩,那女孩正拖着皮箱走向自动电梯,郎周冲过去一把拉住她。那女孩子吃了一惊,看见是郎周才嘘了口气:“您……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不好意思。”郎周瞥见两名高大的奥地利警察露出戒备的神色,朝他走了过来,急忙松开那女孩的胳膊,说,“你能给我讲讲吗?这份《信使报》上的……” “可以啊!”那女孩子也看见了走过来的警察,调皮地冲那两个警察笑了笑,警察摇摇头,嘟囔了一句,转回了身。女孩子说:“今年是2006年,是弗洛伊德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维也纳从5月份开始,开展纪念活动。左边那个人就是我们奥地利最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今年正好是他的二百五十周年诞辰。奥地利的报纸把两个人放一块儿纪念。” “这么巧?”郎周瞪大了眼睛。 “是啊。”女孩儿没理解他的意思,说,“莫扎特生于1756年,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两人正好差一百岁。” 郎周摇摇头,他想的是自己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居然正赶上弗洛伊德一百五十周年诞辰。他默默叹了口气,意识到这种巧合中,似乎冥冥中有一种推动,看来这次要和这位首先发现人类潜意识的大心理学家纠缠到底了。 他谢完女孩子,目送她离去,自己背着包慢慢地溜达出了机场大厅,一出大厅,郎周就打了个寒战。11月底的维也纳已经开始进入漫长酷寒的冬天,虽然还不算太冷,但由于时差原因,维也纳此时是深夜,气温非常低,维也纳人都穿了厚厚的外套。郎周在广州和龙岩穿的都是衬衣,没考虑到气候的问题,一下子冻了半死,急忙又退回大厅里。 机场大厅外灯火通明,郎周校正了一下手表,夜晚10点15分,按照钟博士的安排,他那个同窗,沃尔夫?迪特里希,应该在这里接机了,他却没有见过沃尔夫的照片。 郎周在机场大厅门口来回走动,心急火燎,心里咒骂:十天,妈的,到今天下午5点,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我才刚刚到达维也纳,一切都茫无头绪。忽然,他看见从外面的停车场里跑来一个奥地利男子,气喘吁吁的,见到亚洲人就比划手势。郎周估计就是沃尔夫了。 郎周疾步走过去,那奥地利人刚刚失望地离开了一群日本游客,正在四处打量,一眼看见郎周,他顿时高兴起来,远远地就招手,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问:“嗨,是郎……狗吗?” 郎周心里一阵腻歪,钟博士把这家伙的中文教得也太差了,居然把我的名字叫成了狼狗!不过他此时高兴大于恼火,疾步跑过去:“你是沃尔夫?迪特里希先生吗?” 那奥地利人快活地抱住了他,哈哈笑着:“终于见到你了,郎狗先生。叫我沃尔就行了。” “窝儿?”郎周心想,“差不多。我是狼狗,你是窝儿。还不算吃亏。” “狼狗”和“窝儿”亲热地拥抱起来。沃尔夫大约四十岁,个子挺高,身材挺胖,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日耳曼人特征的奥地利人,一个英俊的鹰钩鼻是他脸上最醒目的特征,鼻梁上架了副眼镜,就像山梁上架着两部军用雷达。 沃尔夫很像萧伯纳笔下单纯、热情、快乐的爱尔兰人,总是兴高采烈的:“狼狗先生,欢迎你来到奥地利,中欧的黄金心脏。” 郎周奇怪地问:“为什么叫黄金心脏?” 沃尔夫眨了眨眼,显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深入研究,想了半天才说:“因为欧洲的地图倒过来看,像一只正在奔跑的袋鼠。奥地利的地图就像一颗心脏正好嵌在袋鼠的胸口上。” 郎周频频点头,其实他也没注意过奥地利和欧洲的地图。 沃尔夫带着郎周出了候机厅,郎周冷得瑟瑟发抖,沃尔夫急忙跑到停车场把车开了过来,居然是一辆宝马。不过后来郎周才知道,奥地利连出租车都是宝马或奔驰。沃尔夫拉开车门让郎周进来:“郎狗先生……” 郎周纠正了一下:“叫我郎周吧。” “哦,狼狗,”沃尔夫点点头,郎周立刻被气得半死,沃尔夫打开空调,接着说,“很抱歉,我没想到你会穿着衬衣来迎接维也纳的冬天。不过我在市内预订了酒店,到了酒店,他们会为您提供衣服的。” “没关系。”郎周稍微暖和了一些,问,“钟博士什么时候到维也纳?” “钟博士的飞机大概五个小时后到罗马,他会转乘罗马到维也纳的航班,将会在明天中午抵达。”沃尔夫说。 机场在维也纳东南郊区,他们顺着锡默灵大街驶进市内,一座原汁原味的19世纪的欧洲古城缓缓出现在了车窗外。 奥地利地处中欧,是个内陆国,阿尔卑斯山脉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将它的森林、山谷和坡地一直推到了东北部边境的多瑙河畔,维也纳就铺展在多瑙河与阿尔卑斯山脉之间,著名的维也纳森林从西、北、南三面环绕着城市,渡过多瑙河,就是辽阔的东欧平原。 一进入维也纳,即使在寒冷的深夜,郎周也能感觉到一种金碧辉煌的视觉冲击。奥地利人比较随遇而安,喜欢舒适、安逸,从18世纪起,他们就开始热衷于把历史浓缩成一幢幢豪华宏伟的建筑保存下来,自己躲在其中,仿佛躲在令他们自豪的历史中。 奥地利人将这些建筑搞得金碧辉煌,甚至连城市公园里的施特劳斯汉白玉像也给镀上一层金。白色的汉白玉拱门外,施特劳斯像金光闪闪地站着拉小提琴,怎么看怎么别扭,不过维也纳人喜欢。 维也纳人似乎很习惯自己古老的居住环境,或许是为了一出门就能够到歌剧院听音乐、到圣史蒂芬大教堂做祈祷,很不愿意现代的高楼大厦入侵自己的生活,把极其现代化的联合国城远远地撵到了多瑙河东岸,自己生活在狭窄、古旧的街道中,和各种各样的名人故居做伴。 沃尔夫一边开车一边向郎周介绍维也纳的历史名人:“狼狗,维也纳最欢迎的就是艺术家!维也纳拥有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当然还有贝多芬,在维也纳,你能够闻到他们的气息。” 郎周只好向他解释自己是绘画的,不是音乐家,沃尔夫于是又列举了维也纳的一大堆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等等。不过他也知道奥地利历史上的绘画怎么也比不上意大利,于是又开始得意扬扬地展示他们的建筑,圣史蒂芬大教堂、歌剧院、霍夫堡宫等等。 郎周打断他问:“窝儿,你知道布洛斯拍卖行吗?” “当然。”沃尔夫眨眨眼睛,“就在环城路上,你住的酒店离布洛斯拍卖行不到五百米,明天我可以陪你去参观。还想参观什么?圣史蒂芬大教堂、国家歌剧院,还是国家美术馆?它们围绕在你酒店的周围,拥抱着你入眠。” “我想……”郎周犹豫了一下,“我想参观一下弗洛伊德的故居。离得远吗?” “啊哈!它离你住的酒店很近,不到两公里。”沃尔夫兴奋地朝他一咧嘴,“狼狗,我代表维也纳心理学界和弗洛伊德先生欢迎你。从5月6号弗洛伊德一百五十周年诞辰开始,维也纳人简直要把平时冷冷清清的柏格街19号给挤爆了。狼狗,你怎么会对弗洛伊德感兴趣呢?钟博士说你是个画家,我还以为你是来参观美术馆的,就在那附近给你订了房间。不过它们相距很近,维也纳的精华浓缩在步行范围内。” 郎周瞅着这个兴高采烈的窝儿,不明白他为什么每时每刻都快快乐乐的。郎周沉吟了一下,说:“嗯,画家也会喜欢精神分析学的,达利不就很崇拜弗洛伊德吗?能为我介绍一下弗洛伊德吗?” “当然可以,我在萨尔茨堡就是教心理学的。”沃尔夫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犹太人,19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犹太人,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爱因斯坦,还有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他们都把各自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当时人类视线之外。不过弗洛伊德的出生地在弗莱堡,属于捷克,他是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很受母亲宠爱,后来弗洛伊德说:‘如果谁是自己母亲的无可争辩的心肝,他将会一生都持有某种获胜的感觉,实际上,他常常会真的获得成功。’他三岁的时候,弗莱堡反犹思想越来越严重,其父亲雅各布带领着他们全家迁居到德国的莱比锡,一年后又迁居到维也纳,弗洛伊德一直在维也纳生活了七十八年。直到1938年在纳粹党的枪口下逃出维也纳,流亡伦敦。1923年的时候,弗洛伊德被确诊得了上颚癌,以后的十五年里,上颚癌一直折磨着他。到了伦敦的第二年他的上颚癌复发,弗洛伊德希望体面地死去,医生为他注射了过量吗啡,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沃尔夫停顿了一下,说:“狼狗,我不知道你究竟想了解他的哪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生平可以写上千页的书。” 郎周想了想,问:“他最后是自杀的?” “不,不,不。”沃尔夫连连摇头,“自杀是违背宗教精神的,弗洛伊德是安乐死,他命令他的私人医生,苏尔医生,为他注射了过量的吗啡,这跟自杀不是一个概念—” “你说什么?”郎周怪叫一声,猛地直起了身子,头砰的一下撞到了汽车顶棚。 沃尔夫吓了一跳,瞪大眼睛望着他
![[卢伊德·比格尔_孙维梓_译] 赫拉诺斯虎口拯美记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