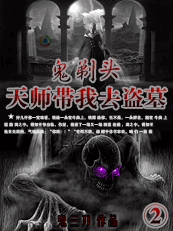带我去阿尔泰-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护士长说要我再想想。
一连三天,护士长那都没动静,安静嘀咕起来,她对万喜良说护士长不会把这件事忘了吧,听说她丈夫正在跟她闹离婚呢。万喜良让她静下心来再等等,明天才是五一哪。她撅着个嘴说只好这样了。
转天安静去找护士长问个究竟,护士长淡然地问她要看什么电影。她惊喜地说是不是院方同意了?护士长点点头,说已经跟电影放映公司联系好了。也许满意的结果来得太轻而易举了,她竟毫无思想准备,用手搓着赤裸的两条臂膀,半天说不出话来。
护士长拉起她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手里,说要看什么电影,得提前通知电影放映公司,他们好从资料库里去找。安静强忍着不让自己兴奋地跳起来,她尽可能平静地说她要跟病友们商量一下。护士长依旧板着个面孔说那好,我等着。
关于看什么电影的问题,病友们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要看国产的老电影,另一派则要看好莱坞的新电影。
安静为难了。幸亏,万喜良给她一个合理化建议,一口气放两部电影,一部老电影,一部新电影,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安静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抛了一个媚眼给他,就跑去找护士长了。回来,她挨门挨户通知,晚上将放映的是《小兵张嘎》和《凤凰劫》。安静出来进去的就像一只快乐的小燕子,唧唧喳喳没个完,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这一天,仿佛是病友们盛大的节日,好多人都在掰着手指计算,自己究竟有多久没看电影了,三个月?半年?或者更久一些?
天还亮着,夕阳正红的时候,就有病友和病友的家属拖着躺椅板凳到草坪上占地方去了。
就连黑桃K也来了。他从住进医院,一天到晚没干过别的,就是从事各种自杀方式的尝试,跳过楼,触过电,服过过量安眠药,都没死,也算是福大命大。他是医生眼里的一级保护动物。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喝完酒之后,就打架,他也曾跟万喜良打过,打过之后反而成了好朋友。
这天的天气也真好,空气里散发着一种湿润、清新、沁人心脾的味道。黑桃K对万喜良说这时候还能看上一场电影,死也值了。万喜良冲他笑一笑,心说常把死挂在嘴边的人,反而不容易死,这家伙就把许多看起来比他健壮的人都熬死了,自己却依然活着,活得有滋有味,虽然面黄肌瘦。他是这个科里的元老。
电影放映的时候,安静拉着万喜良跑到幕布的后面去看,看着比正面还清楚。周围海棠树沙沙作响,像是窃窃私语,那么温柔,那么缠绵。此时此刻,要是再有一两声犬吠和三四声蛙鸣,就跟小时侯看露天电影的情景一模一样了,而且空中飞舞着的萤火虫也四处点起一星星的火光,特有怀旧感。
安静得意地说怎么样,这样的露天电影是不是挺棒?万喜良点点头,说不错,你真不简单,人才呀!
他和她一边看电影,一边享受着夜吻的甜蜜,她甚至还允许他的手钻进她的上衣里抚摸。这时候的她,已经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成了罗马。欲望的小火苗遽然袭上他的心头,他俏声说什么时候能让我瞻仰瞻仰它。她羞怯地明知故问道瞻仰什么?他按了按她的乳房,他想象它一定是玲珑剔透的。她翻翻上眼皮说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老电影里的每一句台词,他都烂熟于心,都能背,用不着再看,他就躺在草坪上,枕着两手,眺望着夜空,他觉得那些晶莹眨动的星星,在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跟他讲话,在强化着他的激情。
安静问他为什么不再对她性骚扰了,是不是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他冲旁边努努嘴,这时候,安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有好几个病友也都跑到幕布后边来了。安静悄悄牵着他的手,溜掉了,径直跑回病房里。两个人摸着黑呆在那,面对面,喘个不停。过一会儿,安静怯生生地问他,是否真的想看她的乳房。万喜良咽了一口唾沫说真想。安静说那就来看吧,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看过它的人。
她洁白一身地站在那里,酷似一尊圣母像。淡淡的橘黄色的光线透过窗户映进来,她的两个乳房宛若两只小鹿,恬静而又柔和。他的脸色和夜色交融在一起,但眸子闪着奇异的光,他感觉得到,她正在瑟缩发抖,显然她比他还紧张。
这个丰润嫣然的乳房,闪烁着月亮一般清冷而又神秘的光辉,距离他是如此之近,它仿佛在对他说:它是你的禁果。他的血液沸腾了,犹如一群蚂蚁在他的心上爬,痒得难受。他忍着,木然地站在那。
他竭力把渺茫的充满了欲望的心从幻境中拉回来,面对现实,想象着这样美丽的神迹,这样圣洁的造物在不久的将来,会枯萎,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不禁黯然神伤,总觉得命运之神对她太残酷了,他发誓他要好好爱她,好好疼她。
这时候,安静的嘴靠近他的唇,给他一个热乎乎的吻,说演出到此结束,闭幕了。然后匆匆穿上衣服,拉着她又回到草坪上,继续看他们的露天电影。万喜良却很久很久没清醒过来,仿佛还在梦中。
还是老电影更受欢迎些,新电影上演不一会儿,就有许多的病友开始退场,万喜良问安静我们怎么办?安静说我们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分钟。万喜良说是不是散场以后,我们还要义务劳动一下,把草坪收拾干净?安静说义务劳动的不是我们,而是你,我只是监工而已。万喜良说我怎么这样倒霉呀。安静说活该。
电影结束,已经是很晚了。
简单收拾了一下,回到病房的时候,他浑身跟散了架似的,瘫软无力,走起路来俨然一叶扁舟,悠悠荡荡。他知道,他是累了,体力有点透支。他赶紧到卫生间冲了冲凉,之后,躺下,点上一支烟,歇着。最近,他闹牙疼,一抽烟,就牙疼,最可怕的是,他的牙齿完全糟了,用手轻轻一拔就掉,不知道是放疗惹的祸,还是缺钙的缘故。
一想到自己的牙都掉了,张开嘴,就像一个黑窟窿,他就禁不住惶恐不安,毕竟他才刚刚三十来岁呀!
这时候,有人敲隔壁的墙,不用说,那是安静。这是他们的暗号,如果敲一声,是问早安,敲两声则是问晚安,现在她敲的是三声,意思是问对方睡着了没有。万喜良赶紧也敲了三下,做了回应,告诉她还没睡呢。
不一会儿就听见有悉悉索索的声音。
安静鬼鬼崇崇地钻进他的屋,万喜良发现,她居然光着脚丫,他说你不怕着凉么?她竖起了一只手指放在唇边,嘘,这样走起路来没动静。
他以为她太兴奋了。所以睡不着。他们的生活太沉闷了,有如一潭死水,随便丢下去一颗石子,都会荡起一阵阵的涟漪。他让出一块地方,让她坐。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睡衣,睡衣上绣了一只大个的米老鼠,他知道,那是她的手艺。睡衣穿在她身上,特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他刚想逗她两句,却发现她有点不大对劲,她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额角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仿佛晶莹透明的雨滴。你怎么了,他问。
疼,她说。他问那里。这,她按着肝区。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他问道。她说就是刚才。他要去找医生,她说用不着,过一会儿就好,我们随便聊聊天,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可以了。他的手有点抖,也许是过分担心的缘故,他担心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他把她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她的额角。
两腿屈着,她那他的枕头顶在肚子上,问他我是不是教科书似的女人啊?他说不是。她追问道不是教科书似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他说是性感小猫。她嘻嬉笑了,又问道看见我的身体,你会想到那个吗?他明知故问道想到哪个。她把身子朝他靠的更近一些,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温存地说了一句。他们靠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他都能闻到她呼出的气息,那气息是甜的。
我说的是性,她说。
他故意说我想不到那个,我还小着呢。她就笑得更欢了。他感到她的手在寻找他的手,很快,她的手指就和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牢牢地握着。后来,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他说你这不是要我当流氓吗?她说我就是要你只当我的流氓。
他说无论如何,她也要把病情告诉给主治医生。她反问道告诉他干吗?他说让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免得病情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的他,真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这个可爱的女孩,如果可能的话。她却毫不在乎地说怕什么,若真的恶化了,实在疼的受不了,就服毒自杀好了。
她的话,让他特难受,犹如一把利刃,扎在他的胸膛上,越扎越深,直到扎出鲜血来。他警告她说给我住嘴,不许你胡说。
她赶紧做了个鬼脸,眨巴眨巴眼睛说ok;我再不胡说就是了,请您老人家息怒。
不一会儿,她就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打败了似的,依靠在他怀里睡着了。她的嘴唇微微翕动,仿佛正在咀嚼她在这个世界有限的时日所品尝过的酸甜苦辣,还不时说几句梦话,不过他很难听清她说的是什么,因为那声音太微弱了,简直就跟森林里飞着的小昆虫发出的嗡嗡叫声差不多。
万喜良把她轻轻地放下,让她躺得更舒服些,然后,拉一把椅子,守在她的床边,像欣赏一幅画似的欣赏着她。她的眉宇间横着两道深深的皱纹,面庞更加瘦削,颧骨愈发突出。他几次想伸出手去摸一摸她的脸,她那美丽的容颜同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醉人的月光交融在一起,可是,他怕弄醒她,没敢。
不知什么时候,他趴在她身上睡着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把房间涂上了一层银灰色,他和她仿佛就像一对长着翅膀,随时准备飞向上帝的天使,沉浸在梦乡里,梦乡宛若天堂。
第二天他去找李萍,把安静的病情告诉她。李萍尴尬地说她就要休假了,最好他去跟安静的主治医生去谈谈。安静的主治医生是个广东人,一说话,满嘴的鸟语花香,他嫌累耳朵。不过,没办法,只好跟着李萍去找那个“鸟语花香。”“鸟语花香”说要控制扩散,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安静加大服药的剂量。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他问李萍为什么这时候去休假,是准备去旅游,还是准备去301医院进修?
因为李萍跟他算得上是无话不谈好的朋友,所以告诉他,他怀孕了,要流产。他笑着说又是一次意外吧?她说是。他问她已经有多少次意外了?她不好意思地伸出四个手指头。他知道,她跟她的丈夫是一对欢喜冤家,总吵,为鸡毛蒜皮也能超得天翻地覆,接着就是冷战,冷战往往能持续十天半个月,再接着就会因为一个媚眼或一句软话而和好,和好必合欢,合欢之夜又常常因迸发的激情而忽略了防卫措施,结果意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有人说,生过孩子的女人已是被吸吮过的葡萄,这话用在李萍身上一点也不恰当,她依然娇娆如花。
李萍休假的那天,“鸟语花香”跟安静谈了一次,安静同意“鸟语花香”的建议,加大服药剂量。安静对万喜良说跟我去做头吧,怕是以后想去也去不了了。万喜良说走吧,我陪你。外面正在下雨,下得是毛毛细雨,他们俩打了一把伞,相拥着离开了医院。
到了美发厅,安静从提包拿出一张克里斯汀·邓斯特的画片,跟美发师说就要她那种瀑布似的发型。还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头了,你给我做仔细一点。做头的是个挺嬉皮的小伙子,说没问题,瞧好吧您呐。这小子嘴特甜,凡是四十岁以上的女人,他一律叫小姐;而四十岁以下的他都叫小妹妹,效果奇佳。
这一套,万喜良也会,会得更多,如果不嫌恶心,对五十岁的女人也可以用香港鸟语叫她们“你们女生,”一般来说,她们都能坦然接受,而且很受用。不就是要讨女人欢心吗?那还不容易。
做头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女人受得了,陪绑的男人则绝对有水深火热的煎熬感。
不过,万喜良倒没有那种感觉,他坐在美发厅的长椅上,东瞅瞅,西望望,看着来来往往的女人,饶有兴趣,仿佛看西洋景。似乎从小他就有这个爱好,只是小时侯站在胡同口看的是汽车,开始看女人则是青春期以后的事了,一边看,一边琢磨对方的职业、生活习惯和脾气禀性……特无聊的一件事叫他做得特专业。
万喜良是个能坐得住的人,而安静则不是,一边做头,一边东张西望,时不时还掉过头来跟万喜良搭讪两句,弄得理发师得不断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