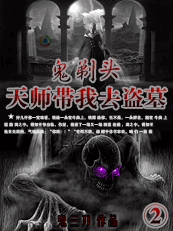带我去阿尔泰-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阵子他们都沉默不语了,仿佛体力透支太多,精疲力竭了。过了一会儿,安静咬牙切齿地说道,一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才知道男人是多么可恶,倒霉的总是女人,男人却躲起来了。万喜良唯唯诺诺地说可不,谁说不是呀。他知道,这时候千万不能招惹她,他吃罪不起。
安静突然想起她的一个女友,她是她所有女友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手提包里永远都忘不了带上安全套,假如有一天出门她忘记带了,她会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会打个车跑回家去拿一趟,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风流得一塌糊涂的她,才不至于让男人搞大了肚子,到妇产科来听大夫护士的挖苦和训斥。在她的女友的心目里,安全套和唇膏、面霜成了随身必须要携带的三大法宝,缺一不可。
安静现在理解她了,可惜,晚了一点。那时侯,她可没少骂她,就在她去日本留学的前一天晚上,安静还骂过她。回想起这些,安静多少有一点脸红了。
回病房的时候,万喜良让她赶紧躺下,休息片刻。
安静说你也休息一会儿吧,看你一脑门子的汗。她想替他擦擦,却发现那汗竟是冷的。
万喜良就乖乖地躺下,躺在她的身边。
她让他枕着她的胳膊,这样可以舒服些。
这天早上,安静刚刚打开房门,就见万喜良跟鱼一样无声无息地游过来,手捧着一大束鲜花,出现在她面前。给,五十朵玫瑰,他说。
安静说假如你要给我一个惊喜的话,那么你的目的达到了。这样一个早晨,有这样一个男人,献上这么美丽的一束花,真是浪漫。
喜欢浪漫,是安静的特性之一。
万喜良吻了吻她的两腮,贴着她的耳朵说宝贝,突然有人给你献花,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安静抿着个嘴笑着摇摇头,不想知道。真的不想知道?万喜良问。她说她真不想知道。
这多少让万喜良有点失望,他起了个大早,颠颠地一个人跑到附近的花店去买花,容易吗,李萍倒是想陪着他来着,他没让。在他看来,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个他们俩都该纪念的日子。他很细心,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放过,特意在大捧的红玫瑰中夹进了五朵黄玫瑰,如果安静足够细心的话,她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并有所醒悟,可惜,安静整个一麻木不仁,只顾闷头摆弄那花,先是把花插进花瓶里,然后又往花瓶里放些水什么的。
许是为给她提个醒,万喜良有意问她记得今天是几号吗。安静头也不抬地说,时间对我来说早已凝滞了,所以她根本不必去关注它。万喜良彻底绝望了,他又不想一字一句地告诉她今天是什么日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不想说,说出来就没意思了。本来,他计划要好好庆祝一番的,现在看来,是没戏了。
安静似乎完全不去顾忌他的感受,一门心思只在玫瑰花上了,左看,右看,看也看不够。其实,万喜良没瞧见,背对着他,她的嘴角含着一丝坏笑。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安静突然问了一句,她故意把问话压低到一种神秘的程度。不,没什么,万喜良说。安静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说道那就高兴一点嘛。万喜良说我挺高兴的呀,尤其是看到你这么喜欢我的花。
在片刻的停顿之后,安静终于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几乎笑弯了腰,她说你这个傻瓜,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正是我们相识的第五个月对不对?她欢快而甜蜜的声音中故意带了点嗲,有那么一股子俏皮劲。
万喜良像野兽一样噌地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她似的吻着她,他说你胆敢捉弄我。她尖叫着躲闪着摇尾乞怜着,饶了我吧,我送你礼物来补偿还不成吗?她说。你会给我准备礼物,万喜良对此表示怀疑,他都被她捉弄怕了。
你看,这不是,安静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贺卡,最上面的贺卡上画着一条潺潺的小溪,小溪上漂着一艘小纸船,安静在上边写了一首诗,诗里有这样的句子:“在爱情的夜晚,命运已给我们摊开了最后一张王牌。”还有“我被抬进坟墓,人们像往常那样生活,仅仅没有了我。”万喜良数了数,一共是五张,就问她怎么这许多,都是你昨天写的吗?安静说你在每一个我们相识的纪念日里,都送我一束玫瑰花,我的诗卡也不多不少是五张,每收到你一束花,我便写一首。
万喜良说你怎么早不拿出来?这些诗卡精致极了,安静的字又很纤巧,他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字总是倾斜的,像一个个游动的小蝌蚪,安静说我拿出来,怕你笑我酸。万喜良说你本来就挺酸的嘛,不过,你酸起来也招人喜欢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这个纪念日过得还是挺酸的。
安静说不知下个月我还能不能收得到你的玫瑰。万喜良拍了拍她的后脑勺说肯定能,上帝不会对我们这么不仁慈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继续充实各自的私人图书馆之外,就是做好事,而且是没事找事的那种。万喜良说这样做死后可以给生者留下个念想。安静则说是为了以后能够上天堂。
一切都始于一个叫金钟的汉子的一番临终遗言。
金钟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里跟他们历数了自己做过的种种坏事,他们劝他,坏事谁都做过,只要他能用做过的好事相抵就可以了,就死而无撼了。
这么一说,金钟反而号啕大哭起来,他说问题就在这,仔细想想,我这一辈子好像没做过什么好事,净干他妈的坏事来着,所以才病了,这是报应啊。他的话就像一记重拳一样砸在他们的心坎上,禁不住后脊梁沟直冒凉气。
那天,他们俩沉思默想了好久,竭力回想着自己在有生之年所做过的所有坏事,比如到老师那给谁打过小报告,背后传过谁的闲话,以及当众挖苦过谁,让谁下不来台……直到想得脑仁都疼了,才不再想。
就在那天,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草案,不管以前都做过了什么,从现在开始,他们要多做好事,做的好事足以抵得过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坏事,才行。
叫他们像雷锋那样雨夜送大娘显然不大实际。
他们只能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例如,给希望工程捐个款呀,给孤儿院赠送些文具什么的,这些勾当他们没少干,而且基本上能够做到做了好事不留名。在他们做好事的鼎盛时期,一天甚至做上好几起。两个人较着劲呢,有那么一点比学赶帮的味道。
他们最大的一笔馈赠是给受龙卷风袭击的灾区。起初,他们计划是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被褥或是方便面之类,直接寄给难民。万喜良说他的救助对象主要是孩子,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安静却说应该把东西给女人们,没有女人哪来的孩子?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讨论了一天,仍是争执不下。
最后,还是决定把款捐出去,给谁不给谁由红十字会拿主意好了。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谁叫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统一来着,而且是一票对一票,想搞个少数服从多数都不成。那些天,电视上天天报道灾区情况,他们天天看,看得人挺揪心的,龙卷风经过的地区犹如摧枯拉朽一般,真惨,让万喜良不由得想起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时,他还小,但是他的父亲就是在那次天灾中遇难的。正因为他想到了这个,才决定,不去劳驾护士,而是由自己亲自到邮局去汇款。
汇款的时候,他碰见了一件意外的事,一男一女在邮局门口打起来了,男的人高马大,挺庞然,女的则小巧玲珑,特袖珍,显然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女的一边哭一边任凭男人的拳头雨点般落下,她唯一能做的动作就是抱着脑袋,掩护住要害部位。万喜良本来是可以不管的,旁边有许多围观者便没有管嘛,可是,他又想,遇见打人的人,阻止他,算不算是做好事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该算是好事吧。于是,他挺身而出劝一下,那汉子却一把将他推开,万喜良不禁怒从心头起,恶自胆边生,一脚踹过去,那汉子没提防一个趔趄就摔在那了,半天爬不起来,围观者齐声给他叫好,这让他有了一种很梁山很水浒的感觉。这时候,没想到的是挨打的那个女人却突然扑了上来,揪着他的袄袖子不依不饶,质问他凭什么行凶,万喜良傻眼了,用半是悲哀半是无奈的口吻说我可是为了帮你呀。那女的说用不着,他是我老公,平时不这样,偶而喝点酒才打我两下,他一天到晚累累巴巴,打我两下就打我两下,没什么。万喜良无法解读这个女人的心路历程,所以他困惑,最后只好在女人的谩骂声中和围观者的哄笑声中逃之夭夭。
回来,他跟安静忆苦思甜了半天,安静说我要跟你一起去就好了。你去有屁用,那是一对不可理喻的狗男女,万喜良愤愤地说。安静说我要是去了,一定好好的教训一下那个女的,告诉她该怎样维护一个女人应该维护的尊严。
万喜良悻悻地说今天算是好心办了坏事。安静说才不是呢,那个打老婆的男人见自己的老婆在关键时刻能够为自己挺身而出,指不定多感动呐,就会内疚,就会跟她重归于好,这岂不是好事一件吗,而且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说呢?
我知道你这么说是安慰我,万喜良嘟囔了一句。安静说不是安慰,而是鼓励,不过,现在想想,我倒有点后怕了,要不是那个男的喝了点酒,要不是他醉醺醺的,他真清醒的话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当时你就不怕吗?
万喜良拍了拍胸脯说当时不怕,怕的是在事后,而且是越想越怕。我这人就是这样,遇事容易冲动,不管三七二十一,事后又喜欢琢磨,一琢磨就胆怯得不行,属于能惹不能搪的那种。
安静不禁咯咯地笑。
万喜良不知道她笑什么,就用勘探队员在采集矿石标本时惯用的目光打量着安静,似乎是在问:有什么可笑的?
安静眯眯笑着说我发现,你这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勇于解剖自己。
万喜良说那是,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嘛。
安静做化疗的频率越来越高。
万喜良发现,安静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做完化疗以后,她不再强颜欢笑,给他讲些荤段子什么的开开心,而是改成唱歌了,唱的都是小野丽莎的香颂歌曲,极偶然的也会唱上一段珍妮弗·洛佩兹的《Get Right》或凯莉·米洛的《Breathe》。唱歌的时候,安静连眼睛都睁不开,就闭着眼唱。
万喜良总是以问询的眼光看着她,奇怪她为什么突然变成超级女生了,但安静却无意满足他的好奇心。
这越发的让万喜良感到忐忑,他叫她枕在自己的腿上,尽可能地紧偎着她,温存地抚摩着她瑟缩的后背。安静强忍住呻吟,却无法抑制胸脯的抽搐起伏。
你是不是很疼?万喜良圆睁着双眼望着她问,迫不及待地想听她如何回答。
在万喜良的反复盘诘之下,终于有一天,安静忍不住告诉他,我疼极了,好像每个骨头节都楔了一根竹签子。她苦着脸用手捏了捏膝关节,纤细的手腕给人一种弱不禁风之感。万喜良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的这句话总的基调是鲜明的——那是一种愤怒的谴责。她撒娇似的说人家不是不太好意思的嘛。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神是迷惘的。
一碰见这样的眼神,万喜良就有点找不着北,他的怒气立马烟消云散了,只说了句告诉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安静说你化疗回来从不叫苦,特坚强,我得向你学习呀。
你跟我比?万喜良来了情绪,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算卦的说我是个盖世奇才。安静噗嗤一乐,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个巾帼英雄。两人对着吹了半天牛,万喜良做了暂停的手势,说得了,你也别硬撑着了,还是让我给你缓解一下疼痛吧。于是,他拿了一块湿毛巾为她冷敷起来。
一天,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他,那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外号叫松井,原因是常年留着一个日本胡。见了面,说了才几句话,就让万喜良毅然决然地做出一个决定,从此把松井的名字从他的朋友的名单上勾掉。
松井说他们班的班长要结婚了,他来送请柬,班长说了,谁不来都行,惟独万喜良不来是万万不行的。
万喜良跟班长的邦交始终处于非正常状态,在学校,班长就没少给他小鞋穿,所以,万喜良推辞道你看,不巧,我正在生病……
松井却说你别逗了,同学们都知道你是没病装病,要么是生意上磕了碰了不顺利了,要么就是坑了谁害了谁怕人家打击报复,才躲到医院里避避风头。
谁这么说的?万喜良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