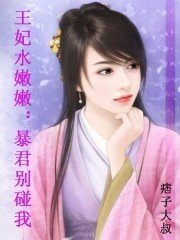魏武情史:暴君的曼陀罗-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密密匝匝的丁香枝吐出了新芽,欢叫的雀儿在花间的缝隙出出进进。折腾了一夜,雁落羽累极了,倒在潮凉的湿地上迅速睡了过去。
梦境凌乱,如灵堂前散碎的玻璃片在暖黄的阳光下闪着诡异的光泽。梦里又回到了温哥华,沿着华埠的央大街四下找寻,店铺外锣鼓依旧,只是不见当日那个“暴徒”的影。
再次走进了那家书店,渴望在那里再度遇到那张狰狞的面孔。如果他再次问起,她会十分确定的告诉他,她是国人。
而人生是不能回头的,不堪做别样的假设,如果事情按照另一条轨迹演绎,她现在或许安然地躺在爱人怀里。
书店里空无一人,百无聊赖地翻看着书架上的书籍,目光空洞,只限于扫过书名。期望在书架后再次看到那双慑人的眼,等了好久,永恒的孤寂……
手上还是那本书,关于一个毫无人情味的北魏皇帝,书上记述了平生的丰功伟绩,却对他的感情生活只字未提。那是人嘛?仿佛是一部不知疲惫的战争机器。她不喜欢这样的书,所以放了多年也懒得去读。
望着古朴的封皮发愣,忽觉一双大手缠住了腰身,眩晕,吻到窒息……
恍惚,那副“梨花带雨”哀伤地躺在暗红的火堆里,渐渐引燃,熟悉的轮廓烧得赤红。心一紧,低喊出声,“佛狸……”
耳边响起粗重的喘息,仿佛是嗅到了猎物气味的野兽。惶恐地张开眼睛,惊觉冰凉而濡湿的鼻尖贴着她的脸。
视线瞬间清晰,腥臭的涎水顺着獠牙的缝隙落入微敞的脖颈,恶犬忽然长开血盆大口汪汪汪地吼了几声。
“啊!”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向后窜出了几大步,仓皇钻出花丛,生怕那条恶狗狂性大发生吞了自己。
咔嚓一声厉响,一双金戈架在了探出花丛的脖上,只听穿银甲披黑袍的武士扬声高喊,“禀校尉,逃犯已抓获!“
雁落羽终于搞清了状况,无奈地伏跪在地上束手就擒。暗自叹息,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尔等速将人犯押送坤宁宫,听候皇后发落。”
牙旗翻飞,仪仗似锦。昏沉之,拓跋焘在高妃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步上车驾。赫连皇后一身隆重的朝服跪谒路旁,顺着眉却暗暗咬牙:高欢儿,别得意得太早了,看看究竟谁人能笑到最后?本宫奉陪到底!
拓跋焘拖着虚软的身上了车,扬手将高妃挡在帘外:“朕想一个人去鹿苑清静清静,不需爱妃随驾。为朕累了一夜,早些回宫休养吧。”一纸诏书,往日的知音良人成了万众瞩目的德妃,忽然间觉得很疏远,又说不清是为什么疏远。隐约觉得,这暗无天日的宫苑之内悄然酝酿着一场隐性的厮杀。深不见底,犹如宫墙角下那口苍凉而幽暗的枯井。
但愿这聪慧过人的女能恪守安分,不辜负他慷慨的给予。焦灼的心高悬不下,害怕那张册封诏书最终会变成阎罗的催命状。
高欢儿愣了片刻,略有些失落,顺从地俯身叩拜。提起宽大的裙摆下了车。高昂着下巴,掩饰着内心的烦躁不安。
伏跪送行的女人们此时都已一一站起了身,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扭曲而傲慢的面孔上挂着讥诮,恍惚,仿佛听到放肆的嘲讽……
车驾浩浩荡荡开出了宫门,送行的人群陆续散去。赫连皇后近乎挑衅地擦着新任德妃的胸圃走过,一脚踩住了对方垂地的雪白裙摆,看不出是有意还是无心。
很高兴看到高欢儿那副默不作声地隐忍表情,她是母仪天下的皇后,管你是什么妃,什么嫔,都没法同她相比!
一大早就听说了瀛澜苑失火的消息,原本担心关在里面的太乐部伎会被大火烧死。幸而乐平王使人传来消息,说那女在失火之前就已畏罪潜逃。怎奈这宫墙深深,纵使插翅也难飞。这不,刚回到宫里就听说了疑犯已被禁军抓获了。
“皇后打算怎样处置此女?”跟在身后的赫连其娜还在为前日的事情耿耿于怀,“高欢儿如愿当上了德妃,姐姐还要留着那小妖精吗?”
“容哀家想想。”长叹一声,疲惫地坐下身,“照理说留着她也没什么用了。只是不知陛下心里是怎么想的?“
“姐姐的意思是——担心陛下怪罪?”
轻轻点了点头,心存顾忌,“嗯。”
“姐姐,留着那刁蛮的小贱人日后必成祸患。若得陛下册封,保不准又是一个高妃。趁其此时还是个乐伎,当断则断,万万不能心慈手软啊。”
皇后砰然拍案,两鬓珠花簌簌摇曳:“杀,杀一儆百,本宫对待这等狐袖媚主的红颜祸水绝不姑息!处死一名逃犯原是情理之的事情,依律治罪,怨不得哀家。”
禁忌之恋,宫掖私情 第69章 刑苑血腥借刀杀人
正午强烈的阳光将赫连皇后轮廓平缓的脸颊照得惨白,浓重的脂粉让人联想到即将入殓的尸首。颊上柔媚的胭脂稍稍缓和了阴森的气质,貌似皮肤原有的血性。
朱红的衣襟上炫目的金凤呼之欲出,凤眼凌厉,振翅长啼。锦袖一甩,霞光闪耀,端坐堂,彰显国母威仪:“传哀家懿旨,将这不守妇道私会通奸的罪婢打入刑苑,明日午时宫刑幽闭!”死并不可怕,为什么一定要这罪婢死啊?在这暗无天日的禁宫之,死,就相当于解脱。
被银甲侍卫押伏在殿外的雁落羽听了传话宦官的复述,不由一头雾水。怎么?又“幽僻”?这次又要将她关押在哪里?殊不知此“幽闭”非彼“幽僻”,乃是一种惨绝人寰的宫刑。
柔弱的身体被粗暴地拖了出去,一路跌跌撞撞直奔宫城西南的刑苑。隔着一片稀疏的小树林,远远听到鬼哭狼嚎的惨叫,凄戾刺耳,让人毛骨悚然。
不是要把她关押在这里吧?脚下发软,身控制不住的剧烈发抖。还要上刑吗?脚下窜起的寒意不由使人脊背发麻……
被侍卫推搡着进了大门,眼前是一座长着茅草的灰石照壁。瓦檐上饕餮狰狞,鼻腔里隐隐闻到焦臭的气味。
突然,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哭喊,急促的尖叫,仿佛是被恐惧淹没了意识,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空的一声,不知什么东西落了地,鬼叫声戛然而止,心随之跌入腹底。
寂静……
跟着刑苑的独眼监守掠过照壁,浓重的血腥直充眼帘——
“啊!啊!啊!”落羽狠狠咬着指尖,发疯似的尖叫,眼前一黑,霎时晕了过去……
侍卫带走了人犯,赫连氏两姐妹蹲在花园的木栅栏旁,兴味索然地饲喂着圈养的白兔。
“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赫连其娜摇晃着干枯的菜凄然自嘲,“兔儿离去时,尚且还能回头看看,男人一旦离开,回头看他又有什么用处?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兔,万岁自从有了新宠就再也没有登过门。”
皇后长叹一声,低沉苦笑,“呵,这都是命。若我大夏不亡,昌哥哥也不会把咱们三姐妹送入魏宫。”将手里仅剩的一片菜投入笼,“若是能够选择,哀家情愿不当这个皇后,留在统万城嫁给一个放马牧羊的庶人。”
“姐姐休要乱说,您天生就是当皇后的命。当日魏宫选后,依姐姐生辰所铸的金人顷刻即成。您是天定的皇后,谁敢不服您?”
“呵,毁就毁在是天定的,不是他定的。”缓缓起身,“妹妹好歹还得过几日宠幸,又生下了皇儿。哀家有什么?陛下从来就没喜欢过我。我若不是皇后,或许这辈都没有机会侍)寝。”忽听廊上金铃作响,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概是图娅来了。”
话音刚落,赫连图娅顶着缀满大串宝石的狐裘小帽,气喘吁吁地冲到两位姐姐面前,“累死了,累死了。那小娼妇何在?姐姐治罪了吗?”
“侍卫已将其送去了刑苑,这会儿怕是已经到了。”
“糟了!”图娅猛一击掌,“姐姐不知其厉害,快快收回成命!”
“怎么?”两位姐姐互看一眼,不知所谓。
“乐平王担心皇后姐姐一怒之下会做出什么糊涂事,趁陛下出宫之机私下与我通了些消息。王爷说,那小娼妇早在去年秋方山游猎之时便得了陛下恩宠,正是宝音公主回来时说的那个被御箭误伤的民女。万岁下旨将其发配阴山,不久便后悔了,暗使辰王爷在戍镇搜寻。据说,陛下微服出宫私临山也是为了这奴婢。圣心所系,杀不得,杀不得!”
“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比那高欢儿更胜一筹。人还没进宫就把个万岁弄得神魂颠倒了。”二姐其娜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
皇后轻挥锦袖,骤然板起面孔,“不,越是如此就越不能留!早知如此,兰儿一死就该趁乱要了那贱奴的命。以她遏制高欢儿,无异于引狼入室!”
“姐姐勿急,只需收回成命。乐平王已为我等献上了一条一石二鸟之妙计。”薄薄的单眼皮下瞬间漾起一片高深莫测的诡异。
“哦?”皇后赫然抬起一双凤眼,表现出十二分的兴趣。
“高欢儿好容易才爬上德妃的位置,怕是早就急着辅佐姐姐治理后宫了吧?姐姐不如趁此时机休息休息,把这后宫大权交给德妃。”
“你的意思是?”
“称病。”
“一早送驾出宫时还好好的,哪儿来的急症?“
“陛下新封德妃,姐姐此时不病更待何时?“
“哈哈哈,”笑声森冷而奸佞,“果然妙计!”情慾是怮惑的毒药,嗔妒是杀人的钢刀……
********************************************************************************
*茕茕白兔*
出自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貌)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兼含比喻。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劝故人应当念旧。
禁忌之恋,宫掖私情 第70章 变态虐杀人间魔域
血淋淋,血淋淋,血淋淋的……
惨死在院落央的女人阴魂不散,被木桩上下贯通的身体滴着血,滴着血,填满了她的噩梦……
梦见自己同死者一样被酒气熏天的侩手高高吊起,长长的、尖锐的木桩对准了“犯下罪孽”的下身、刀光一闪,勒紧的绳砰然断裂,轰的一声,木桩穿透身体冲出了口鼻……
“啊!”雁落羽尖叫一声,赫然惊醒。发疯似地伏在地上乱喊乱叫,僵冷的双手抱紧脑袋,高高撅起屁股,活像是遭遇了惊吓的鸵鸟。
脑海里荡漾着血光,一个苍老的声音交错着混乱的杂质在耳边嗡嗡回响:“姑娘,别怕,别怕……姑娘,醒醒啊……”
怪异的声音没能使雁落羽归于平静,反到平添几分恐惧。无法从声音分辨讲话的人是男还是女,仿佛年老的宦官。思维瞬间搭错了线,脑袋里挤满了《倩女幽魂》里的“树精姥姥”。
“不要!不要!不要!”沉浸于可怕的梦魇,平生第一次感到震撼灵魂的恐惧。终于刷新了从前对于死亡的定义,在她固有的印象里,死亡至多是刀捅进心脏,弹贯穿脑前,服毒,上吊,溺水……
从没幻想过如此可怕的死法,一根穿透身体的,血淋淋的木桩……
恐惧的一幕再次出现在眼前,那个女人尚未断气,痛苦地翻着白眼。
一股清凉的甘霖从天而降,渐渐浇熄了焦躁不安的心火。缓缓抬起恨不能戳进地面的额头,注视着一张黝黑的,异域特色的脸。那样的轮廓仿佛来自印象里的“宝莱坞“。南亚,或者东南亚,遗憾的是她对亚洲并不很熟悉,没有清晰概念。
“姥姥”忽男忽女的声音再次于身后响起,猛一回头,是几张苍老而看不出性别的脸。神色慈爱而温和,很难与妖佞的声音重合,“姑娘,醒了就好。别怕,来,喝点水。”其一个微笑着将一碗清水递进她手里。
友善与关爱迅速拉进了彼此的距离,雁落羽扬起颤抖的小手接过破旧而肮脏的粗瓷碗,勉强还以一个不成形的笑。努力稳定着失控的情绪,环视四下,密密麻麻的立柱让她终于明白此时已被锁进了牢房。栅栏外,遭遇酷刑的女人依旧挑在庭院央高高支起的木桩上,在暗红的暮色下,拖出一条漆黑的长影……
“她,为什么……”思维混乱,词不达意,“她,犯了什么错?”经历了重重磨难才换来的那份开朗,随着脸颊上模糊的泪痕悄然干涸。笑不出来了……
震撼!被心底不断放大的恐惧,打败了……
“错?”盘腿坐在地上的胖大“姥姥”捋着披在肩头的白发凄然苦笑,“呵,错就错在不该得宠。”
雁落羽一脸困惑,莫非真如兰儿生前所说,被皇帝宠幸又没能得到个尊贵的封号,最终将会被那些孤独变态的“弃妇”活活折磨死?抿了口水,放下破碗,颤抖着嗓音探问,“什么罪名?”
“不守妇道。”
“背着皇上偷人?她也是这宫里的嫔妃吗?”望着监舍外被夜色吞没的“图腾柱”,穿透身体的不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