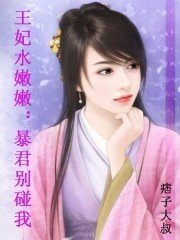魏武情史:暴君的曼陀罗-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空岔口,穿越千载 第40节 旧伤隐痛婉拒深情
“好一个免叫生死做相思!”男人温热的气息拂过稀薄的鬓发,一阵酥麻自耳后向全身荡漾开来……
想要离开那副让人堕落的怀抱,脸颊却被脑后的大手固执地压在肩上,“佛狸,不,不要……”仓皇推柜,颤抖,清楚地感觉到覆上她胸口的指掌。
无视她并不坚决的抗拒,两根长指已挑开了前襟,直奔他专属的烙印。
“不要!”紧紧攥住他探索的指掌,生怕暴露那块丑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光润的蔻丹掠过嶙峋的疤痕,混乱,气息颤抖,“伤……痛吗?”
猛然挣脱他的怀抱,望着眼前深不见底的黑暗,不知道该说什么,颤抖的唇擎着羞于启齿的委屈。
“你……恨他吗?”隐约有些胆怯,想要听她亲口证实,期望得到救赎。
“一场噩梦,我已经忘了。”赶忙打断对方的问话。非要揭开伤疤吗?他很介意吧?长吸一口气,忽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在乎起这个男人。她是怎么了?萍水相逢而已。
“落羽?”扬起大掌,在黑暗摸索——尖尖的下巴,滑下脸颊的清泪。拇指温柔地拭去漾出眼窝的温热,暗自哀叹:伤得太重,她不会原谅他吧?
举袖抹了把眼泪,恍然发觉自己哭了出来。毫无缘由的伤感,就因为面具之后的那双眼睛?轻轻覆上托着她脸颊的大手,陷在浓重的黑暗里,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我问菩萨:世间人秽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我该如何对他?菩萨说:那只有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佛狸,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莫须有。呃,应该有吧。”祖上累世笃信佛教,他自幼耳熏目染,早年还于姑臧与诸多高僧一起译过经书。即使如今入了道门,依旧很难全盘否定过去的信仰。
“我不信!为什么善良真诚的人都死了,而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都活得逍遥自在?”父亲、席乔政,还有她都成了枉死的冤鬼,而倪凯却活得无比滋润。今世亦是如此,她在阴山的风雪饥寒交迫,险遭凌辱;那骄淫凶残的暴君却端坐在金銮殿上指点天下。天理何在?报应在哪儿?
“天涯沦落,同病相怜。落羽,何人死了?你究竟有何冤屈?或许,我可以帮你。”如果有命活着回京,他一定为她沉冤昭雪。
“我的恋人。”破泣为笑,抹去眼角的泪水,“多谢你的好意,可惜你帮不到我。我不属于这里,早告诉过你,我只是个妖精。”
黑暗,一双大掌猛然捧起她的脸庞,“好吧,妖精!生死有命,死者已矣。然红颜易逝,你不能一辈待在庙里。”心意已定,他要带她回京!虽然无法预料会是怎样的后果,先把她弄回万年再说。
“举目无亲,我还能去哪里?”音色伤感,看不见脸上的表情。
“与我回京。”
“不不!不行……”沉默片刻,索性坦白道,“实不相瞒,我是朝廷通缉的重犯,蒙恩人相救藏身在这尼姑庵。回京城无异于自投罗网,或许还会让你跟着受牵连。”
“哪里话?姑娘救命之恩,佛狸无以为报。你我二人同是亡命天涯,休再说什么牵连不牵连。”低沉一笑,似有些局促,“跟我走。落羽,没有人可以伤害你。我是说——我会一直守护你,直到死。”脑袋里转动着蝶恋双飞,鸳鸯交颈之类的缠绵画卷,嘴里却唯恐冒出一个虚华不实的字眼。后宫妃嫔无数,而她,只能是他榻下的奴。
他不忌讳她胸口的那块耻辱的伤疤吗?明知道不该轻信,可她还是动了心。雁落羽,你怎能轻易相信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她甚至都没见过对方藏在面具后的真面目,她就这么答应他了?
可她真的好感动,在黑暗聆听着复活的爱情。心,狂跳不止,怂恿着周身燥热的血脉……
冷静!她要好好想想:
George……
如果她就此答应了对方,算不算背叛了爱情?
是的。这对眼前的他也不公平,她对他的渴望无非来自面具背后的那双眼睛。靠着那副宽阔的肩膀,脑海里却是故人的面孔。害怕他摘下面具的时候,她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努力疏导着矛盾的情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时辰不早了,天大概亮了。总算熬过了一夜,可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上去看看寺门开了没有,师太早课的时候,我找机会送你出去。”
“落羽?”为什么不回答他?是拒绝,还是默许?深邃的黑暗,像一堵无从逾越的墙遮蔽了那缕“皎洁的月光”。
女人轻柔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停顿了片刻,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
他明白了……
隐隐有些伤心——
然而圣驾私临山已经不再是秘密,她继续留在这里多半会丢了性命。拓跋辰为了洗脱欺君之罪,难保不会杀人灭口;而怀着各种居心的党羽,都在瞻望他微服出京的目的。她没有拒绝的权利,他定要带她同返京畿!
时空岔口,穿越千载 第41节 喋血菩提生死茫茫
压抑的黑暗,仿佛生死簿上干涸的墨迹,拓跋焘不知自己昏睡了多久,终于张开了眼睛——
黑暗依旧,分不清身在人间,还是堕入了地狱。冥冥看见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耳边隐约听到冤魂凄厉的的哭泣……
恐惧,
再次昏睡了过去,依稀看见太晃的生母贺兰穿着一身飘渺的白衣,站在十丈高的双阙殿宇上掩面哀号。浓重的雾霭浮过宫阙的匾额——“太庙”?
祖先的牌位在祭坛上颤抖,无数支蜡烛诡异地摇曳。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仿佛是,先皇?
烛光一闪,但见明元帝拓跋嗣身披金甲,手握长剑如生前一般威仪,紧锁眉宇,对着他大声呵斥道,“焘儿,你好糊涂!身为父亲,你怎能对朕的宝贝孙儿这般冷酷?他还是一个未及弱冠的孩!位居东宫的难言之隐,你少时也曾经历过。要多多体谅他!看你对他这般猜忌,实令为父心痛啊!”
赫然惊醒,额前的冷汗顺着脸颊滴滴答答地落在襟前,扬起手背在下巴上随意抹了一把。自数年前一怒之下灭了凉国,将凉帝沮渠牧犍之宗族、吏民并沙门数万迁入平城,他便时刻担心那些暗藏沙门的乱臣贼会伺机兴风作浪。每得密报太与众沙门聚于东宫,都会感到身下的龙座乃至脚下的大地都在颠簸摇晃。落难之时,先皇托梦,莫非,他当真错疑了晃儿?
纷乱的思绪如嗜血的虻虫在耳边盘旋,嗡嗡嘤嘤,叫人一刻不得宁静。寂静的黑暗让人对时间失去了判断,焦心的等待,期待那昏暗的石阶上再次响起温柔的脚步声。
时光在半梦半醒之间静静流过,最初的寂寞被挥之不去的牵念化为惶恐……
她去了多久?为何始终不见回来?
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
暗夜里的刀光剑影在脑海重复回放——
但愿不会牵连到她吧……
等待,
愈发漫长的等待……
该死,
他等不了了!
扶着身后的谷仓吃力地撑起身体,凭借隐约的记忆,摸索着潮冷的墙壁攀上陡峻的楼梯。形容狼狈,几乎是五体投地,手脚并用艰难地爬向出口,全然丧失了帝王的威仪。
掌心满是前夜烫伤的水泡,吃力地挪动沉重的石盖。轰轰一阵闷响,终于又见一片夕阳——
不!
那耀眼的赤红并非夕阳,而是一片寥落的火光,像侩手行刑前酣醉的脸,淡漠却张扬着杀戮的血腥。
半张狰狞的面孔大睁着愤怒的眼睛望着自己,砸碎的头颅属于威武仗剑的毗琉璃天王。燃烧殆尽的庙宇只剩下漆黑的架构,即将熄灭的火光染红了夜空的冷寂。
长襟一抖,跨过倒伏在地的神像,在火焚后的废墟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体隐隐打着哆嗦,空白,一时弄不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
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漆黑的灰烬下埋藏着深重的恐惧,断壁残垣的余温炙烤着干涸的心。
缓缓穿过院落,在房毁屋塌的正殿内四下收索。
突然,在烧得漆黑的椽木下发现一具焦黑蜷缩的尸体。疾步冲上前去——
一阵眩晕……
苍天啊!何止一具身体!
天道昭昭,朗朗乾坤,“天平真君”的天下何时有过真正的太平?行凶者何等猖狂?杀人灭口,毁尸灭迹!
心一惊,终于忆起他下意识寻找的面孔——
落羽?
注视着几具焦黑的尸体越发胆战心惊……
呼吸瞬间加快了频率,以至于上气不接下气,怔了片刻,歇斯底里地冲上前去,颤抖着双手翻腾起那些面目全非的尸体,或油滑粘腻,或酥软粘连,或干瘪焦硬……
而他的表情过于专注,忽略了恐惧,甚至忘记了恶心。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秀发燃烧过的灰烬,这里没有他的落羽!
凄凉的夜色下,微弱的火光摇曳着飘渺的暗影,苍白的面具看起来愈加哀伤。攥紧双拳,将指骨捏得咔咔做响,仰视苍穹,龙啸天:“落羽!你在哪里?”
无人回应,夜的冷风荡漾着起伏的回声……
声嘶力竭,赫然垂下骄傲地脸庞,内心交织着愤恨与无助:他的落羽——他的奴儿去了哪里?被什么人带走了?亦或,已在利刃之下屈枉殒命?
拓跋辰……
拓跋辰有最大的嫌疑!窝藏钦犯,欺君罔上。他的奴儿若有个三长两短,他定将那竖诛灭满门!
时空岔口,穿越千载 第42节 鸾鸣中山和困万年
夜风擦过苍白的面具,吹动散乱的发丝,火光将远去的踉跄身影映照得越发修长。
过客匆匆,看不清擦身而过的面孔,仿佛是归心似箭的路人,又仿佛是飘来荡去的灵魂。拓跋焘独自一人在茫茫暗夜里行走,思绪陷入一片混沌。
虎落平阳,眼下他该如何是好?
是该潜回万年,还是该现身山?
何人妄图袭驾弑君?又是何人烧毁了尼姑庵?是否同一伙人作案?
前日,藏在暗处的行凶者纵火之时,房门上了锁。近身的侍卫背叛了他,拾寅究竟受何人指使?
应该——
不是汉人……
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人影,隐约回想起地窖的那个梦。迅速否定——不,不是晃儿!
会不会是拓跋辰?
照理说,山王归省封邑,不会这么快就得到他微服出京的消息。然而庙里突发的这场大火,却排除不了受其指使的嫌疑。
郁闷,找不到落羽。那奴儿即使没有被杀人灭口,也会被藏匿在隐秘之地。
临近城门,忽听鸡鸣犬吠,前方隐约亮起一片火光。浮动的赤霞渐进,转眼化作根根闪烁的火把。拓跋焘心里弥漫着一片恐惧,哪里来的一队人马?是想逼宫,还是来救驾?
孤零零地立于城下,已是无路可逃了。片刻,人已被闪耀的火把团团围住,嚓啦一声抽出暗藏靴的短剑,眼浓重的血腥让人不寒而栗。天有天的死法,万不得已之时他会选择自杀。
手持火把的兵士被那双杀气腾腾的眼逼得节节后退,但见乱军之冲出一袭熟悉的人影。拓跋辰战袍加身,却未着战甲,猛一抱拳伏地跪拜,“臣等接驾来迟,罪该万死!”
数百军士轰然伏跪在地,众口同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迎圣驾巡幸山!”
拓跋焘长舒一口气,垂下手的短剑,终于将提在嗓眼的心放进了肚里。如此看来是他多虑了,难得山王一片赤胆忠心。“平身。”强忍肩头的疼痛,拖着蹒跚的步履上前扶起伏首称罪的兄弟,“朕微服出巡山,险遭贼人暗算。山王护驾有功,待朕还朝之日定当重重封赏。”
“多谢陛下不杀之恩!昨夜接到太密函,臣弟才知圣驾临幸山。信说,近日于朝听到些风言风语,有‘挟藏谶记’之术士煽动朝廷重臣结党谋反,殿下恐逆贼途袭驾,嘱臣戒严全城,务必确保圣驾安然无恙。”
听了拓跋辰的解释,帝不由喜形于色。难为太晃能尽心为君父分忧,暗使人保君护驾。先帝在梦教训的是,他当真错怪了晃儿。解开了暗藏多年的心结,无疑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唯一的遗憾,他的奴儿不知是死是活……
没有人知道,雁落羽已被人捆了手脚,堵着嘴巴,阴差阳错地扔进了载满舞姬伶人的“囚车”。
直到此时她还不晓得,车上的十几名美女乃是幕府小吏奉山王拓跋辰之命精心挑选的送往万年为乐平王拓跋丕祝寿的贺礼。那位丕王爷堪称能征善战,功勋显赫,威震合,但唯一的嗜好就是慛残美色。但凡美人被送进乐平王府,无一不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
该着她雁落羽走背字。大清早刚钻出地窖步入正殿,就被持刀盘问师太的蒙面歹徒撞了个正着。情急之下拔腿就往外跑,怎奈两名黑衣人跟在身后一路穷追不舍。
拼了命冲出寺门,钻进了横七竖八的小巷,远远看见一群身着白袍的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