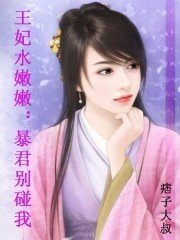魏武情史:暴君的曼陀罗-第1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爷,咱们鲜卑人打江山靠的是金戈铁马,不是靠什么民心。您自幼学的都是汉人的经史集。读书可不能读傻了!”盛道眨巴着略显松弛的眼皮,无奈于太优柔的个性。
“抛开孝道不提,本宫问你,皇叔公拓跋范手里掌握了京畿近半数的兵权。古弼那班征伐在外的忠臣良将自是站在父皇一方。”
“我方也有不少能征善战的良将,论兵力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就算真的兵刃相见,对方怕是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外行看战术,内行看补给。朝廷的钱粮有几成攥在你我的手里?何况,内战若真打了起来,对我大魏国有什么好处?无非是给刘宋和柔然留下以可乘之机。”一手撑着前额,极不情愿地正视自己的弱点,“父皇在位一日,那柔然与刘宋就断然不敢犯我边境。与父皇横扫合的天威相比,尔等以为本宫的战功如何?”
“这……”当朝太不善征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刘宋、柔然来犯,本宫就派尔等前去迎战吗?”乐安王那样能征善战的重臣皆是父皇的亲信。生死之交的情谊皆是战场上血与火锻造出来的。就凭他手底下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能跟人家相提并论吗?
想到国家被内忧外患所困,任平城的态度首先软化了下来,“臣只是担心,万岁回宫之后,真能将朝政大权交给太吗?之前,万岁曾下旨让太总揽朝政,结果没几天就把放出的权利又收了回去。”不得不承认,宦官就是宦官,窝里斗他们拿手,说到打仗就……
“这次貌似不大一样。兵变前后,父皇的表现让本宫一直觉得很奇怪。以他老人家的个性,不会就这么坐以待毙的。可直到今天也没见对方有一丝动静,听乐安王说,父亲是真的想要安居深宫,颐养天年了。”
在安乐殿当差的任平城不住地点头,“这也很有可能。皇后不是把那小杂种送回安乐殿了吗?眼下,应该在黄泉路上了。”
太晃心急如焚,“天一放亮,速速派人入宫打问!”那孽种一死,就代表着他的处境终于安全了。虽说兄弟众多,可能让父亲想到废掉他这个储君的却只有那小野种一个。对方若死了,父皇还舍得杀他吗?他若死了,还有谁能继承大魏国的万里河山呢?以他对父皇的了解,对方即使对他恨之入骨,也不会做出这等动摇帝业根基的事。
然而,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会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黎明时分,禁卫军终于在冷宫里搜出了些许线索。
赫连皇后独守在钟粹宫的正殿里一夜未眠,忽听门外响起传令官急切的通报,“启禀皇后,我等奉命搜查冷宫禁地,在罪嫔高欢儿的榻上发现了可疑的血迹。”
高欢儿?
只觉得心口骤然一紧,轰然起身询问,“快说,还有什么线索?”心底弥漫着深重的恐惧,声音开始不稳。
“房门内外血迹斑斑,在不远处的柴草堆里发现了小皇的一只手镯。”说着话,将满是血迹的证物——甚至是遗物,毕恭毕敬地呈上前来。
“什么?”皇后眼前一黑,险些晕了过去。用力撑着案头,强打着精神询问道,“高欢儿何在?”
“已被我等拘押,送往刑苑拷问。临行前还一路大嚷着,要皇后娘娘还她的儿。”
“什么,她的儿?她高欢儿什么时候有过儿?”心里很清楚对方已经疯得不明人事了,怀疑跟她索要的儿正是失踪的望儿。
“对方一口咬定,皇后娘娘要把她儿溺死。还说带我等去找证据。结果,我等在宫墙一角的废水池边发现了乳娘的尸体。”
“乳娘她——死了?”脸色煞白。因为那个女人的一句疯话,她这后宫之主怕是难逃嫌疑。
“是。乳娘乃是被人用发簪刺死的。那种长簪乃是高句丽独有的款式。所以臣等推测,凶手正是那高欢儿。”
魏宫旧制,子贵母死 第331章 困境脱险绸缪再生
拓跋焘带领着仅剩的几十名亲军围坐在帐外整夜酗酒,时而高唱,时而大笑,犹如打了胜仗一样。
萧竹强撑起虚弱的身,稍稍愈合的伤口撕裂般的疼痛。寻着爽朗的说笑声望向帐门,依稀分辨着那缕熟悉的男声。
“来来来,陪朕喝个够,死也要做个地地道道的酒鬼!”坦然说笑,“朕十五岁登基,吐哺天下二十余载,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万岁,吉人自有天相,我等定能化险为夷,顺利还京。”
“朕闲来卜了一卦,战龙于野——大凶。”全然并不理会他人的宽慰,面对生死坦然一笑,“呵呵,诸位放心,喝毒酒砍脑袋朕一个人承担。尔等不得怨恨,仍要尽心辅佐太,以大魏的江山社稷为重。”
众人把酒豪饮,七嘴八舌的闲聊,忽听有人气喘吁吁地入宫来报:“万岁大喜,乐安王亲率五千精兵赶来盛乐接应,围困行宫的叛军如鼠丧胆,皆已望风而逃!”
拓跋焘轰的一声站起身,悬在心头的大石当下落了地,“太仁孝,朕之福。”什么闻风丧胆?这种粉饰太平的话就不要在他面前说了吧。晃儿若是想杀他,乐安王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驾。无非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各自找了个台阶下。
目光投向月色下白茫茫的湖面,平静无波,仿佛结了冰似的。一场虚惊过后,双腿开始发软,整个身迎着夜风微微地瑟缩……
人是被抬回毡房的,萧竹以为他喝醉了。强忍着剧痛下了榻,却换来对方的一通数落,“哪个要你来伺候了?还不给朕滚回榻上!”
乖乖回到榻上,眼看着拓跋焘被几名将士放在她身边,扯起被掩住身,生怕被人发现她是个女的。待众人退下之后,方才开了口,“酒鬼,喝到站不起来了?”
“不是酒,因为——紧张。”思维有些迟钝,打量着略带嘲讽的小脸,伸手将她揽进怀里,“好些了吗?这三更半夜的,怎么不睡了?”
一股酒气直冲鼻孔,却并没有想象的反感,柔声回应道,“没明没黑地睡了那么久,哪里知道外面是黑夜还是白天?”安然靠在他怀里,双臂圈着紧窄的腰身,“佛狸,如果回不去京城,你不后悔吗?”
“乐安王此时已率兵赶来了盛乐,围困行宫的乱匪已纷纷知难而退了。”刻意将围困行宫的兵马定性为“乱匪”,而不是“叛军”,以掩盖东宫叛乱的事实。
“万年怎么样?”萧竹问得转弯抹角,无非是担心她的望儿。
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朕也想知道……”轻轻抚过她的后脑,“安乐王一到,便有消息了。”
“望儿他……”鼻发酸,强忍住哽咽,紧紧咬着下唇。凶多吉少——之所以没有说出口,因为她知道,他比她更在乎那个孩。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的宠爱,才将年幼的孩推向了无情的利刃。
“怪朕。”他十分清楚对方想说什么,欲哭无泪,心却在滴血。不停地问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固执地想要一个年幼的孩继承他的一切?是因为孩本身,还是因为他的母亲?留在他母亲的身边,做个置身事外的朝臣有什么不好?只因他的一缕“妄念”,就断送了一条幼小的性命。
为人父母,常常对孩抱着太深重的期望。爱他,却常常忽略了那副幼小的肩膀。只知道那份望成龙的感情是厚爱、是关心,却看不穿期望的背面是不堪重负的压力。为人父母的“妄心”少一点,对于孩亦是莫大的慈悲。
“落羽,你可以怨恨朕。如果望儿真出了什么意外,朕甚至愿意把命赔给你。”
“不,我不恨你。望儿没了,你的确有责任,但你毕竟不是凶手。”就像当初的席乔正,她父亲的死说来因他而起,然而真正的凶手却是倪凯。
不会就这么算了,谁碰过她的望儿,她就要谁偿命!
锁定女人燃烧着沉沉仇恨的眸,脊背不由阵阵发冷,“朕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心虚,仿佛丢盔弃甲的逃兵。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只会害了晃儿。
萧竹微微眯起双眼,凄然苦笑,“我呢?我已经没有儿了!”
拓跋焘以为,他没有办法劝阻这个女人。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亦如幻。然丧之痛可谓终极之幻,这个“忍”字,叫他怎么说得出口啊?
这种情况下,只能寄望于晃儿保全自己了。只要太足够强大,区区一名女何以为难他?
而他能做的就是既往不咎,窝在万寿宫里长久的“消沉”下去。正所谓“无为而为”,进而保证太掌握足够强大的权力做他想做的、该做的事情。
魏宫旧制,子贵母死 第332章 爱之愈深责之愈切
拓跋焘径自换了一身玄袍,等待着拓跋范入帐朝见。心事重重,抚弄着狐裘褥上的白毛,时不时瞥一眼侧卧在身后的女,轻声说道,“朕与这位小皇叔年龄相仿。自打穿着开裆裤就在一起玩耍。当初他被蠕蠕大军围困云,朕拼了性命前往解围。如今,终于两不相欠了。”
“怎么,你想杀他?”萧竹冷不防冒出一句,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自知失言,战战兢兢地迎上惊诧的眼光。
“你——怎么会这么想?”好可怕,就像能看到他心里一样。全然没有得遇知音的感觉,恐惧,仿佛被人剥光了衣裳。
“大恩成仇,但凡功高盖主者都逃不过一死。”伸手抚弄着他袖口的菊花,回避去想可能已经遇难的孩,“呵,这话我原不该说出来。无奈,太了解你的为人。”
“朕不知道,得遇知音是好事还是坏事?”心在矛盾挣扎:抛开帝王权谋,他的本意并不想杀小皇叔。
“两心相映原是件美事。只可惜身为帝王原应是孤家寡人。”
“或许这就是朕对你又爱又恨的原因。幸遇知音,又怕遇知音。”
“就像你当初在病的时候——怕我的是那个暴君,爱我的是那个亡国流民。”
“呵,那个暴君就不爱你吗?他一直在妒忌,甚至比那个亡国流民更渴望得到你。”
“那个混蛋,一点都不可爱。”轻轻触碰他的指尖,直视他苍凉的眼,“可我,还是爱上了他。”
“什么?”太意外,反掌握紧她的小手,“你是说真的?”
“还记得宝胤吗?”温情满满,与他十指交握。
“见鬼!”仿佛遭遇了一盆冷水,愤愤地低咒。
“别恼,听我说。你不觉得宝胤和那个亡国流民很像吗?”几经重创,忽然想明白了许多事情,“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宝胤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可我为什么不能像对你一样对他?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因为我在他身上找不到那个暴君的影。”
“那个暴君,那个混蛋,他一次一次伤你,你不怨恨吗?”五脏腑都在颤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都是真的。
“我的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做‘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或许,这是女人天性的悲哀。我们并不期待跟神生活在一起,情愿爱着我们的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有时是循规蹈矩的圣人,有时是狂傲不羁的马贼。”
他眼有泪,却分明在笑,“让朕说什么好?或许,从始到终朕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俯身吻上她的眉心,“朕有许多难言之隐,需要你担待,需要你容忍。”
“人活着,在索取的同时也渴望着付出。女人在获得爱情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被对方需要着。就像对待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出于天生的母性。”在宝胤那种男人的身边,很难满足这种心理。对方给她感觉更像是父辈,是兄弟。而完美的情人,大概是父亲和儿的混合体。
“也许这正是朕最最渴望的东西——朕,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
话题渐入佳境,拓跋范却在此时带着人马抵达了盛乐行宫,拓跋焘觉得有些扫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宿帐,前往不远处那座最大的毡房。
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就像他在那封密信里描绘的那样。钝痛,急切的询问,“小皇他……”举目望向门外,眉心纠结,小心回避着乐安王的目光。
意料之外,拓跋范轰然跪了下来,惶恐地伏在地上久久不敢抬眼,“臣有罪!”
“怎么?”错愕,迅速将视线拉回近前。
“小皇他……他……”全身瑟瑟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孩没了——
“意料之的结果,小皇叔无须自责。”狠狠攥起拳头,仿佛要把骨头捏碎似的。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臣没法对万岁交代,请万岁赐臣死罪!”趴在地上,始终不肯起来。
拓跋焘越发心虚,急切地追问道,“到底怎么了?”
“小皇他——”暗暗一咬牙,“事发当日,皇后潜人将小皇送去了安乐殿。”
“那么,不是皇后……莫非,是晃儿?”论及凶手,手足相残大概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未经查证,臣不知。”乐安王额前的冷汗大滴大滴地滚落在地上,“冷宫之内只寻得一滩血迹,小皇的金镯落在了柴草堆里……”
拓跋焘心口一沉,顿觉昏天黑地,捧着胸口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