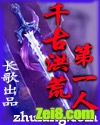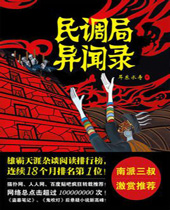千古大变局-第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抟沙杖怂得巍�
又有人言,“当诉诸国民全体,先以国民全体之名义迫袁退位,倘若恋栈,乃兴民军,未为晚也”。这一说法固然有理,看似可行,可由谁来诉诸国民全体?如何组织操作?社会各界是否认可?只要稍加分析,就会觉得此说并无实际操作之可能。
还有人认为,“临时总统,即将告终……则将来选举,相约不投袁票,亦未尝不可。”而事实则是当时的国会已处于袁世凯的操纵之下,议员们失去了自由投票的权利与可能。
如若“二次革命”避免,国民党人于宋案唯有不闻不问,一切听凭袁世凯处置,还得拱手交出南方事权,由他纳入“全国一盘棋”的专制集权范畴之内。
法律解决不成,又受袁世凯强力威逼,国民党才迫不得已奋起抗争。从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至9月2日南京被北洋军攻占,9月11日熊克武在四川失败,不到两个月时间,“二次革命”便告彻底失败。
国民党在力量远远不及袁世凯,又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失败的结果早在预料与注定之中。只是没有想到惨败得如此之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为军队干预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错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整合改造当时各种武装集团,向军队国家化转轨的大好良机。当然,其主要罪责在袁世凯,但国民党也难辞其咎。
就因果报应而言,所有参与刺杀宋教仁的个人最终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武士英在狱中被毒药灭口;应桂馨虽被人劫狱逃过一难,但在“二次革命”后邀功请赏时惹怒袁世凯,于1914年1月19日被他派出的京畿执法处侦察所杀;赵秉钧得知应桂馨结局,不免兔死狐悲,无法掩饰对袁世凯的不满情绪,为除后患,袁世凯乘赵秉钧生病之际,派人送去毒药逼其服下,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其任职的天津督署中毒身亡。赵秉钧之死,更加证实了袁世凯与宋教仁被刺有着无法洗清、难以摆脱的重大干系。袁世凯本人的结局众所周知,1916年6月6日,在众叛亲离的忧虑、全国民众的唾骂与讨袁巨潮的惶恐中命归黄泉。死得最晚的要数洪述祖,宋案爆发五年后,被宋教仁年仅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及宋教仁的秘书刘君白在上海外滩发现,两人当场将他痛打一顿,又扭送至法院,后移交北京,被判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判决,一再上诉。审判延续到1919年春,此时已是“五四”运动前夕,在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洪述祖的申诉不仅没有成功,反被加重惩处,于1919年4月5日处以绞刑,临刑现场惨不忍睹。
若从国家与民族、民主与宪政、政治与法律等角度而言,刺杀宋教仁这一悲剧所造成的严重缺憾,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直到今天也无法弥补,难以消除。
刺杀的恶例一开,此后便不可收拾。民主选举中,暗杀、威胁、动武、辱骂、拉拢、操纵、欺骗、收买、利诱、贿赂等层出不穷,虽手段各异,但本质归一。直到今天,类似的丑行仍“源远流长”,不断上演。
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失败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而在两年之前,他还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清廷请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他提出六项措施作为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解除党禁。可他一旦当选民国大总统,就出尔反尔,倒行逆施了。此后,袁世凯更是偏离民主建设轨道,在专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4年1月10日强令解散国会,1915年12月12日改民国为洪宪元年,上演了一出称帝闹剧,着实令人不齿。
宋教仁被刺一案既促成了袁世凯迅速垮台,也造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动势力的更其猖獗。毫不夸张地说,宋案乃中国近代一大转折,标志着17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广为采用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象征着近代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的努力归于失败。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笔墨作一延伸,对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稍作描述。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员逃散,组织一片混乱。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认为此次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鉴于过去内部号令不一,孙中山反复强调:“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具誓约。”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人,“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按指模。这些做法,无疑使一个议会政党退回到旧式会党的落后水平,打上了宗派主义的浓厚色彩。同时,孙中山对政党功能也进行了重新定位,先是“一党革命”、“以党建国”,然后则“以党训政”、“以党治国”。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忧惧而逝,北洋军阀各自为主,各自为政,互不买账,中国陷入没有休止的军阀混战。孙中山为革命呼号、奔走几十年,组织会党,发动起义,可长期以来,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正式军队。辛亥革命以前,主要是运动新军反正。辛亥革命以后,则是借助一派军阀势力反对另一派,而这些军阀没有理想信仰,唯以利害关系为重,向背无常,弄得孙中山一败再败,好几次差点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当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后,他才真正认识到“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无法完成革命大业,建设一个新国家。于是,孙中山下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援,可他们置之不理,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给予孙中山的帮助实在是少之又少。失望之余,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犹如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孙中山很快便与苏联达成有关协议。1923年秋,派蒋介石等人赴苏联考察红军的组织与训练,仿照苏联模式,在广州黄埔岛上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后来人所共知的黄埔军校。苏联派来军事顾问,运来武器弹药予以实质性的帮助与支持。在组建黄埔学生军时,孙中山采取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党军制度”——党凌驾于军队之上,军队成为政党的工具,牢牢控制在党的手中。这种党军制度很快便以其坚强的意志、严格的服从、铁的纪律使得国民党武装力量在政治、军事素质等方面完全超过了军阀武装力量,由黄埔学生军推行于驻扎在广东的其他革命军队以及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确保了国民党东征北伐的一系列军事胜利。
先是施行“党军制度”,党掌控军队;然后是“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将提高党权,加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作用视为推动国民革命的关键,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
可见短暂的民主化实验失败之后,政治精英们已经失去了建设宪政民主制度的信心与耐心。
当然,在此我们应该看到,孙中山推行以党治国,并非一党治国,而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然而,当中国国民党结束北洋军阀统治,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于1928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党国体制取代民国宪政制度之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此完全中断。
南京国民政府彻底篡改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本原思想,抛弃了他的“三大政策”,建立的是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治国政治体制,施行的是“领袖集权”的主席制。其中心内容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借口,反对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曲解“以党治国”含义,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党派、团体;为“一个统帅”大造声势,确保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自1901年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到民国创立,乃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基本上得到了保证;不同政见的政党,其活动也属合理合法;公共人物特别是那些握有实权人物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受到大众传媒的跟踪与监督。而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后,人民的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没有了,书刊被查封;除国民党外,视其他政党为非法,监禁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中国国民党一党坐大、一党专制的结果,完全走向了孙中山一辈子追求的民主政治的反面,特别是为夺取政权而建立的“党军制度”,更使得民主宪政最起码的基础——军队国家化成为泡影。其实,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对“一党专制”的危害有所预见,在改组同盟会时,就曾力图避免一党专权,认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又说:“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可一连串的失意与失败,使得他“急火攻心”,一心执著于打倒北洋军阀,夺取革命政权,却疏于对一党专制的防范……
一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集权政体、封建愚昧、专制恐怖如沉沉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民主、宪政与自由,成为只可追忆、无法抵达的美好梦想。中国民主之发展,真可谓一波三折,进一退二,正如蒋梦麟所言:“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一段并未完全消逝的历史,便愈益觉得宋教仁之死,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挫折实在太大,所造成的影响是太深刻了。由直接杀手、间接杀手、幕后杀手、真正杀手等一系列大的小的、明的暗的、有形的无形的、伪善的狰狞的杀手们所组成的庞大的杀手集团,杀死的不仅仅是宋教仁个人,而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每当我们想象着宋教仁被刺的那一瞬间,便觉得一颗阴险的子弹已化成无数,正猖狂地呼啸着往来穿梭于头顶的万里长空;一记沉闷的枪声也变成了声声惊悸的雷鸣,在我们的胸腔无休止地隆隆作响——宋教仁的个人悲剧早已演变为历史、民族、国家的悲剧: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土壤过于深厚,民主自由的空气过于稀薄的国度,宋教仁似乎就此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身后,不仅没有无数个宋教仁的站立与前仆后继的悲壮,就连第二个宋教仁,也没有出现……
一个早已习惯造神与下跪的民族,尝试着站起身来挺直腰杆,看似容易,实则何其难也!
跋:历史的杠杆
很长一段时间,我视野里的中国近代史,是教科书里的近代史,是强势媒体笼罩下的近代史。这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剥削的历史,是一段晦暗、屈辱、压抑、丧气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我不愿提及,不愿涉足,害怕所引起的苦痛使我难以忍受,害怕那片黑暗的天空将我吞没,我尽可能地,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又不得不浸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更是耗费了我大量的单元时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进入越深,了解越多,特别是触摸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与局部细节之后,对近代史的认识,竟发生了较大改变。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历史,被利用了的历史。
重读、深读、细读的过程,也是去蔽与还原的过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同样适合于中国近代史。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专制的,又是民主的;既是愚昧的,又是科学的;既是落后的,又是进步的;既是黑暗的,又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腐朽败坏的时代……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汇集一身、纷纭复杂、交错并存,它们在对立中统一,在冲突中转化,在涅槃中新生。
而教科书与过去的宣传告诉我们的是,以鸦片战争为肇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干涉、禁锢、遏制了中国的进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愚昧、腐败、积贫与积弱。一句话,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乎所有灾难,全由帝国主义一手造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学贯中西,早年推崇西方文明,晚年又回归孔孟的严复认为,中国的病症并非由帝国主义负主要责任,其困境与落后百分之七十来自“内弊”。
严复的这种认识,无疑相当清醒而深刻。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