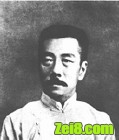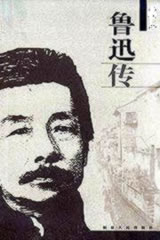鲁迅-第2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7〕指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十二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8〕杨荫榆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召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她所匿居的太平湖饭店开会,提出请警察迫令被开除的六名学生出校、提前放暑假等主张,以破坏学生运动,因受到部分与会者反对而未得逞。(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晨报》消息)
〔9〕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杨荫榆开除刘和珍等六人后,给学生家长发信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夙仰贵家长平昔对于家庭教育,甚为注重,而于子女在校之品性学业,尤极关怀。为此函达,并盼谆属照常勤学,免为被退学生莠言所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北京《晨报》)
文摊秘诀十条
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2〕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3〕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EE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
〔2〕胡适之(1891—1962)即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育界名声较大。
有些人提及他时便常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
〔3〕墨翟(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杨朱,战国时魏国人。
胡怀琛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第十六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月)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两文,据“墨”字本义为黑、“翟”与“狄”同音,而断言墨翟为印度人。
这里说“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杨朱是澳洲人”,是对这类“考据学”的讽刺。
(按“翟”字本义是一种长尾野鸡,“杨”与“洋”同音,故有此谐语。)
文学救国法
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
〔2〕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
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一,取所有印刷局的感叹符号的铅粒和铜模,全数销毁;并禁再行制造。
案此实为长吁短叹的发源地,一经正本清源,即虽欲“缩小为细菌放大为炮弹”而不可得矣。
二,禁止扬雄《方言》〔3〕,并将《春秋公羊传》《谷梁传》〔4〕订正。
案扬雄作《方言》而王莽篡汉,〔5〕公谷解《春秋》间杂土话而嬴秦亡周,〔6〕方言之有害于国,明验彰彰哉。
扬雄叛臣,著作应即禁止,公谷传拟仍准通行,但当用雅言,代去其中胡说八道之土话。
三,应仿元朝前例,禁用衰飒字样三十字,仍请学者用心理测验及统计法,加添应禁之字,如“哩”“哪”等等;连用之字,亦须明定禁例,如“糟”字准与“粕”字连用,不准与“糕”字连用:“阿”字可用于“房”字之上或“东”字之下,〔7〕而不准用于“呀”字之上等等;至于“糟鱼糟蟹”,则在雅俗之间,用否听便,但用者仍不得称为上等强国诗人。
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
四,凡太长,太矮,太肥,太瘦,废疾,老弱者均不准做诗。
案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身体不强,诗文必弱,诗文既弱,国运随之,故即使善于欢呼,为防微杜渐计,亦应禁止妄作。
但如头痛发热,伤风咳嗽等,则只须暂时禁止之。
五,有多用感叹符号之诗文,虽不出版,亦以巧避检疫或私藏军火论。
案即防其缩小而传病,或放大而打仗也。
EE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感叹’二字,……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他对新诗所用的感叹号加以统计后又说:感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
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3〕扬雄(前53—18)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汉成帝时他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汉,又做了王莽新朝的大夫。
《方言》,搜集西汉各地方言和异体字编辑而成的辞书,共十三卷。
〔4〕《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齐语。
《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鲁语。
《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四二年间鲁国的史实,相传为孔丘所修。
〔5〕王莽篡汉王莽(前45—23),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汉孝元皇后侄。
西汉初始元年(9)篡汉称帝,国号“新”。
〔6〕嬴秦亡周指东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昭襄王灭周。
〔7〕“阿房”即阿房宫,秦始皇建造的宫殿。
“东阿”,地名,即今山东阳谷阿城镇,春秋时鲁庄公与齐侯会盟地。
闻小林同志之死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EE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第四、五期合刊,原为白文。
小林,即小林多喜二(1903—1933),日本作家。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兼书记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逮捕,毒打致死。著有长篇小说《蟹工船》、《在外地主》等。
我的种痘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
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2〕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
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
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
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
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
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
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
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
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3〕,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
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4〕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
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
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
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
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
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5〕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6〕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
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
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
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
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
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
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
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
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
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