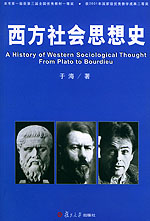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J。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 378
附:1947年的补充
1947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由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马托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产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观。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都用它的标准校正杂志和报纸。 杂志使人感到非常艰难。 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几乎给它提供了特权的地位。 但是,教会生活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教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自由。 在俄国,宗教运动有无可怀疑的增长,在俄国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强的。 由于革命与战争所经历的体验,在俄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很重要的精神过程,这个过程还不能自我揭示出来。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会中,在高等的教会等级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复到16和17世纪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为拯救个人以达永恒生命的独特的宗教。 俄罗斯关于社会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关于
…… 379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563
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宗教思想的课题是没有的。 这种教会的保守方向正是苏维埃政权所鼓励的。 民族感情的增长可能是得到赞许的。 但是,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会代替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样,全面发展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也使人厌恶。 与此相联系,最使我苦恼的是最后两年里在侨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决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敌视它,排斥革命后俄国的一切。 然而,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对革命在人民的历史命运中的意义的态度,对苏维埃制度的态度,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并不能等同起来。 我可以承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成果的积极意义,可以在苏维埃原则本身中看到很多肯定的东西,可以相信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群众,同时,对现实的苏维埃政权我又可以作很多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专政我可以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像以前一样,在侨民中是很孤独的人。 当正统的东正教决定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建立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即“如果不是由于上帝,那么也就没有政权”之上时,使我特别地厌恶。 帕夫尔的话有着历史的意义,而没有宗教的意义。 这些话是教会被奴役、奴颜婢膝的根源。 我对在苏俄产生的很多事物(我很好地了解其中所有丑陋的东西)持批判态度,特别的困难是我感到需要在敌视我的祖国的世界面前保护我的祖国,不能协调地解决这个问题,使我感到痛苦。 在最后的时间里我重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两种本原:从一方面看,是贵族的本原,对个性和创造自由的贵族式的了解;从另一方面看,强有力的历史命运感,不允许
…… 380
63自我认识
恢复到以前,从宗教根源中得出社会同情。 我不能不将这两种本原结合于自身之中。 我继续想到,在俄国,变化与改善只有从俄国人民的内在过程中产生。我这样想了25年,而且和大部分侨民绝了交。
G1947年春天,剑桥大学授予我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这被认为是很大的荣誉。 在一个欧洲国家里,我还没得到过像在英国这样的赞许,对我的思想这样高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在我被逐的沉重年代里支持着我。 过去,俄国人中得到名誉博士学位的有柴可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这与其说是承认功绩,不如说是承认学问的水平。 我一直不很喜欢学院的圈子,认为自己是一个过于“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家,比起学者型的哲学家来,我更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此外,我不是神学家,而是宗教哲学家。 宗教哲学是非常俄罗斯化的产物,而西方基督教始终不将它与神学相区别。关于上帝的对象我写了很多,剑桥大学和它的神学家注意热爱自由的方向,它认为我比同样列为候选人的卡尔。 巴特和马利丹要好。 7月我为了接受博士学位而到了剑桥,像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要举行极为隆重的中世纪式的仪式。穿上红色礼服,戴上中世纪式的天鹅绒帽子,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们在大厅中庄严地行进。 神学是科学中最高的,作为神学博士的我走在最前面。 我的后面,则是外交事务大臣贝文和印度总督韦维利元帅,他们获得了法学博士。所有这些很少适合我的本质和特点。 我从各个方面去看
…… 381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763
待这一切。 我想到了自己命运的悲苦。 在这个春天从瑞典传来消息,说我成了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我立刻想到,我未必能得到它,为此所需要完成的一步,我没有做。 非常不利的是,我是俄国流放的犯人。 我经常听到说,我登上了“名人”的高位,人们很难相信,这对我很少带来喜悦。 我一直感到自己是完全不幸的,这种不幸不是根据外在的命运,而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结构,由于不可能体验满足,由于不喜爱什么最后的东西,由于忧郁的倾向,由于经常的不得安宁。从内在的方面我还应说一说。我已经变老了,生命也疲劳了,虽然精神还很年轻,并且还迷恋着创造的智力。 但是,我,和我的亲人一样,被各种疾病搅得不得安宁。 此外,我很不会处理物质事情,不能从自己的名气中得到利益。 经常体验物质上的窘境。秋季,(日内瓦国际会议)邀请我作报告和参加集会,题目是“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去掉了难以忍受的签证等等的麻烦以后,我同意了。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济济一堂。日内瓦的“Rencontres”
组织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瑞士人,特别是罗曼语系的,非常敌视共产主义。然而,在10个报告中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作的。 也有没作报告但很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很大的宽容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Rencontres”
中所起的作用使我惊讶:一些人宣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是所有的人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打转。 我感到自己被抛到50年以前了,那时显示出,不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来说,而且从对它的内在洞察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
…… 382
863自我认识
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专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定的。 但是,我不想去迎合对唯物主义的批判。 对我来说,在唯物主义中有基础性的东西,我想,世界转向浅层时,可能需要经过唯物主义,精神的运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存在于俄国和欧洲的——则被挤到一旁。在“Rencontres”
中有具有唯灵论方向和具有很高知识和精神水平的人,他们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有水平,但是他们没有成为注意的中心。 这对于时代来说是很有特点的。我自己起了充分积极的作用,我的报告吸引了甚至是最多的听众,不过我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我很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某些社会的真理。 我并不感到自己是完全轻松和自由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过分地抨击,因为所有的时代都感到,对世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指斥的,是要崩溃的,但是希望精神不要泯灭。 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批判的回答是很无力的。但是,在它的回答后面可以感到有组织的力量,意识的压力。 与此相比较,历史上的基督教没有活力,它的活力已经成为过去。 这完全与我关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思想相吻合。 但现在这个过于浅薄但又有力量的环境难于理解我的思想。 我重又尖锐地感到我孤独到怎样的程度。 我不能在有组织的宗教教会上讲话,当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社会进程结束时,我转向未来的世纪。 我的生活的基本矛盾一直重新自我显现。 我是积极的有能力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又极端的忧郁,向往着另一种,完全是另一样的世界。我还想写一本关于新的精神和神秘主义的书。 它的中心
…… 383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963
是我对人的创造的巫术行为的生命直观。 新的神秘主义应当是巫术的。
…… 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