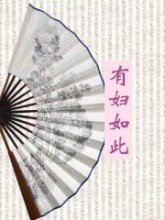废驸马,如此多娇-第7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
她哭着离开他还温热的身体,看看四周,在发现不远处的大水潭后立刻将一块石头投了下去。当石头落水,发出轻微的响声,在水面上荡起层层波纹时往旁边的树林里钻去。
黑衣人以轻功直下山坡,看了看地上躺着的贺飞扬带血带伤几乎不辨面容的尸体,随后便往树林跑去,却在瞧见一旁水潭上的波纹时立刻停步在上面审视了片刻,跳下水去。
树林里茫茫一片不辨方向,月光从树顶照下来只给了里面幽幽的一点光芒,宣华也顾不了脚下的磕绊、身侧的阻拦,打树枝荆棘间穿过,前路望不见光明,却不敢回头去。许久不哭,泪水的味道如今尝来特别咸。心里的悲痛,仇恨,竟不比当初堕胎时轻。这一次的重逢,竟是来得匆匆去得匆匆,晃如梦一场,她几乎就要以为,父亲从来没出现过。
一边哭一边想,一边不辨方向地拼命奔跑。若是普通的贼匪,她或许能利用一点小伎俩将对方迷惑住逃跑,可对这一拔刺客却不能。她能肯定,用不了多久,那人就会发现下水的不是她,然后会理所当然地朝树林这边跑来,而以那人的速度,追上她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是什么人?是什么人能请到这样的高手来杀她?宣华第一个便想到了二皇子,却又不敢相信他培养了这样一批人。或者,二皇子也和太子一样,竟勾结了江湖上的杀手组织?可二皇子,似乎没那样的财力。
哪怕她用尽了全力也只是越跑越慢,宣华感觉到了自己严重的体力不支,只觉得再跑下去心肺都要喘了出来,实在无力之余,扶住了身前的树干回过头去,这一看竟吓了一跳。原本身后还是黑黑寂静的一片,还没松口气,就见黑暗中有什么在移动,只是定睛细瞧的一瞬间,那移动的东西就因距离的拉近而能辨清形状,竟是黑衣人。
这么快,竟然这么快!那一刻,她几乎想到了钟离陌,觉得这人的武功都能和钟离陌相提并论了,可那怎么可能,钟离陌是禁卫府的大阁领,禁卫府是天下间最高手云集的地方,而禁卫府大阁领又是禁卫府数一数二的高手,外面的人与他们又岂只隔了一个档次?
就算知道自己的速度与对方完全不可比,她也唯有跑,此时此地,独她一人,除了拼了命的往前跑,她别无他法。身体是那样虚脱,以至于觉得都要被自己丢下了,自己只带着灵魂再跑。
身后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她心中开始无法言语地慌乱,想快却快不起来,要再使一次力,脚下却被什么一绊,重重扑在了地上。
地上是厚厚的树叶,她立刻要撑地站起继续往前跑,却一下子看见眼前的一根小指粗的生锈铁杆,顺着那铁杆往旁看,只见那铁杆是牢牢固定在旁边树上的。心中一惊,小心地扒开眼前的树叶,果真看见个金属的夹子。
这……是不是上天给她的最后希望?
宣华又迅速将树叶盖上去,从地上爬起来,跃过那夹子往前跑,才跑出几步,黑衣人便袭至身后,以与山坡上相同的姿势要跃起给她一剑,却在跃起前脚点地时闷哼一声,没能跃起来,反而沉沉单膝跪在地上,那一只点在地上的脚动也不动。
宣华回过头知晓成功,才要松口气,只见那黑衣人神色一凛,当即便条件反射地趴倒在地。这一趴,真真是救了她自己一命,这黑衣人果真不是一般人,脚踩进兽夹只是闷哼一声,而且在身体受重伤时想到的第一个仍然是目标,没有去看自己的脚,却执了手中的剑朝眼前的目标飞去。
宣华的动作自然没有他快,可她在觉察到他眼神的变化时就往下蹲,竟真让她避开了这一剑,那剑疾速向前,插进了她身后的树干上,竟埋了好几寸深。。
射出了剑,黑衣人再无其他能伤她的武器,这才一边盯着她,一边坐下身来去看脚上的兽夹,只是一瞬的时间就开始用力开起了兽夹。
宣华不知道兽夹还可以自己解开,黑夜中也不知道他在以什么样的方法解开,但看他立即动手的样子便知道他对兽夹定然是有所了解的,而且用的方法说不定真的可以将这兽夹打开。
怎么办?她原以来只要用兽夹困住了这人自己便能慢慢逃走了,没想到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能自己解困,然后负伤追到她,再杀了她。此时此刻,她完全不怀疑这人有这样的本事。
别无他法,宣华立刻跑到身后那一把剑跟前,握了剑柄将剑往树干外拔,本以为只是轻而易举的事,却扎得十分深,直让她用了全力才得以拔下。回头再看黑衣人,他一边弄着兽夹,一边直直看着自己。不能多等,宣华只稍稍歇了口气就提着剑往黑衣人走去,他的一双眼眸也盯着自己,两相对峙,宣结转到他身后,用力握了剑朝他颈上挥去。
逃命,流亡
没想到黑衣人竟瞬间将上半身闪到一旁,右臂抬起,手握拳,在肩膀上方将剑身反手捏在了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爱偑芾觑
这,是宣华万万没想到的,她竟又一次低估了这黑衣人的本事。本以为他被困住了脚便是他为鱼肉自己为刀俎,没想到他有这样的闪避速度,又有这样的力气,在重伤之下还能以单手夹住剑身。
她用力拔剑,却拔不出来,反而,他那一头的力量越来越大,只是背朝她,反手抬起,竟将剑寸寸往他那边夺去。
他的后劲她不知道,而她的后劲却是没有的,刚才已是用了最大的力气,越往后,她的体力便越不支,如此下去,她只能被他拉得渐渐往他背后移动,到最后若不放手,自己就会被他拉得移至他身后或是直接栽下去倒在他怀中,那时他要刺死她或是掐死她都随他作主;若放手,那她也许暂时能躲开,剑却又回到他手中了。
无论是什么情况她都不愿,然而眼看力气用尽,剑一点点往他移去,自己努力固定着也忍不住要往前移动脚步,她唯一的选择便是放手,将剑给他。
宣华看着四周,希望能找到一点点的希望,然而四周只有树,地上只有树叶和几块石头,别无其他,失望之际,脑中突然一闪,她又看向那块就在她脚边的石头。
最后一搏,她突然放了手,然后立刻弯腰搬了脚边石头往黑衣人的头砸去。
黑衣人才拿了剑,正翻过剑去握剑柄,只觉脑后有重物袭来,立刻低头,那块石头正好砸在了他后脑上。宣华并没有那样的力气让石头平行飞出去,而黑衣人习惯地以为若有东西攻击定是平行飞出的,一低头,却正好接住了重重下落的石头。
哪怕他武功再好,头也仍是最脆弱的地方,那一块石头砸了他后脑后在他额前落下,又掉在了他被兽夹夹住的腿上,这才滚落下地。
宣华仍不敢大意,砸了石头后就立刻后退,怕他又反手拿剑刺向她,没想到他低着头,握着剑了手抬了抬,竟没能抬起来,有红色的液体沿他后脑往后淌去。
宣华不再迟疑,再次搬起地上的石头往他头上砸,砸三次才砸中两次,再砸时他已倒了下去。
看着那满头的血满地的血,宣华忍着心中的颤抖,再次补了一块石头,没砸中头,只砸在了颈上,那人却躺在地上再没了动静,握着剑的手也松开来。
宣华知道,他是真的没有意识了,要不然他是不会松开剑的。这时才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喘息着缓缓上前去,蹲下身扯开他沾了血满是温热湿濡的黑色面巾。
意料之中,不是熟悉的脸。然而她想,就算知道是什么杀手组织也好,这样以后定能查到幕后主谋。如此想着,便立刻在黑衣人身上翻找起来,果真在腰间翻到一块牌子,有些沉重,似乎不是一般的质地,掏出来一看,顿时让她愣住。
金色,看重量似是黄金,上面赫然刻着个“禁”字。
禁……禁……她想告诉自己不过是巧合,不过是另有个民间的组织与“禁”字有关,可却无法说服脑海抹去那些相关的记忆——她与钟离陌,有过无数次的床榻纠缠,自然见过他随身带着的身份象征。那是禁卫府的大阁领金牌,比这一块华丽精致了许多,却仍能看出是出自一处的,而且那金牌上,也是刻了个“禁”字。
除了禁卫府,谁敢对公主下手?除了禁卫府,谁能将五百名兵士迷晕?除了禁卫府,谁能有这样的实力与行刺素质?钟离陌不也是如此么,行动敏捷,悄无声息,坚毅谨慎,对谁也毫无畏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禁卫府,这些人是禁卫府的……如今的禁卫府不是钟离陌在统领,那杀她的人或者是聂庭,或者是聂庭所派,而聂庭的主人是谁?皇上……是,皇上……她的母亲。
也许,聂庭也和钟离陌一样并非全心效忠皇上,也许他是帮着别人在做事,也许他帮的那个人就是二皇子,可是……可是她有最起码的判断,若聂庭是替别人做事,他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大动静?怎么可能一下子出来好几个人?怎么可能露出一点破绽来让母皇知道他的二心?
母皇,真的是你吗?是你要杀我,是你杀了父亲?
宣华只觉得瞬间天昏地暗,无力地伏在地上痛哭流涕。
……颖州城内,宣华一头乱发,一身男人的粗布衣服,抹黑了脸,无力地坐在了墙角下。街市之上,带着些许萧条。正值天寒地冻之际,街上本就少人,更何况早饭已过,许多卖面食早点的铺子已开始关门,空剩一张招牌。倒是有几家酒楼、供应饭食的小店开始开门迎客,虽未到正午,却有阵阵饭菜香从里间飘出来。
街上敲饭碗乞食的人们三三两两缩在各处角落,见无人路过,只是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些酒家、饭馆,或是旁边未收摊的包子铺。
宣华的目光,也不自觉朝飘出食物香味地方投去。从树林中逃出,本可朝京城方向去,可想着身后的银面卫,她只好放弃京城方向,回到了颖州。料想银面卫定会往京城方向追去,所以反向而行的她应该能在颖州城得到片刻安宁。然而这片刻的安宁却一点也不安宁,这两日,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前路在何方,只是一遍遍想着那被她砸破头的黑衣人,想着那一块金牌,父亲的模样,还有京城那位女皇的模样。
有多想,多想去问她一句,是不是做了皇帝的人都这样铁石心肠、断情绝爱,是不是在她心里,从来就没有自己这个女儿,是不是父亲死,自己死,对她来说都无所谓。
母皇……母皇……寒风阵阵,吹得酒家的幡子往南直飘,吹得她脸上、颈上如刀割般疼痛,昨日一整天不曾进过粒米的腹中承受着从未承受过的饥饿,可饶是如此,她也希望这身上的煎熬来得更强烈一些,好让她忘了心中的痛楚,全心想着如何让身体好过些。
钟离陌又如何了呢?母皇对她已动杀心,心中或许对钟离陌有怀疑,只怕他也不会幸免于难吧……说来,倒是她连累了他,而她连累的,又岂只是他?
有富贵人家的轿子过来,前面的几个乞丐立刻将碗往前伸了伸,甚至有人端着碗以愁苦求怜的目光围了上去,轿子旁边走着的嬷嬷见有人靠近眼中带着不悦的神色,像没看见他们一样目不斜视地往前而去。乞丐们见这富人无心施舍,便都散去,伸了碗的也又将碗放在了地上。
没想到轿子经过宣华面前时,那嬷嬷朝这边看了看,却见这人头也不抬一下,身前也无碗,只是呆呆坐着,竟从腰中掏了两个铜板朝她扔了过来。
前个前到。铜板精准地滚到宣华面前,宣华这才抬头,愣愣看向眼前的人,只是普通的嬷嬷,此刻竟是高高在上站在她面前。那嬷嬷看着她的目光中露出些许怜悯,而后收回目光,随着轿子往前走去。
宣华看着眼前的铜板,隔了好久才将那铜板捡到手中,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竟与旁边那些乞丐成了同样的身份。她何以,沦落至此了?其实沦落至此也不算什么,她的尊贵身份,她的无上荣耀,本就是那个人给的,那个人不再给,她不就什么也没了?那……她现在不是宣华公主,那她是谁呢?原本的路,原本的归途不再属于她,那她又该回到哪里去?
腹中阵阵难受,让她不得不收回意识,又将目光投向飘来香味的地方。
依次往左,是虔德酒楼,实惠面点,胖三鱼馆,再隔几家,便是一个小小的包子铺。从这里可以看到铺子上挂着块木牌,上面写着:馒头两文,白菜包子三文,猪肉白菜包子四文。此刻已不再有生意,铺里的老板正收拾着蒸笼。
最便宜又最填肚子的,当是馒头了吧。拽了拽手上的两个铜板,宣华撑着从地上站起身,往那包子铺走去。
到包子铺前,宣华站了好久才能够开口,极其不自然又小声道:“一个馒头。”说着,将铜板递了上去。
老板看他一眼,一边将蒸笼往后搬,一边说道:“馒头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