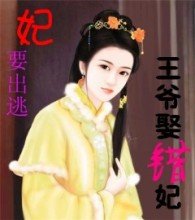大雨过后,我一直都在 [出书修订版]-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起来是个很悲情的故事。”
“但我觉得这是他爱她唯一的可能,爱情就是这么不公平。”
他起身去流理台上把咖啡端过来递给她,也光着脚在地板上坐下来,跟她并肩靠在床尾。
“《解构生活》呢?”
“有点难看的电影,除了裘德洛。”她喝了一口咖啡,加了红茶和牛奶,很棒的红茶拿铁。
“《爱情回水》?”
“画面很火辣,故事很纯情,美少年和老女人,大概英国人都喜欢这个调调。”
“谁挑的?不是我吧……”
她笑着用CD盒敲他的胳膊:“这个呢?《窃听风暴》,你挑的……”
“嗯,这个好,学德语时看过,导演是个天才,我还推荐这个,《幻想之痛》,德国电影都不错,比如《疾走罗拉》。”
“提尔?史威格很有男人味,”她翻过去看背面的简介,“……是励志片。”
“原来你喜欢这一型?”
“纯欣赏,”她放下碟,回头捧住他的脸,晃了晃,“你在吃醋?”
“哼哼,”他抓住她的手腕,作势要咬她的手指,“难道看我还不够?以后只准看我一个。”
她用CD盒盖住脸,仰头笑倒在床上,原来这人也这么霸道。
那天上床很早,两人喝了咖啡都睡不着。他房间里有一台袖珍的组合音响,他们开了音乐,把声音调小,关了灯对着天花板聊天,只剩红色的指示灯在半明半暗中一闪一闪。
“跟我说说你的事。”他帮她把枕头垫高,让她靠的更舒服些。
“你想知道什么?”她慵懒地蜷着身子,把腿支在他腿上。
“先说说莫斯科呢……”
“莫斯科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或许以前比较冷,我记得我到的第一天是零下27度,那可能是我在莫斯科那几年温度最低的一天……天很蓝,树很绿,泥土很黑,空气很干净,起码比这里干净,但是天气不太好,一年当中,几乎有8个月看不到太阳,所以俄罗斯人总是很忧郁……”
“有多忧郁?”
“连神父都很忧郁,”她笑,“虽然忧郁但是又很乐观,你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知道了。”
“嗯,还有呢……”
“机场很破,破得像我们这里90年代的火车站,海关警察看心情决定要不要扣你的行李。不过从机场往市区去的路上都是高高的白桦树,还能看到有轨电车,很像老电影里的场景……在我们这个时间,莫斯科的天还没黑,进入夏令时后,这个高纬度的国家会出现白昼之夜,太阳在晚上十点前不会下山……”
“那睡觉岂不是很痛苦?”
“他们不会,白天变长了,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很多俄罗斯人会选在七月和八月的时候结婚,或者去乡村庄园度假……去莫斯科一定要吃коломенское(沙皇庄园)的烤饼,嗯,还有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每年都过很多节日。不管男女都很会打扮,表情冷漠又堕落,几乎每一个都像从杂志上走下来的。”
“你呢,一个人在莫斯科怎么生活?”
“我读的学校是普希金俄语学院,简称普院,因为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之父,他们喜欢用名人来命名大学,像列宾美术学院,还有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学过他的诗,叫什么来着?”他抓抓头发,笑了,“对不起,我对这些不敏感……”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Еслижизнитебяобманит;我背给你听。”
她的声音在夜里有点哑,念起俄语来有一种淡淡的忧伤,那是他不熟悉的一面。
他摸摸她的脸,语气温柔:“怎么背这么熟?”
她笑:“这是功课,整个大学和研究生就研究这个了,不熟也得熟。”
“在莫斯科……一直是一个人吗?”他的手指卷着她的头发,装作不经意。
“嘿,你想问什么?”她半支起脸,笑盈盈得问他。
“噢,被你看穿了……”他笑,屋里并不是太黑,他看起来竟有些腼腆,“你不想说的话也可以……”
“我在莫斯科有过五个情人,”她用很认真的眼神看着他,伸出手指比划,“一个是韩国留学生,富二代,开顶级跑车;一个是医生,牙医,拔牙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是木材商,在圣彼得堡给他做过翻译……”
“还有什么?飙车党?酒鬼?牧师?”他一副你还可以继续往下编的表情。
“还有出版商跟建筑师,都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不信。”他摇头。
“真的。”她点头。
“真的不信。”他用力摇头。
她扑哧一声笑了:“不信就算了……”
他还是摇头:“我玩不过你,你太坏了……”
☆、七、(2)
后一个礼拜依然是他过来找她,他们去超市大采购,她很意外他也是爱逛超市的人,他们一起坐在地毯上列要买的物品清单,从牙膏到清洁剂,然后开车去最近的大卖场,在购物前先去逛顶层的特力屋,选浴室用的防滑垫和漱口杯,牵着手在按摩椅里睡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导购小姐来把他们叫醒。结了帐出来,超市外面有投币的那种自助投篮机,他看到,突然把她拉了过去。
“你要干嘛?”她看了眼一旁玩得兴高采烈的高中生,有点惊讶。
“等我赢个小熊给你。”他说着,把手中的购物袋放在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要投进去。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小熊?”夏耳睁大眼睛看着他。
“刚才在特力屋,我看到你多看了几眼。”他说。
夏耳愣一愣,然后微微笑起来,她早就过了拥有公仔的年纪,就算喜欢,多看两眼也就过瘾了,没想到他会这么细心。
“你的技术行吗?”她故意说。
“等着瞧。”他眯起眼睛,很嚣张地扬了扬下巴。
夏耳好笑,却没有阻止他。她看着穿着休闲衬衫和西裤的安梁挤在一群高中生里帮她投篮,他单手投,动作快得吓到她,实在没法把眼前这个孩子气地像个大男生的安梁跟那个做新闻直播的安梁联系起来。唯一相同的一点是,他投篮的时候同样十分专注。
夏耳喜欢一个男人做事专注。
计数结束的时候,面板上红色的数字停在297,安梁把手中最后一个球丢进篮筐,回头对她遗憾地耸了耸肩:“要不再来一次?”
“我饿了,我们去吃东西吧。”夏耳体贴地转移话题。
他好像有点不服输,不过还是无奈地笑了笑,说:“好吧,下次我一定会投到300个。”
并肩坐在快餐店落地窗前的高脚凳上时,夏耳一直在笑。
安梁吸了口饮料,握一下她的手:“笑什么?”
“没什么?”夏耳摇头,却还是笑。
“一定有什么。”他盯着她不放。
“好吧,”夏耳投降,“我觉得很开心。”
安梁愣了愣,也笑了,握着她的手更紧了些,却没有说话。
“怎么了?”夏耳转过头去。
“没什么。”他晃着饮料里的冰块,摇摇头。
“一定有什么。”夏耳盯着他。
他抿了抿唇,好像有些不好意思,把眼微微别开说:“我以为你在笑我。”
“我为什么要笑你?”夏耳还是看着他。
“我怕……”他转过视线来看她,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刚才很幼稚……”
“的确是很幼稚。”夏耳喝着饮料,面无表情地说。
他傻眼,然后突然拿装着冰块的饮料杯贴在她脸上,夏耳大叫,他哈哈大笑。
她也去看过他一次,但是她不会开车,而他总不会放心让她一个人坐车回程,总是开了车送她回家然后又回去,这样来回折腾,还不如他直接来找她。
有一个周末他们留在屋里各自工作。她做兼职的笔译,他打完报告后靠在床头抽了她书架上的书看,后来又用她的俄语电子词典玩俄罗斯方块,等她合上电脑的时候,他已经玩通关了。
“晚饭吃什么?”
“叫外卖好了。”
“不如去外面吃吧,我有礼物送给你。”
“是什么?”
“先不说,去了就知道了。”
他还装的很神秘的样子,任她怎么逼问,只是笑:“别急,待会儿保准你就高兴了。”
他居然是带她去做旗袍,那是一家专门做中式衣服的店,而且最资深的老师傅很摆架子地只接受熟人引荐,轻易不接活儿。
“你怎么找到这的?”她站在门口,看着屋檐下的那块招牌,三个字力透纸背,古意盎然。
“前几天我二姐来看我,穿得就是这里的旗袍,我看那个做工确实没话说,便让她介绍了帮你做一件,你穿旗袍一定好看。”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进去了先挑布,那么多花色看得眼花缭乱。他说她穿红色的好看,想要给她挑匹红色的。
她笑着不敢苟同:“那可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他也笑:“那就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再来给你做。”
是不是男人说话总是不知轻重的,她心一滞,没有敢当真。
最后挑了一匹藕荷色底子,上面有印花的,店员说她有眼光,这种花色做成短袖的小旗袍,滚了边镶了盘扣,秀气雅致,会很衬她的气质。只可惜已经过了那个天气,'。 '等做好也要留到明年穿了。
年过六十的老师傅依旧耳聪目明,给她细致地量尺寸,极为复杂,从脖子到腿,在纸上记了二十多个数字。
量到她腰身的时候,老师傅好像叹了口气:“腰粗了近一寸……”
夏耳微微垂下眼,不知道是不安还是窘困:“我今年28岁了,肯定不能跟18岁小姑娘的腰身比……”
最后量完了,老师傅一边收起皮尺,一边看着她,好像欲言又止。她很快出去,安梁还在外面等她。
“喜欢这个礼物吗?”吃晚饭的时候,安梁问她。
“嗯,我觉得很荣幸,而且有些太贵重了,很多人排队都穿不到这位师傅做的旗袍。”
“所以才要带你去做一件,师傅年纪很大了,说不定他哪天就收山不做了。”
她笑着问:“不是每个人都穿得起旗袍,你怎么知道我适合?”
“男人的直觉……”他微微一笑,“其实是我看到你夹在书里的照片,是不是留学生的晚宴?”
“嗯,几乎每个在俄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件,出国必备品之一,我当时走得很急,在民族服饰店随便买的一件,尺码不对,还被黑心的店主坑了。”
“肯定比不上量身做得好。”
“其实不用这么费心,我很少有机会穿到旗袍了,做了肯定是挂在衣橱里的机会比较多。”
“我总要给你最好的,实在不行,你穿给我一个人看就好。”
此刻分明还是快乐的,他在身边的时候,曾经的惶惑和忐忑,都会被那些不经意的喜悦和感动遮盖掉。有天早上她洗完脸,对着镜子照照,竟然发现自己的嘴角是笑的,她已经许多年没有这样带着连自己都不自觉的微笑了。安梁其实是简单的人,忠诚度极高的那种,要他全心全意接受一个人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习惯了一个人,那就真的只对她一个人好。以至于夏耳都有一种,如果能一直这么下去,那也很好的错觉。
周五的时候公司有总部的客人过来考察,夏耳兼职去当秘书接待外宾。在参观团中,夏耳看到了一个很多年没见过面的人。若干年前,她在厦门给他当过导游。这个名叫奥列格的莫斯科男子,是很典型的俄罗斯人,金发,有忧郁的眼神和苍白的脸孔,笑起来很迷人,难得是少数对中国人没有偏见的俄罗斯年轻人。他们当年在厦门认识,因为一些误会分开的时候却不是很愉快。后来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还遇上过两次,一次是在她发高烧送急诊的时候,在莫斯科生病是最悲惨的一件事,救护车会把你直接载到医院却不会联系你的亲友,也不会帮你保管私人财产,所以当夏耳从晕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她连一个朋友都联系不上。因为是公费医疗,护士除了打针和送药,不会出现在她病房里,也不会来催她缴费。夏耳就这样孤零零地在医院躺了两天,直到奥列格出现在她病房里。他帮她打电话给学校请了假,帮她缴清了医疗费,然后又给她换了新的手机。她出院的时候,他送她回学校,留了名片给她,他们却没有再联系。直到第二年的暑假,夏耳想利用假期做兼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了电话给他。他介绍她去圣彼得堡给出口木材商做翻译。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直到今天。
奥列格也认出她来,他笑得很开心:“真高兴能见到你,夏耳,看起来你过得不错。”比起前几次见面,他的中文已经说得很流利,叫人不由肃然起敬。
“我也是,虽然有点意外,不过能共事多少是一种缘分。”夏耳诚心地说。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奥列格似乎并不知道她已经回国很久了。
“去年吧,”夏耳点点头,“已经一年多了。”
“那你去找宋迟了吗?”奥列格突然问她。
夏耳愣了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