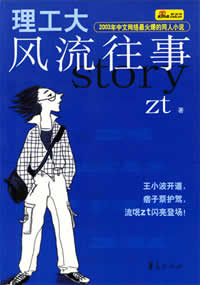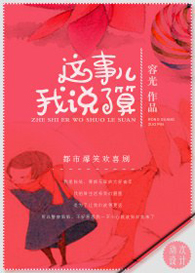音乐的故事-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W詈螅嗄甑哪谛某逋唬馕焕硐胫饕逭吒械皆嚼丛酵纯啵沼诳衽⒀荼涑砂潦右磺械挠⑿壑饕濉J┨乩退沟拇笮υ凇恫槔妓固乩缡撬怠防锵癖拮右谎樵谖颐巧砩希耱卮桃谎掏醋盼颐牵《囊庵居衷凇队⑿鄣纳摹防锔钔春痛焐俗盼颐牵∠衷谒芩阌檬だっ髁怂牧α浚母甙辽搅思蓿凰老踩艨瘢炊床患约旱某绺呃硐刖辰缫丫涑闪耸率怠5潜凰囊衾址从沉嗣褡寰竦牡鹿嗣窨吹搅苏庖坏恪=裉斓牡鹿衙确⒘瞬√闹肿樱恢置褡遄院篮妥孕诺目袢鹊酱β樱晔悠渌褡宓睦顺笔谷讼肫鹗呤兰偷姆ü!暗鹿涤腥澜纭薄亓值纳痰瓿鞔袄锾诺谋暧镎庋骄驳匦肌H欢说搅苏庖徊剑宰泳突岵磺逍选L觳抛叩秸庖徊骄突岱⒎琛5炊喾业姆杩袷羌性谒陨淼模悸蚁胧俏俗杂椤6苯竦鹿矶嘁帐跫业奶觳旁蚴且恢智致岳┱诺亩鳎哂写倜鹦缘惺铀说奶氐恪U馕弧坝涤惺澜纭钡睦硐胫饕逭呖赡芑峄搜刍枇送贰K淳褪且持我桓瞿诓渴澜绲摹6徽倩饺ネ持蔚哪歉霭哽档耐獠渴澜缛窗阉蔚貌恢耄挥谑牵窨龃蟮勰茄呙粤寺贰5鹿谡业侥岵傻纳羰被辜负跆覆簧鲜歉鍪澜绲酃O衷谒芩阌辛死聿椤な┨乩退沟暮甏笠衾帧�
这一切狂热要走向何方?这种英雄主义向往着什么?这种冷峻而严酷的意志力一旦达到目的——甚至还没达到目的——就会衰弱下来的。它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胜利。它蔑视自己的胜利,不信任它,很快会厌倦它。正如尼采所说:“德意志精神不久前还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治理欧洲的力量,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放弃了它们。”
这就如同米开朗琪罗的《胜利》,它把膝盖抵在俘虏的背上,并准备把他迅速杀死。可它却突然停下来了,犹豫起来,用迷茫的目光扫视四周,一脸的没精打采和反感,像是被厌倦夺走魂儿。
这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迄今为止留给我的印象。贡特拉姆杀死了罗伯特公爵后,立即就丢掉了手中的剑。查拉图斯特拉的疯狂大笑结束在一份丧失了勇气和软弱的声明里。唐璜的狂热激情泯灭在虚无中。唐·吉诃德在临死前发誓放弃了他的幻想。甚至连英雄本人也承认自己事业的徒劳无益,并走进没有感情的自然界要求把往事淡忘。尼采在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时,就嘲笑他们:“这些意志的坦塔罗斯〔4〕,法律的反叛者和敌人,当他们心碎、消沉时,就走来跪倒在耶稣的十字架脚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十字架也好,空虚也罢),这些英雄厌恶而绝望地放弃了到手的胜利,或更加悲惨地从世上退隐。贝多芬可不是这样克服他的悲伤的。悲哀的柔板在他的交响曲中段哭诉,但欢乐和凯旋总是响起在它们的结尾。他的作品是一位被打败的英雄的胜利,而施特劳斯的音乐则是一位获得胜利的英雄的失败。这种意志的不坚定和犹豫不决在当代德国文学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表现在施特劳斯身上就更引人注目,因为他比别人更加英雄化。于是,我们在欣赏了超人意志的全部出色表演后,得到的结局却只是“我的欲望没有了”!
而在这之中却也埋藏着德意志思想的不死的蠕虫——我说的是那些启发当代预示未来的极少数被选中的人的思想。我见到了一个英雄般的民族,陶醉在她的胜利中,陶醉在她巨大的财富、无数的伟人、强大的力量中,张开伟岸的臂膀搂住世界并把它降服,然后却停下了,被其征服弄得疲惫而厌倦,并问道:“我这样征服是为了什么?”
注 释
〔1〕这种会社基督教的味道很浓。——译者
〔2〕施特劳斯在总谱上每个变奏的开头都标明他要阐述的是《唐·吉诃德》原著中的哪章哪节。——原注
〔3〕演奏施特劳斯晚期作品的乐团十分庞大。——原注
〔4〕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站在齐下巴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口渴欲饮时,水即流失;肚饿欲食时,果子就被风吹去。——译注
马勒与施特劳斯〔1〕
古斯塔夫·马勒现年四十六岁(本文写于1905年)。他在德国音乐家当中属于具有传奇色彩的那种,颇像舒伯特,介于小学校长和牧师之间。他长着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长脸,发尖的脑袋上长着一头蓬乱的头发,前额秃顶,鼻子突出,眼睛在眼镜后面不停地眨,一张大嘴,薄薄的嘴唇,双颊内陷,表情疲倦而带讥讽,总体感觉是苦行僧,禁欲主义。他神经质得厉害。他像只猫那样缩在指挥桌前痉挛的侧影漫画像在德国十分流行。
他出生在波希米亚的卡利什特,后去维也纳做了安东·布鲁克纳的学生,然后成为那儿的宫廷歌剧指导。我希望有一天能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位艺术家的创作,因为目前他在德国是仅次于理查·施特劳斯的作曲家,而且是德国南部的主要音乐家。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一组交响曲。其中《第一交响曲》称为“巨人”,创作于1894年。整部作品的构造恢弘,规模庞大。作为这些结构地基的旋律有点像斧凿粗糙且质地不太好的石块,但因其本身的规模宏大及固执地重复其节奏型而沉甸甸地感人。这种节奏型的重复有点像驱之不散的魔影。如此堆砌音乐造成风格上既粗糙又学者气,和声有时笨拙有时精巧,“块儿头”大得让你不敢轻视。该曲管弦乐配器沉重而喧闹,铜管乐器占统治地位,并粗略地装饰这庞然大物颇为阴沉的色彩,使其点点闪光。该曲的基本观念属新古典主义,并相当海绵质(轻柔且富有弹性)和罗嗦。其和声结构是组合式的:我们听到巴赫、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风格同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风格对垒和较量。另外,由于马勒特别喜欢两重轮唱的曲式(卡农曲式),所以该曲甚至让人想起弗朗克的某些作品。整个《第一交响曲》像一堆奢华炫耀的古玩。
马勒这些交响曲的主要特点总地来说,是运用了乐队伴奏的大合唱。马勒说:“当我构思一幅宏大的音乐图画时,我总会有被迫使用语言去帮助我实现音乐构想的感觉。”
马勒从这些人声与器乐的结合中获得了惊人的效果,他在这方面还从贝多芬和李斯特那里获得灵感。十九世纪的音乐创作竟然很少运用这种人声与器乐的结合,真是难以置信;因为这种运用可获得诗歌与音乐的双丰收。
在他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中,头三个乐章纯粹是器乐的,第四乐章里出现一个女低音的人声,唱出下面这些悲伤而简单的歌词:
人间灾难深重;
人类痛苦不堪;
我愿身在天国!
灵魂努力想接近上帝,发出激情的呐喊:
“我来自上帝,并将回到上帝那里。”
随后是一段交响曲片断(Der Rufer in der Wüste,德文:荒野里的呼唤),我们从中听到“荒野中一个声音在呼唤”,声音凄厉而痛苦。然后是(基督教)《启示录》般的终曲,合唱团唱起克洛普斯托克致耶稣复活希望的优美颂歌:
“您将从墓中升天,您将再次复活,哦,您的尸骨,在稍事休息之后复活。”
接着宣布摩西律法:
“有生就有死;死者必复生。”
最后,全体乐队,合唱团和风琴加入到这对永恒生命的赞歌中去。
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也叫“一个夏日清晨的梦”。其中第一和末乐章是只为乐队而写的;第四乐章包含马勒音乐中最优秀的一些成分,十分出色地把尼采的话谱成了曲:
“哦,人啊!哦,人啊!请留意!请留意!留意漆黑的夜半说了什么!”
第五乐章是一首根据民间传说谱写的欢乐而激动人心的大合唱。
在《G大调第四交响曲》中,只有末乐章是有歌唱的,而且几乎具有幽默的性格,是对天堂之乐的某种孩童般的描写。
马勒拒绝把这些带有合唱的交响曲同标题音乐联系起来,虽然表现上有此之嫌。如果他是指他的音乐有其自身价值、无需要任何标题“助兴”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音乐必定总是表现某种特定的情绪或基调,表现某种有意识的心境;而且事实上,不管他喜不喜欢,这种情绪赋予他的音乐一种远超过其音乐本身的意味。他的个性在我看来远比他的艺术有趣。
德国的艺术家常有这种情形。马勒的情况确实很特别。当你研究他的作品时,你会确信他在当今德国属于那些罕见的类型,即一位自我为中心论者在用真诚来感觉。也许他的情感和理念并没真正做到真诚和富于个性的表现自己,因为它们总是通过一团怀旧之云和一种古典主义的氛围传达到我们耳中。我不禁要想,马勒作为歌剧院指导的职位以及他因此泡在音乐中必须整日研究总谱的现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对一位富于创造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读得过多更致命的了,尤其是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读他人的东西;像马勒,他被迫吸收过量的营养,其中一大部分他都消化不了。马勒也许试过去维护自己心灵的圣所的纯洁,但无用;它已被来自各方的外部因素践踏得够呛。他不仅不能把它们赶走,反而他作为乐团指挥的良心责成他接纳甚至拥抱它们。由于他日常活动繁忙,作为指挥的担子太重,他只好不停地工作,而没时间去梦幻。马勒只有辞去行政工作后才能成为马勒;他只有合上别人的总谱、退隐到自己内心深处并耐心等待自己再次成为自己之后——假如不是太迟——他才能成为自己的马勒。
他的《第五交响曲》比他所有别的作品都更使我感到他迫切需要走上述之路。在此曲中,他没有使用合唱,而这正是他前几首交响曲的主要迷人之处。他希望证明他也能写纯粹音乐,并拒绝在发表的音乐会曲目单上对此曲作任何说明,以此来让别人更相信自己的话。他想让人严格从音乐的角度来判断这阕作品。而这对他来说是一道严峻的考验。
虽然我很希望自己能欣赏让我十分尊敬的马勒的这部作品,但我还是觉得它不会以很好的成绩通过这次考验。首先,这部交响曲过于冗长(一个半小时),而且没有明显的缘由解释它为什么这么长。它旨在规模宏大,结果主要达到了空洞。那些动机(motifs)过于熟悉了。葬礼进行曲的性质平庸,行进热烈汹涌,好像贝多芬在里面正在向门德尔松学习;接着奏响一支谐谑曲,或不如说是一支维也纳圆舞曲,其中夏布里埃尔正在向老巴赫伸出援助之手。“小柔板”(adagietto)颇为柔情蜜意,多愁善感。结尾的回旋曲颇像是弗朗克出的主意,也是全曲最出色的部分,奏得如醉如狂,并从中响起一支欢天喜地的赞美诗大合唱;但整体效果却丧失在它的一再重复中;这种重复使之窒息和笨重。贯穿全曲的是一种学究气的死板和松散不连贯;它杂乱无章,行进中常遭突降的阻碍,一些多余的念头常常毫无缘由地插进来,造成整体犹犹豫豫,像枪、炮发射不出来子弹。
总之,我担心马勒是让追求力量的想法给弄糊涂了;这种想法在当今德国艺术家头脑中普遍存在。他似乎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集悲愁、嘲讽、脆弱和烦躁于一身,整个儿一个努力追求瓦格纳式宏伟的维也纳音乐家形象。没人能比他更好地表现“连德勒”舞曲和轻巧的华尔兹舞曲的优雅及哀伤的沉思;大概也没人比他更接近舒伯特那感人和煽情的忧郁的本质;他的优点和某些缺点时时让人想起舒伯特。可他却想当贝多芬或瓦格纳。他错了,因为他缺乏他们的平衡感和巨人般的力量。只要看看他指挥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这点便可一目了然。
但无论他像谁,无论他在斯特拉斯堡音乐节上带给我什么失望,我都绝不敢小瞧或嘲笑他,我坚信,像他这样一位目标高尚的作曲家,总有一天会写出一部无愧于他自己的杰作。
* * * *
理查·施特劳斯同马勒形成极鲜明的对比。他总是像个掉以轻心和不知足的孩子。他又高又瘦,颇为优雅、傲慢,似乎比当今大多数德国艺术家都更出身高贵。他目空一切,满载荣誉,十分苛求,对其他音乐家的态度绝不像马勒那样谦逊迷人。他同马勒一样神经质,指挥乐队时像在跳疯狂的舞蹈紧跟自己作品的所有最微小的细节——他的音乐像一池细水投进一块大石头掀起的浪涛。不过他比马勒要优越许多;他知道在苦干后如何休息。他天性既易兴奋又慵懒,高度紧绷的神经幸亏得到他的懒惰的平衡,骨子里还颇有巴伐利亚人对奢侈的爱好。我确信,他在耗尽了过量的精力、紧张的生活完全结束之后,他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