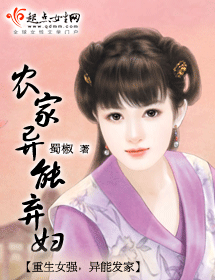爱莫能弃-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清水慢文
。
小姐
我穿越的那天晚上喝醉了。
其实我也就喝了一瓶红酒,但喝的时候肚子里没什么东西,难受又吐不出来,只觉天旋地转,向后一摔,倒在了床上。
朦胧中,我在一个黑色的走廊里飘荡,黑色但并不可怕,让我疲惫不堪的心灵能换口气。只是感觉到,没有看到,一个同样在黑暗中飘荡的灵魂与我的擦身而过。说不出什么,只知道是同样地疲惫,同样地绝望,同样地悲伤。
再睁眼,天亮了。我头痛得想吐,眼睛干得难受。我以为我还在梦里,因为我看着头顶上绣得凤飞九天百花吐艳的帐子,就知道我不在我自己的床上。
我不敢抬头,怕头更痛,就转着眼睛,想看看周围。这一看,不要紧,我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当即头痛得我大叫了一声。我抱着脑袋再看了一下我所见的恐怖景象,没消失,还在!
只见一个人赤身裸体血淋淋地被吊在我的床边外几步处,自然一眼就看出是男的。他的头低垂在胸前,蓬乱的头发挡住了他的脸。他的身上鞭伤累累,烙痕处处,脚尖离地面半尺,指向的地上有一小滩黑血。
我哆嗦起来,我是穿到牢房里来了吗?那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我了?!可这帐子,不象是牢房。。。。。。
随着我的叫声,一个女孩子战兢兢地快走了进来。她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有些黄,眉眼温顺,身材小巧。她到我身边,细声问道:“小姐,是否要醒酒汤?奴婢已备好了。”
我看她不像个监狱看守,就指着那个吊在那里的人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那女孩瞪大着双眼看着我,颤着声音说:“小姐,我没动过他。您把吊他起来后,我没动过。”
我头痛得想自己把脑袋给砍了算了,是不是我听错了?我皱着眉说:“是我把他吊起来的?!”
那女孩的声音更抖了:“是,您吊的。”
我捧着脑袋:“我干了什么了?”
那女孩说:“您把他吊起来,说要打够一百鞭,烙他三十次,看他求不求饶。。。”
我眼睛都快掉出来了:“什么什么?我干了吗?!”
那女孩忙说:“您都做到了。我听着您还给他抹了盐,另外还再打了有上百鞭子。。。”
我大喊起来:“啊?!我疯了吗我?!”
那女孩赶紧说:“小姐没疯!您就是喝醉了。”
我实在不该问下面的话,但是我这人一向二百五,问题还是脱口而出:“那他求饶了吗?”
女孩犹豫着说:“他没有,但是您烙他的。。。。。。时,他叫出了声,所以,小姐,您还是赢了。。。。。。”
我双手齐挥:“我赢他干吗呀?!没事找事吗这不是!快帮我把他放下来!”
我站起来,又头痛得大喊了一声,那女孩忙说:“我先去给小姐拿醒酒。。。”
我打断她说:“救人要紧哪!我只是头痛,死不了。”那女孩目定口呆,我来回找凳子,口里说:“他是怎么被吊上去的?”
那女孩指着墙边一处绳子说:“那绳子。。。。。。”
我仔细看,梁上有个铁环,吊他的绳子是从环中穿过,又栓到了墙角的另一个环上。我看那女孩身材细小,比我矮,就对她说:“你去解绳子,我在这里抱住他。”
那女孩大惊道:“小姐要抱他?!”
我问:“那让别的人来?”
那女孩急道说:“小姐,您从'奇·书·网'不让别的人进门哪。”
我疑惑道:“那怎么放他下来?”
那女孩说:“平时小姐就是放了绳子让他摔在地上的。”
我又大惊道:“啊?!这还不是第一次?”
那女孩终于盯着我慢慢地说:“小姐,一个月来,您几乎每天都这么吊打烙烫他一次。。。您还好吧?”
我出了身冷汗,我成什么人了我?!仔细看着那个女孩,她一脸的惊恐,不像是有坏心的样子,就问:“实话实说,我酒醒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叫什么来着?”
她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小姐,我,叫,杏花。”
我忙鼓励地说:“好名字。”
她说:“是小姐您起的,您说起个俗气的名字,别人就不会多看我一眼。”
我咳了下说:“杏花,你去解绳子,咱们快把这个人给放下来吧。”
她一步三回头地走到墙边绳子处,我抱住那个浑身是血的人,对杏花说:“现在解了吧。”
杏花几下扯松了绳子,我手臂中一沉,那个人坠到了我身上。我一连倒退两三步,到了床边,没站稳,一下子连坐带躺地仰倒到床上,摔得我大叫了一声,加上头痛,差点背过气去。那人压在我身上吭了一声。
杏花大惊失色地跑过来,连声问道:“小姐,你怎么样啊?”我喘着气说:“快帮我把他扶下躺好,我快被压死了。”
我们同时动手,把那个人翻到床上,他的手臂还是半举着的,我忙给他解了绳子,把他僵直的手臂拿下来,放在他身边。他又吭了一声。我知道血液突然回流,会十分疼痛。我抛了绳子头,见他的头发遮着脸,就用手给他捋开,一下子怔住。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两道浓黑秀美的眉毛,眉头紧蹙着。长密纤细的睫毛,如扇般覆盖在现出暗黑色阴影的眼底。挺直的鼻梁,淡白色的棱角清晰的唇紧闭着,明显咬着牙。虽有短短的一层胡须,可长得真是十分秀雅俊美。我不禁叹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家仇血债,其实,你的小姐是喜欢上他了呀。”
杏花大惊,几乎讲不成句子地说:“小姐,您从不曾,明白地,说这样的话!。。。。。。你,你,你是谁?!”
我站起身,问道:“杏花,有没有伤创药?”杏花哆嗦着,指着床边的一个拳头大的罐子。我拿起来,重新坐在那个人身旁,先用一角被子盖住了他的下身,打开了罐子,又说:“杏花,给我干净手巾。”杏花递过来,手颤抖着,看着我的神情象是看着怪物。
我从那个人的肩膀开始,用手巾先轻擦去残留的血,然后把药膏抹在他一道道的伤痕和处处烫伤上。他前胸最是悲惨,糜烂处处,血肉模糊。我尽量下手轻微,恨不能不碰到他的皮肤,手指只在药膏上滑行。他紧咬着牙,毫无声音,皱着眉头有时极轻地颤抖一下,可没有睁眼。
我示意杏花坐下,她根本不敢,抖着站在那里。我一边给那个人轻轻上药,一边低声说:“杏花,我不是你的小姐。”
杏花吓得哭起来:“那,你,是鬼吗?”
我笑:“杏花,昨天我喝了一瓶酒,醉倒后,我的魂魄在一处黑色的长廊里,与你小姐的魂魄掉了个儿。现在,你的小姐大概正从我的床上醒来,叫着你的名字呢。”
杏花哭起来说:“你,是不是,要害了我们。。。。。。”
我苦笑了:“杏花,别总想坏的事情。我现在才是害怕的人。我是谁?我日后会在哪里?怎么才活得下去?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害人哪。”
杏花破涕为笑说:“小姐,您真。。。。。。”马上又吓得不敢说话了,瞪着眼睛盯着我看。
我嘻嘻笑着说:“杏花,你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别说您了,就说你就成了。”杏花眨着眼睛不敢说话。我尽量温和地说:“杏花,我是谁?”
杏花颤抖着说:“小姐,你是当朝太傅董之鹏的女儿,董玉洁。”
我大喜过望地说:“好啊,还是高官之家,衣食无忧了!”手下正涂上一处裂开的皮肉,不注意地按了下去,那人听着没气了,我忙抬手,说了声:“对不起。”
杏花说:“老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中重臣。”
我又有些忧虑地说:“不会功高盖主吧?”
杏花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手指方抹过那人的一处伤口,伤处突流出一股脓血,我忙说道:“要疼一下。”我用手巾稍用力蘸干了脓血,轻上了层药膏。唠叨了一句:“弄好了。”那个人屏住了呼吸,就是不出声。我又要了新的巾子,继续护士大业,嘴里说:“你接着说。我有没有兄弟姐妹之类的?”
杏花说:“你有一个哥哥,董玉清。”
我笑:“玉清玉洁?清洁?加个工字,这不成了扫大街的了吗?”
杏花疑问道:“小姐,您,你在说什么?”
我忙说:“没什么。我有没有什么指腹为婚的夫君?”别我还得逃婚之类的。
杏花说:“小姐,你对老爷说过,你的夫君要自己选。”
我笑了:“这样,太好了。”我看着我旁边的人问道:“这又是谁?”
杏花紧紧地盯着我:“小姐,你真的不记得了?”
我赶忙笑:“杏花,我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你的小姐。”千万千万别忘了!
杏花松口气,看着我旁边的人说:“他叫谢审言,是原来谢忠誉御史大人的小儿子。从小文武双全。一年前,他十八岁,夺了京城诗坛首冠,被人誉为文情横溢的京城第一才子。”
我嘿嘿笑着:“你的小姐是不是那时喜欢上他的?”
杏花说:“是啊,小姐从来没告诉过别人,但那天是我陪着她,女扮男装,混在人群里,看这位谢公子一挥成诗,轻易夺了魁首。小姐一夜未眠,次日就去求老爷提亲谢家。”
我叹了口气。杏花问道:“小姐,为何叹息?”
我垂头:“一定没成,不然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杏花点头说:“老爷那时也对小姐说谢御史为人十分古板,与老爷在朝中十分不和。他恐怕小姐不会如愿。可小姐不依不饶,一定要老爷去提亲。〃
我接下茬地说:“其实干吗见一面就提亲呢?你家小姐既然那样去看了他,先成为朋友不成么?怎么就知道日后会处得好?性情会不会和得来?”
杏花叹气说:“我家小姐性子不好,真要是那样了,大概更没有希望了。”
我微皱眉:“那结了亲,人家不喜欢不更可怕?人心怎能强求?”
杏花说:“小姐觉得成了夫妇,在一起,就如愿了。”
我感慨:“成夫妇还不容易?得到深情厚爱才是难的。后来呢?”
杏花接着说:“小姐不放心家人的传达,提亲那天,她和我都扮成了媒婆的丫头,进了谢府。那谢御史,一听是老爷提亲,就大骂不已。说老爷不遵先法,混乱朝纲。说他家世代忠良,绝不会与老爷同流合污。那时正巧这位谢公子回来,听了小姐的名姓,说道,人讲小姐是个不懂妇道的女子,这样的家世一直未嫁,连亲都未定,必是有难言之隐。那谢御史恍然说正是如此,老爷与他从不交好,今日却来提亲,一定是家有丑女,借机陷害谢家。”
我轻摇头:“你的小姐一定气死了。”
杏花说:“小姐是生气。她从小习武,性情急了些,还常在外面走动。大概这就是不守妇道?”
我依然给这个人上着药,嘴里说:“这样讲,是狭隘了些。”我的手指感到他的身体极轻地颤了下,我忙加了一句:“但你的小姐干的也太出格了。他说了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这样对他。不理他就是了。”那个人轻喘着咳了一下,又压了下来。
杏花继续说:“小姐回家砸烂了房中的所有东西,然后离家四处游荡。三个月前,听人说,谢御史当朝顶撞皇上,反复狡辩,不认错误。皇上发怒,流放谢御史,将他的家产抄没入官,他的夫人早逝,他的两个儿子判为奴籍。”
我吃了一惊:“这不是你家老爷的报复吧?”
杏花说:“小姐日夜赶了回来,也这样问过老爷,老爷苦笑说:我是何等人?后来小姐说既然不是老爷给他谢家的灾祸,那她就不必顾忌什么了!与其让谢公子被卖成娼倌杂役,不如让小姐来完成这命里给他的劫难。也算是他咎由自取。”
我笑:“你的小姐好狠的性子啊。”
杏花低声下气:“小姐从小没了娘亲,对人是急爆了些。”
我说:“看谢公子这个样子,大概该说是残暴吧。”
杏花叹了口气说:“一个来月前,小姐去官奴场把谢公子买了回来,恶言恶语,推推搡搡。。。。。。”她看了我一眼,想了想,接着说:“后来就日夜鞭打折磨他,说一定要他求饶认错。可谢公子不说话,结果,小姐的手就越来越狠,火烧刀割,棒打针刺,灌辣入喉。。。。。。只不动他的脸。。。。。。”
我悄声道:“当然,你的小姐当初就是从这张脸喜欢上了他。”
我手下的人突然大咳起来,我停了手,看着他,他皱着眉,咳了一阵,停下来,喘着气,还是不睁眼。我疑惑地看着杏花,杏花说:“自那次小姐把他在冰水缸里泡了一夜,又灌了他辣椒水,他一直咳嗽。”
我惊:“啊?!你的小姐比锦衣卫都狠哪!”
杏花又问:“什么是锦衣卫?”
我赶快问正经的:“可请人医治?”
杏花摇摇头。我忙说道:“今天请郎中来吧。”看前面的上身胳膊和腿都抹好了,我让杏花帮着我把那人翻了身。我看了一下,明白了,赶快给他用被子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