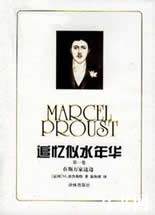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3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ҹ���������ϻ��裬ֻ��̿��Ҫ��ԶЩ�������̿��Ѭ���ˡ�
����������������̧������һ��ط�G�������ô���������ת������ĬĬ���������˼��
�������������Ƶ�ʱ�֣��������ͨ���������������£��»���ˮ����Ӧ�кޣ���Ӧ�кޣ�ԶԶ�ģ�����ˣ������ͻأ�һ�������·���̾Ϣ���������ƴ����ϣ��������⣬ӡ�������ϼ�į���飬ҹɫ���������һ�����Ѳ����İ��ӣ��ǰ����������컣��������ޣ�
����������þ��˱��˫�շ��ȣ����Ʋ�������̨�������һ�գ������һ���죬����������ȴ�迿�������裬����͵�ð��ջ���������β��ޣ�
�����������������������ﴫ�����������㣬Ϊ����������㲻���ֶΣ����˾����ǻ�ȥ�������磬����Ҫ�µ�����������飬ִ���������ǿҪ�����Ҹ��������Ǿ��л���ˮ���£���ʱ�������ˣ����ݼ��ţ�һ�����顣����������������
�����������������������ڸ�����ϴ�գ��ϴ�˯ȥ��շת���࣬һҹ���ߡ�
�����������������������������˷��̹���ϴ��æ������һӦ���£�������������ˣ����������ַԸ����䣬Ƭ�̹���һ�˴�������븮��ȥ��
����������֮ͣ����һ������Ժ�䣬һ��������������������ǽ������½Ρ�������ǰ��ߵͭ����
��������Ӧ��֮������������ӣ�ƽ�յ�Ҳ�������������ٷѴ��࣬���˴���һ������¶���ɣ����Ĵ�����ȡ������Ʊ���������У���������Ӧ��������£�ָ�������ڡ�
�����������ļ���Ժ����˵ռ�ز�������Ҳ�ǻ������������������ģ����ߴ�ɽ�����᷿�����Ÿ�ɫ���ģ���ü����ȸ����ȸɢ��ͥ�䣬ů�շ�ͣ��д�ɫ������ϲ����
������������������䣬���������ݻ������ɴ�Ʈ���ڴ�ǰ�����Ĵ���ʯ�����ڷ����������룬������������齣�ȫ���ľ�Ҿߣ����Ͼ��������ֻ������Ĺ�Ҥ��������һ��һ����һ��һյ�����»�����
����������һ�۱��Ƽ�һ���ŷ�ɫ������Ů�����ӵز������ڽ�β����ǰ�������Ľ�ë���Ű봹�ŵ�˫�������ɵı�����СС�ⴽ������бб��������֬��������ϣ�������һ������Ĺ���������Щ����
������������Ů����������ת�����������Ŀ���һ���������侹������ò�������֮�ˡ�
��������ֻ��������̾һ������ʮ�ĵܣ��������Ǻοࣿ��
��������ʮ�İ�����Ļ��ף������˾�����ɩ��������һ������������ѷŻ����ϣ�������������ɩ������ô�����ˣ���
�����������ľ�����������ô����յľͺȵ���ѬѬ�ģ�Ҳ���������Ը����ӣ���
��������ʮ�İ������ͷ����ȥ�����۾���ֻ�ǵ���˵��������ɩ�㲻�õ��ģ����������зִ�ġ���Ω�к����˲��ܹ�����������ˡ����������������������þ���ֻ˵�����Լ����Ķ���㣬�������Ŀ�Ц���ڲ�ס���۽�ü�ҵı��ǡ�
��������һ����˫�ַ��ϲ�����͵�����ģ���λ�ĸ����������ţ�ȴȫȻû�������еĻ����黷��䣬ֻ�Ǽ�Ѱ����֯��˿���������峺��Ц�������������ǵĸ߹�������������Բ��λࡣ
���������������������ϵ���ֻ�������IJ��Ѳ��ɵ�һЦ����Ϊ����Ҳ֪���ⴺ����������ţ�۱���
������������ת������ʮ�İ��磬�����к����������������ã�����������ʮ�ĵܣ������������ˡ���
��������ʮ�İ�����ɫͽȻһ�䣬˵����ʲô������ɫһ�Ӷ�������ǰ�·����������Ľ���Ц�̣�Ȼ���۵�ȴֻ�м�į��������Щƣ����̾Ϣ��������ɩ���㲻�����ص�����ר����˵��Щ���İɣ���
�������������֪�����Ȳз��ˣ��������Ķ��˶٣���Ƿ·���һ˿Ц�⣬ȴ�ַ·������ı��ݣ���������ĸ�ܿ��Ҫȥ�����˩���ˡ���
��������ʮ�İ��������͵�һ�𣬽���һ�����ģ�Ŀ��Խ�����ĵļ�������Ǵ�����ͷ��
�������������������������òų������������ʮ�ĵܣ������˼�Ҵ�����֪������һֱ��Ϊ���������£���Ȥ��Ͷ�����ǰ��䣬ȴƫƫ�²����ˡ����������Ϳ�Ҫ��Ϊ����ɩ�ˣ���ȴ����������һ����������һģһ�����ˣ����ڲ�������ij��ţ����ֵ����Ƽ��������ĸ������ںεأ����˿�ȥ���ûʼҵ������ںεأ��㾹��Ϳ��Ҫ�������˶������¾���Ц���𣿡���
������������ǿ����ס������ӿ���ڣ��ٱ�����һ�䣬��ʮ�ĵܣ����ֵ���Ҫƭ�Լ���ʲôʱ���㾿���岻����Լ�������Ҫ����ʲô����
����������Ȼ�䣬ʮ�İ���ֻ���ǿ��ķ·�ʲô����˺�ѿ���ʹ�����������Ŀ��������������Ϊ��ʲô����Ҫ���ĸ��ˣ��ѵ�������֮������Ҫ�Ӵ��˶ϣ��������ˣ���ǰ��һ�о���Ķ�ֻ����Ȼ������������������˼ĺ�룬��ǣ���Ӷ�����������ʮ�İ���Ŀ�����룬ͻȻ���������Ц�����������˰��¾������棿�ǣ��ǣ��ǣ��Ҿ��ǰ����������Ҿ��ǰ��������ǷŲ�������������ô������������Ҫ��Ϊ��ɩ���ˣ��һ��ǷŲ�����������Ҫ����������һ��������˵�Ұɡ����������˶��������ң�ָ���Ұɣ������͵�һ���ƿ����ģ������ȥ��
������������Ҫ��ס�������͵�һ��������������������ȵط�ס�����ļ磬�����Ƽ���Ŵ�ŵ���������������䣬���������·���Ҫ˵ʲô��ȴ�վ����ԣ������ƿ�����������˼������ʮ�İ���Զȥ����Ӱ�����ǹ��𣬵�Ը��ɵС����������������Ըһ�л������ü���
��ի���֣��ֲ�Ȭ��
��������ط�G����������������������������ü��ŭ����壬С�һ���й�ɵ����ͷ�ؼ�������������������ʱ������һ������ҪȰ��˵��Щ���Ǽٵģ�����̫������������Ҫ����������������ݵģ�ط�G��������˿Ц�⣬��������ǰϷ�ʵ�����Сɵ�ϣ������������˿����鿴������ħ�ģ���
������ֻ����������һ����������������������С�˿�����֮��Ϊ����;������ݺݺ����������˵�ó��ڡ������������������ˡ��Ĵ������ɼ�����������֮�Ķ�������ͼ��ͼ���ģ������DZ���ѩ����ݾ��������гݣ���
��������ط�G��������һ�ƣ����Ƴ�Ԫ��ġ�ݺݺ���������º�Ц�������������£���ϸ������һ����Ȥ�������������ǡ�������ò������ȴ�����ǡ����ಡ������������������ģ��ҵ���������������
��������������ü���ӣ����ɷ߷���ƽ�������ߣ�����ʲô�ò����ĵģ�ط�G�����������������������������ݺݺһ�㣬Ը�ķ��䣬�������ˣ����������������������ˮ������Ҫƾ���¶�������������������������Ҫ����ǰ�������˶ϣ���Ҫ�ϵøɸɾ�����ʹʹ���ؿ�ʼ�ڶ�������
��������ط�G����˵������ü�����������һ����ƣ���Ҫ�����������������DZ�����Ц���绨���촽����¶��һ����㱴�ݣ���ŭ��������������˺��С�죬������������Ҫ˺�����źã��������ˡ����������������촽������ȥ��������Ű���У��ݺ���ҧ��
����������������ſ���������������Ȼ��ʹ��ֻ���ô���ӿ�������ȣ����ã�ط�G�ɿ���������˿˿�Ⱥ�����ڱ˴˴��䣬����������ͷ����������������˵�˵����Ҿ͡�����������������ס˵����ȥ��Ī��ӿ������ͷ����˲ʱ���ʧȥ���㣬��˫���������ι�ס��������������ط·�Ҫ���������������а㡣
��������ط�G��Ƴ����֪��ʱ�����ڵص��Ǿ��飬����һ���߷ɣ���ݱ�����ˣ��ֲ�����Ҫ���飡��
�������������Ƽ����Ǹ�����ģ��������������Ц��ȴ�������Ҳû�����������ˣ���ȥ����������Ǻ�˵�˵��ء�������Ц�����Ŀ�������������������ߣ��Ҵ��˴������ú���ƽϣ�ʡ������Ż����ط�G�������ڸ�֪�����ж��ͻ��˰ɡ���
��������ط�G������Ц�������ϣ��������������㷢�����ǰ������������ܲ�����ʱ���ͻݵ�����ɰ��أ�����
���������������Ҳ��������������أ�������бб��Ƴ��ط�G���Ǽһ��ѱ���Ѭ�յ�Ҳ֪�����������ˣ���ʡ������һ��˵�ǡ���Գͼ����һ�����ſڿ���˵��ʲô����ѻϷˮ���ģ�����ƽ�����¡���
��������ط�G����������ǰ�����Щ��ʲ���̲�סҪЦ�����˼����ԧ�춼�ǰ�籺���ף����Dz�ɫ˿���弒�Ϻ�����Ҷ����ɫԧ�죬���ų�Ϊԧ��Ϸˮ�����㵹�ã�ֻ�ûҰ�ɫ���ָܹ������Ǻ�ѻϷˮ�𣿰����㲻����Ϊ�˶�������İɣ��������������ӣ����������ļ��ʵ���
����������û���أ�����������ôС���ۣ���֪���˼��������ˣ��Լ�û���㣬�������˼��Ը���ȥ����
��������ط�G���Բ���ֻ������ȡ��һ��������������������������ǰ������ķ��ӣ������е��ţ����㡣��
������������չ����ط�G����ͬ���������ü�����������ӬͷС��д�ţ�����滨�����һ��������������ɏ�����tɏ������ѣ������ؽ������ɣ����һ���ľ�ϻ������㡢���㡢��ľ�㡢���۸����ɣ����顢��м�����ɣ���ˮ��һ�ɣ���ĩ�ߺϣ��鼚ĩƿ�ա�ÿ����ϴ���棬���չ❍����Ҳ��
������������������ƽ����������ǰ�Ǹ���֪��˷����ȵ��ˣ�������ⷽ�ӻ����ֺ������ĵ�˿˿����ȴ�����ķǵ�˵��������Ҫ���Ҳ�����ͿŪ��Щ�أ��˼����վʹ�������ͿĨ�ġ���
��������ط�GѰ������ƫ������ص����������翴�����ˣ��ںڵġ���
��������������Ϊط�G��������������ʣ�����������ѧ����㻵������ȥ����������һת������Ť�����������������ߵ���һ�䣬������������ȥ��ԡ��ط�G����ԭ�����ţ��������������࣬��û��κ��£�����������֬���ѩ��֮�£������Ų���֬��ɫ��˫������¶��Ů����̬���������ף����ɵ�����һ��������������ȥ���Ų���һյ��Ĺ����������˻��������������һ�ɡ�
������������������һ�ۣ�����ô���ϴ���ˣ�����˵�߸������������������µ�������ȥ��
��������ط�G���������������ʲô�أ���
����������ط�G������ôû����ľϬ��¶ѽ����
���������������������Ǹ��ġ���
����������Ŷ����������һ��Ҳ���㣬��û��Ȥ���ˡ��㻹���Ը��ٿ�����ɣ���Ҫ��ȥ˯�ˡ���������������˵������˵�꣬��ط�G����һ�ۣ����˶��̲�סЦ��������ط�Gһ�������������ϣ����ֱ���������֫�������ӣ�����������һ��ò�������ʹ������
������������Ц�Ĵ�����������ֻ�����Ȳ��ܶ���û���ӣ������������ģ�����ү����ү��С���»���Ҳ�����ˡ���
��������˵Ц�������Ĵ�ϢͻȻ�ͼ���������ü��Ҳ���������ƺ����Ϻܲ�����Ƶģ�ط�G�ܻ�������Ц���ٿ�����ɫԽ�Ӳף������亹�乣��ž����
��������ط�G��һ��������������������������ô�ˣ����ﲻ������������������������ڻ��У�̧��Ϊ����ȥ�亹��
������������ֻ��������������ط�G���ģ�ǿЦ��˵û�£�ȴ�������������ܣ�������������ط�G��������ˣ��촫̫ҽ����ط�G��������������
������Ƭ�̹���̫ҽ�Ѽ���������ط�G���͵ػ�����ȥߵ�ݣ��⸮��̫ҽ�ĸ���֪����λ������ү��ζ��ʲô���Ͻ���ǰ�����ְ��������������ϣ�������Ϣ���£�����ϸ�����а�̵Ĺ����������֣��ิ���ǡ�
�������������Ϣ����̫ҽߵ�ʣ����������������������������������ξ�̫�飬ʹ���Ҵ�ϸ����������Щԭ����;���ͷ��ܺ����𣬱���ֻ������ӱ�����ľ߯�����ųٳ�δ������ū�ſ�����ֻ�谴ʱ��������Ӧ��Ȭ������
��������ط�G��������ģ�����Ͻ����¿�ȥ����ץҩ������
����������˵������������ҽ��Ϻ���˵���հ�ʱ��ҩ����ȴ����һ�գ����������˯��ż��������Ҳ��������ã����֪�Լ����ںδ�������������������ֻ��˯ȥ������
������������ط�G�Żظ���������������Ժ��̽�ӣ������������У��������ڣ���ǰ�밲��������ԥ����˵������ү������Ҫȥ��ͷ��Ѱ���ô��������Ҫ������Щ̫ҽ��ԭ���ֶ�˵û�ģ��ɵ�����ӣ���˵���ڣ�������һ��ÿ����������ɶ����������Ƶ��������Ǻϻ������ſ����ӣ�����˭Ҳ�����������ø��������ģ��ⶼ��ʮ�����ˣ�����������ô����ҩ��Ҳû����ɫ��ү�������ⲡ�������Σ��⺢��˯��ʱ�㳣��˵Щ������������ʲô�ණ������������а�ˡ���
���������İ������ˣ������������齱ߣ�����ɴ�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