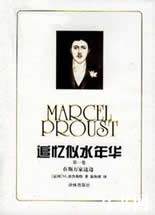惊情三百年-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耿碧瑶可不觉着她那话有什么好笑的,可眼下也没法子,只得接过,打了开来,才一眼她那颗心顿时落了下来,“哎呦,不就是龙胆草吗?你神神秘秘的,吓我一跳。”
年佩兰心底暗自好笑,也不与她计较,更耐着性子问:“这府里也就姐姐最好学个草药的,你再瞧仔细了,这可真是龙胆草?”
“这不就是龙胆草嘛。”耿碧瑶面露三分得意,她娘亲常服汤药,她见得久了,再加上也有几分兴致,倒学过一阵医,一般草药自是难不倒她。
耿碧瑶见年佩兰难得在自己面前露怯,便将那龙胆草又仔细看了看,方道:“你瞧它表皮暗灰色棕,茎基长着许多细须,这是龙胆草中的上品………坚龙胆草的干燥根茎,《神农本草经》载,坚龙胆草,性寒,味苦,有清肝火,泻湿热,健胃,是味使用极频的草药罢了。”
“我早知道姐姐学识好,可这回哪,”年佩兰顿了顿,“是连姐姐也骗过去了,我可就更放心了。”她见耿碧瑶还将那龙胆草放置唇边轻嗑了下,似更坚持般。便伸手去取了过来,“这叫桃儿七,制干后,别说是样子,就连它初入口的味都与那龙胆草是一样,非得要那生畜尝了,才知道这一样是要它生;另一样是要它死。这桃儿七初服倒也能叫人泻湿热,只是慢慢便会叫人水泻,血泻,再停不下来,泻到她虚脱………死为止。”
耿碧瑶完全听呆了,背上涔涔冷汗,结结巴巴道:“可,可要真死了人,那那总查得出来。。。。。。”
“到那时又管咱们什么事?就算查出来又怎么了?那药方是太医们自个开的,药材是他们亲手配的,药汤是手下的药童煎的,就算查了出来,他们有什么证据说是咱们做的手脚?我还说是他们自个两只眼珠没长好呢!何况,那太医敢和爷说是因为吃错药了吗?那摆明了不就是他们自个的责任了?他们只会说宛琬体质有异与常人,原先旧毒并未除尽什么什么的一堆理由。”年佩兰冷静说道。
耿碧瑶听她说得也有理,又瞧瞧她说的那什么桃儿七实在是与龙胆草无甚分别,不由点了点头。这时,她才注意到那年佩兰目光炯炯的盯着她,顿时,不详的预感袭来,这下她算全明白过来了,目瞪口呆道:“你,你不会是要我去放药吧?”
年佩兰并未答她这话,端起茶碗,轻呷一口,这才缓缓说道:“我倒有一事忘了问姐姐了,前些日子哥哥从川中带信回来,说这世上人才易得,可办事难觅贴心可信的人那。当时我就想着以姐姐这样性情和善沉稳的人,她兄弟定也错不到哪去,肯定也是个办事实心的人,只是不知姐姐可舍得让家中兄弟去那川蜀之地任个一官半职的,所以也不敢莽撞和姐姐商量。”
耿碧瑶眼睛放亮,听得心里一动,她家中兄弟回回抱怨她不去求爷给谋个好差事,可他们哪知道那爷是好开口相求的人么,更何况这一年里头爷根本就不常来了,她也常听人说那年羹尧年轻有为,是在皇上面前都得宠的人,想必跟着他办差以后定有出头之日。
这耿碧瑶眉眼变化的一举一动年佩兰可都盯着瞧呢,她言有深意道:“如姐姐愿意,今后咱们就真正是一家人了,齐心才好办事,我也不怕和姐姐说实话,我与那宛琬素来不合,若要多打听两句,别人定然起疑。可姐姐不同,你与人和善,身子又一向不好,一年四季总断不了药,平日里也好自个配些个草啊药啊的,常去那额椅殿的,又有谁会多说两句?办那事最妥当,唯一的人选啊还非姐姐不可。我心里也想着是万无一失的法子才敢来和姐姐商量的。我知道姐姐心善;可就算你自己不计较;也得为自己肚子里的主早做打算才好呀。”
耿碧瑶虽说也嫉妒那宛琬,可凭心说,她还真是没想过要去弄死她,可在这世上谁又是能完全按照自己心意活着,而不做一点违背良心的事呢?这府里虽只有李淑雅生有阿哥,可最有势力的还属福晋和年佩兰。那福晋自然是和她亲侄女联手的,根本不会视旁人为亲信。而年佩兰素来就比她要强,她知道那年佩兰是有些瞧不上她的,可这样正好她也不会提防着她,吃她的醋,反而有什么好事还会分她一羹。这年佩兰的手段她也算是领教了;单是这用桃儿七去换下龙胆草,定是她背后有高人指点,布好了局,若自己坏了她的事;只怕便是与她背后整个势力做对。自己一人在这府里势单力薄,倘若这回真能一举生下男丁;更会成了别人的眼中钉。就趁此与那年佩兰坐在一条船上也好,想着便横下心来与年佩兰细细商量。
回头说那众人散了后,李淑雅逶迤进了她院中角门,刚走至廊檐上,只见她房里的丫鬟已等在那里,见她回来了,上前笑迎道:“主子,惠静师太在里屋已等了好一会了。”
李淑雅听见是她来了,眉色一喜,忙向屋里走去。说起与这惠静师太的缘分,还是她滑胎的那年,事后虽设了祭坛,请众和尚念经,超度亡魂,可“五七”之后她仍是夜不能瞑,听人传说静月庵中留有菩萨贝叶遗迹最是灵验,她去那庵里待了几月才渐渐缓了过来,从此信佛之心便更诚些,与那庵中老尼惠静结下因缘倒也常来常往了。
李淑雅入屋后,打发了众人,只让秋梨去摆了茶碟子来。
李淑雅向那惠静问道:“前日我让人送了八百钱去,在菩萨跟前供上,你可收了没有?”
惠静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那孩子前世也没投错胎,亏得福晋心善,都这么久了还念念不忘。”
李淑雅叹口气道:“阿弥陀佛!你是没看见那情形,都已经是个有鼻子有眼睛成型的阿哥了,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的上个供,求个心安,只是常心有余力不足,这府里是比不得寻常人家,可眼睛盯着你,指望着你的人也多呀。”
惠静劝道:“你只管宽心,这府里虽说现如今那两位都有喜了,可是不是阿哥还说不定呢,再说了,就算都是,可还不是这房里的阿哥为长吗?等熬到他大了,那时你要作多大的功德不能?”
李淑雅听她说后,淡淡苦笑着摇头说道:“罢了,罢了,可别再说将来的事了。就是如今这个样儿,弘时算这府里的独根苗,也及不上那屋里的一根手指头呢。”她一面说,一面指了指那腿。
惠静会意,便问道:“可是大福晋的侄女?腿瘸了的那位?我才进院就听人说了。”
李淑雅唬的忙摇手儿,起身走到门前,掀帘子向外看看无人,方进来同惠静悄悄附耳道:“这府里提起这个主儿可了不得,是半句闲话都不能说的。也不知那位是怎么想的,赶情她自个养不出了,让她侄女来独霸着也好。”
惠静瞧她眉色带有恨意,便探她口气说道:“谁不知道你心最善,气量也大,原不是见不得人家好的主,还不是被她送的那盆迷迭香伤透了心。”
李淑雅拜手道:“天可怜见,总算是遇着个明白事理说公道话的了,可又能怎么样呢,那桩事是连提都不能提的,我心里憋屈呀。”
惠静鼻中一笑,过了半晌才说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就是佛家也要讲个因果报应的呢,明的不敢怎样,暗里也就算计了,何还用难受委屈到如今!”
李淑雅一听这话里别有深意,心底暗暗欢喜,便顺着问道:“她们楞是让条人命没了,可就没个报应,我咽不下这口气,只恨没这样的本事。你若教我个法子,让那地下的人安了心,我大大的谢你。”
惠静听她这话打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过,罪过。”
李淑雅道:“师太,往日你最是个肯救苦救难的人了,只这回就如此心狠,眼瞧着人家都已欺负到我娘俩头上了,还不能支声气?难道还怕我不谢你?”
惠静听她如此说,便笑道:“你要提到那谢字,可是错打算盘了,我一佛门中人要那些银子做什么,不过是瞧你念佛之心,一片赤诚罢了。”
李淑雅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道:“真该掌嘴,原是我糊涂了。师太一心向佛之人怎么会图那些身外物呢?我说错了,只求师太替我好生想个法子。”
她走到橱柜里取了一堆银子及些首饰出来,递于那惠静,”这些个你先拿去了做香烛供奉使费算替我孝敬菩萨的,事成之后,我照旧再出双份香火钱,你看可好?”
惠静瞧着一堆白花花的银子,满口里应允,伸手便抓了掖放好,又附李淑雅耳边窸窸窣窣好一阵指点。
满室春光,不同心思
福晋午觉醒得早,起身盥漱后,便唤人一同亲往宛琬那院走去。
二门处打着瞌睡的老婆子们瞧见福晋来了赶紧起身请安,福晋摇手做罢,一行人走入院内,只见绣帘垂地,悄无人声,只有那半夏一人守在回廊,手里做着针黹,福晋让人小声招呼了她近前,“昨夜里是不是没睡好?药可都定点服了?”
半夏道:“格格夜里有些咳嗽,睡不沉,药都按时服的。午膳后服了安神丸倒睡了一个多时辰,这会子也该唤格格起身了,不然夜里又睡不塌实。”
福晋从那袖里取出张方子递与半夏,“我让人配了张方子,你现拿去额椅殿让那王太医瞧瞧可妥,这里放心,我进去看看,等你回来了再走。”
半夏听了,只得接过方子往那额椅殿去。
福晋掀帘进来,瞧那宛琬翻身朝里睡着,身盖着一幅石榴红绫被,青丝散于枕畔,一弯雪白的手臂撂于被外。宛琬才醒转来,觉着有人卷起帷幔,沿着榻边坐下,以为胤禛回来的早,依旧调皮朝里装睡,也不睁眼。
福晋瞧着叹道:“都这么大了怎么睡觉还是不老实,等让风吹了,又叫嚷肩窝酸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她盖上绫被。
宛琬这时才知是姑姑,有些尴尬,只得继续合着眼。
福晋凝望半晌,只觉心口发酸,那眼泪早就掉了下来,半响拭泪说道:“宛琬,你这苦命的孩子,你让姑姑日后去地下如何面对哥嫂……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自幼伴我左右,打小便能过目成诵,性情却又一派天真,不知有多讨人欢喜,只怪从前姑姑总存有私心,舍不得让你早早嫁人,想着慢慢再帮你配个如意郎君,琴瑟和鸣,才算了我夙愿,可谁承想如何还这般年轻,就。。。。。。”
宛琬听得心口一滞,嗓子眼里竟有了些腥气,却瞧不见福晋脸上一掠而过的痛苦怨恨神情,“姑姑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孩子,嫁入这府里也好……只是怜卿薄命甘做妾。”
闻言宛琬如雷轰电掣一般,她早知会到今日的地步,但乍听见这话的一瞬,哀伤、内疚却奔涌而来,气噎喉堵,翻转身来,福晋忙扶她起身坐好,宛琬瞧着姑姑那般慈祥高贵,风姿绰约,眼眸深处却留有抹掩不去的悲伤,她心中定是极不快乐的吧,人人都要与她争抢丈夫,她却只能大方接纳,愧疚戳得她心中虽有万句言语,只是说不出口,半日,方哽咽道:“姑姑,姑姑,对不起……”
福晋搂她入怀,轻拍她背,慈爱道:“傻孩子,你有什么对不起姑姑的?只是委屈了你,是姑姑不好,弄得你要吃这般苦头。”福晋瞧她的脸色极其苍白,却依旧清冷美丽,心底终不得不承认她实在是美得让人心动,“宛琬,你玛发府里原有一文士医术更胜于国手,我让人将你的症疾告之,他回话说这腿未必便真废了,姑姑让他明日再来亲诊,等咱们把腿给治好了,再来美美的当新嫁娘可好?”
宛琬有些发窘,颊上飞红,讷讷道:“一切只凭姑姑做主。”
两人说话间,四阿哥入院走至窗前,嗅着一缕幽香从那碧纱窗中隐隐透出,他掀帘进来,福晋忙起身问安,四阿哥略说两句,便坐于榻边,抬手理那宛琬鬓发,低语询问几句又连声唤了半夏、苏木进来伏侍梳洗,另有丫鬟们拿着茶盘托药,托水的,捧着痰盒漱盂的,端着燕窝雪粥的,鱼贯入内。四阿哥只站在一旁从那些罗裙春衫中挑出件樱粉色的,一时各有各忙,满室热闹。
福晋退至室角淡笑瞧着,原来古诗中说的‘纤手铺锦褥,皓腕捧银杯。绫罗绸绢丝,情人细挑衫。’便是这般模样,此情此景倒似只多了她一个人,也罢,福晋转身推窗,顿觉春风阵阵,痛快多了,屋外春光无限,姹紫嫣红都开遍,却只怕那花繁叶茂,禁不得风催雨送。她移步出屋,无人察觉。
过得片刻,宛琬下地稍一停顿,忙寻姑姑,屋外丫鬟挑帘入内回禀说福晋回去了,走时吩咐,格格才起身手脚却都还有些微凉,虽说入春了,夜里尚需笼上火盆,只是炭盆要搁远些,免得让炭气熏着了。
宛琬听罢抬首望了一眼胤禛,但听得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