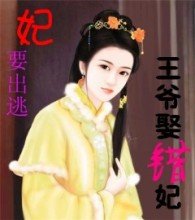你若撒野,我把酒奉陪(高干)-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说吧。”苏酒视线落在花瓶上,妖艳欲滴的玫瑰,怎么看都是高雅。
“我知道他爱你,用尽了全部力气爱你,可是,我就像他爱你一样爱着他……同样的没有办法……我父亲也整日的骂我‘人家都不要你你还死乞白赖的往上贴你有没有脸?’我连哭都不想哭。想这么多年的陪伴都是假的吗?凭白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想不通我这么骄傲什么都学到最好,可你只要简单的一个微笑,他就奋不顾身朝你飞奔去。为什么?凭什么是你这么个人?”
林以芯一直看着她,口气是很软弱,无能为力一般,“我知道你从不当自己是杂草,就算是,也是长在最高最高的地方,谁都不能践踏,也不敢上去。我什么都比你好,随便拿出一样,你都比不了,可是,我没有你强,我需要庇护,没了保护一推就会倒,可你,宁可站着死,都不会跪着让人辱。我是佩服你的,真的。”
苏酒深呼吸,只觉胸闷,始终一言不发,不知说什么,也没什么好说的,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谁也帮不了谁。
“我不是拿了什么威胁他们家,我还没那个本事!有些事,是你们这些做老百姓不能懂的,我父亲也没必要为了我逼自己的老友那么不耻。我父亲说,衍森他父亲……为人太刚正不阿,惩治贪官污吏纠正风气手段太强硬,一点情面不留的,也从来不跟从任何派系,处处得罪人,风头又压过了一位重要人物……总之这其中的复杂,是普通人不懂也一辈子插不上手的,我只是想尽量帮他……”
苏酒抽过玫瑰,上面没有刺,可削了刺的玫瑰依然是玫瑰,放在鼻子前嗅了嗅,很香,掰下一片花瓣,说:“那你想我怎么做?”
“你走,走的越远越好。”林以芯忽然之间变成了备战姿态,“他的心脏不能再过于激动,他不对我动心反而好,一辈子安稳。你若是想他活的长久,就走,走远了人不在眼前,他会很快把你忘记,人自然就平静了,或许还能活的久一点。你应该明白,人不都这样,一时执念,过去就能想明白了。”
这一刻,仿佛是脱去所有铠甲战袍,不战而败。苏酒低着头不说话。
突然有人从背后激动的说:“以芯!你怎么能这样!苏酒,不要听她的,跟我去看我哥!”
穆衍柏瞪了林以芯一眼,拉起苏酒就走,她却挣扎着,定在原地,“衍柏,不了,你哥醒了再告诉我吧,我想先回家了。”
“你别听人乱说,跟我走。”
“衍柏,我真的不想去,求你。”苏酒只觉疲惫不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苏酒你听我说,别人我不多说,可我认了你这个嫂子,你跟我进去看看他。”
林以芯始终坐在沙发里,沙发背很高,看不到是什么表情,可姿态,永远是胜利的那一方。
不该逾越的,狂妄自大的挣了过去,终归是连块踏脚板都寻不得,她身后没有人,早习惯了孤立无援。
苏酒往后退了半步,“我真的要回去了,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说完,几乎是用逃的,拼命按键电梯,等不到,走楼梯,总之是想要快点离开这无所遁形的地方。
穆衍柏看着苏酒离开的方向,回身坐下,与林以芯面对面,“你怎么能那么自私?她和我哥多痛苦,你感觉不到吗?”(文-人-书-屋-W-R-S-H-U)
“她不是弱者,不需要任何人同情。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以芯姐!我从小叫你一声姐姐,你太让我失望了!”
再撑不下去,林以芯红了眼眶,“衍柏,怎么连你也这样?咱俩从小一起长大,还说叫我姐姐,你却帮着她不肯帮我。”
“以芯姐,我不是不帮你,这种事不能靠帮的,我帮你,我哥就会爱你了么?他不会,我知道我哥心里是真爱她,所以谁帮都没用。”
“我哥昏迷中一直喊她的名字……连我爷爷都看不下去让我找她过来看看……”
穆衍柏见她是快要哭了,不是不心软,可还是照实话劝她,“开始我听说你们的事是想着别让我碰上,碰上我一定帮你报仇。可那天在俱乐部,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二哥为了谁在外人面前失态,你也知道的,他多爱面子的一人,为了她却什么都不管不顾,连爷爷都不顾了。一次次回家闹,你知道么他后来回去又挨了打,就那么跪着死都不动求他答应。爷爷发了好大的脾气,打的他心脏受不了趴在地上却怎么都不起来就逼着爷爷从他的意。你也知道,他要是想站着,打断了腿都不可能跪着的人。苏酒和他是一种人,强求不了的。他这次是来真的了。你,放手吧……”
“她和我们不一样的。”
“可我哥觉得一样,甚至还觉得没有人能比得上。咱们一起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哥那样开心,吃着饭都是笑的。有的人,任谁都代替不了的。”
“我恨你……衍柏,我恨你,连你都这样说……”
林以芯捂住脸,无力极了,这些年,多少岁就多少年,相依相伴,何曾为了谁这样伤她?只因一个无意误闯进来的人,将一切情感毁成枉然。将对他的爱熬成毒,一丝一缕,侵入血脉,疼的自己痛心入骨。却是怎样都费尽心机,不过一场徒劳。连自己都清楚,想要得到他的爱,只是痴人说梦罢了。可得不到,也不能拱手相让。
哭了良久,林以芯抬起头,脸上透着倔强与冷漠,对穆衍柏说:“她怪不了任何人,怪只能怪她自己生的不好。”
回到家人瘫软在床上,蒙着被子,又是哭了一整天。第二天,买了报纸想找工作,可看着上面的字,看着看着想起他的脸,眼睛不自觉又开始模糊。什么都做不了,只想呆呆的坐着。有时实在是忍不住,偷偷跑去医院,在他的病房楼下看着,就那么躲在暗处看着窗户上的亮光,看够了就回家。日里总心慌的厉害,夜里噩梦不断,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又忍着不开电话。
挺着挺着,挺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要振作,一定要找回所有的力气,咬牙活下去。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她甚至用小刀割自己的肉,告诫自己:要重新来过,从这道坎上跨过去,将来再没什么好怕的了。
印了简历去商场应聘,说是经理有事让她先等一等。苏酒去卫生间补妆,怕样子太憔悴给人印象会不好。
就那么巧,碰上了朗朗,见苏酒瘦了好多,以为过的很不好,追问了很久,她却什么都不肯说。
苏酒问她怎么样,朗朗说去年参加比赛得了金奖被国外的音乐学院录取,过了年又要回去上学,临走买点国内的东西送给外国同学。
苏酒是真心替她高兴的,朗朗从来用功刻苦,几分耕耘几分收获,都是应得的。朗朗问她在做什么,苏酒有些哑口无言,她也想不明白自己这一年都做了什么,把自己弄成这般不人不鬼的样子。不想多说,谎称有人在等,匆匆道别。
一个人在街上走,漫无目的,认不清方向,最后,却是走到了医院。已经是凌晨,上到顶层。走廊里异常安静,值班的护士问她找谁,苏酒才惊醒,自己竟是不自觉走到了这里,想了好久,说:“我知道病房在哪里,不用麻烦,我看一眼就走。”
小护士始终不那么放心,狐疑看着她,让她等等,小声叫了护士长。
这里是特殊病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探望的,苏酒只苦笑着,转身想走,被护士长叫住,问她姓什么,她如实回答。
护士长点了下头,说:“去吧,有人嘱咐过我,是你的话随时都可以,只是最好安静些,他恢复的不是很好。”
“谢谢。”
她知道是谁,非亲非故,怕连朋友都算不上吧,衍柏对她,却始终那么用心。
轻轻推开病房的门,生怕惊扰了这寂静的夜晚和里面的人。可她从来都不是做贼的料,一时没能适应屋里的暗度,不知撞了什么,轻呼了一口气,捂着嘴巴定在原地,听床上没动静,才继续往前走。静得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她努力,很轻,很慢,一步步靠过去,站在床边。
窗帘只拉了一半,室内温度适中,苏酒却觉热得透不过气,浑身血液倒流。终于是,见到他了,他就躺在自己眼前。像一场梦,好怕一触就会破碎。
他是背对她的,蜷缩在床边,从苏酒的角度俯看过去,手抓着床沿,睡姿并不好,像受了什么气。她默默站在原地,不敢动,不敢伸手去摸,甚至不敢呼吸得太多。就这样看着他的背,明明就在眼前,可什么都不能做不能说,仿佛隔着最遥远的距离,处在两个世界里,看见了,得不到,想忘记,又做不到。痛,是最痛的痛,苦,苦进五脏六腑。
“你要好好,不能在一起,我也希望你好好的。”
她说的声音极小,小的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说了话。万般不舍,不想,不愿,可还是得离开。
转身,床上的人一跃而起,从背后死死抱住她,语音凄凉:“我不好,我一点都不好。”
她直直的站着,忽然,落了泪。竟是这般想念他的声音,只一句话,所有固执一瞬间全部崩塌。
他将她的脸扳过来,狠狠地吻住她的唇,没有多少气力也想要全部用尽,吻她,死死地箍住她的腰,那样紧,如果可以,仿佛想要嵌到自己的身体里去。泪是咸的,吻是苦的,纠缠在舌齿,仿佛是吞了毒药,侵蚀折磨两人的心。
一切都那样隐晦急切,吻的几乎无法呼吸,肺里的空气全都被挤出去,而他,只怕来不及,只怕是假的,只怕松了手她便会消失不见。仿佛世世纠缠都已是来不及。
她哭的厉害,已是站不稳,嘴里呜咽:“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
静静的看着她,将她的脸捧在手心里,带着万千珍视,擦去泪水,“不要哭,怎么都好,就是不要哭了,好不好?”
抱着她依偎到床上,又慢慢的,轻轻的,低低的俯下去,亲她额头,鼻子,眼睛,唇瓣。又紧紧拥住,想念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她终于是来了。
“你知道吗,我想过了,只要你肯来,你肯来看看我,这辈子,我绝对不让你再离开我。无论如何,我只要你。”
“我要是不来呢?”她轻轻的问。
松了松抱住她的手,可还近在咫尺,黑暗中寻到她手背,握住,仿佛是凝结在一起。
他说:“原谅我也有自尊。”
他说:“请你原谅我的自私,我不能割舍,我真的不能,我怎么样都放不开你。听到动静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一定是你,你让我怎么疼都行,但你不要离开我……求你……”
透着隐约月光,苏酒能看清他的脸,有东西滑落,很大的一颗,哧的一声,落下去。
这辈子,只有这一个男人为她流过泪,为她不顾尊严的祈求,可是她不能,不能够执意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不能……我怕我做不到,我害怕,我不能够再让自己陷太深,我是最清楚自己的人,往后我若是真被逼到撒野发起疯来你会彻底完蛋。我不能让你不好,我希望你好好的,你明不明白,怎么样都可以,只要你好好的……”
“那么,就让我完蛋。”
他的唇又落下,很烫,彼此的泪痕都洇干在炽热的唇间,像是烙铁,融化了苏酒顽石一样的心,将她仅存的理智烧成灰烬,一瞬,灰飞烟灭。
重新拥住她,深深地,用力地,彼此只顾着唇舌纠缠,吻的深切,吻的地久天长,夹杂着药水味,他身上甘冽的烟草味道,一寸一寸将苏酒点燃。如莲花盛开,哪怕只能远远看着,不能触碰,只要是美的就好,只要这一刻,是最美好的。
又是她先跨出了这一步,是她没有管好自己的心闯到他面前,既然被抓了现行,那么就不能再逃避,何苦让彼此都这般煎熬,不如顺其自然。
是真的割舍不掉,不想再骗自己,母亲走的时候再难受都能挺着一个人过,可离开他,仿佛连喘口气都是疼的,他是如此珍贵,怎么可能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她做不到,如何逼迫自己都还是做不到啊。
忽然便想通,苏酒回抱住他的腰,“我不走。其实,我舍不得的,真的舍不得……”
多难得她肯在他面前软一点,穆衍森搂得更是紧,“舍不得就不要放手。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你对我死缠烂打,对我撒泼耍赖,你打我骂我甚至可以威胁我,跟我怎么闹都好,只要别那么理智说离开就走的那么坚决。你总是与人不同,让我害怕,很怕,好像怎么样都留不住你,你不贪图任何东西,连爱都不贪,可以说走就走。其实,你不来,等我好些了,还是会去找你……我怕你会过的不好,没有你,我会过的更不好……”
“别说话……”苏酒用手心轻轻覆盖住他的嘴唇,“我不走,我照顾你出院。好困。我们睡觉吧。”
一整夜,穆衍森都紧紧抱住她不放,像是不小心她就会溜走一样。而苏酒也像平常和他睡在一起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