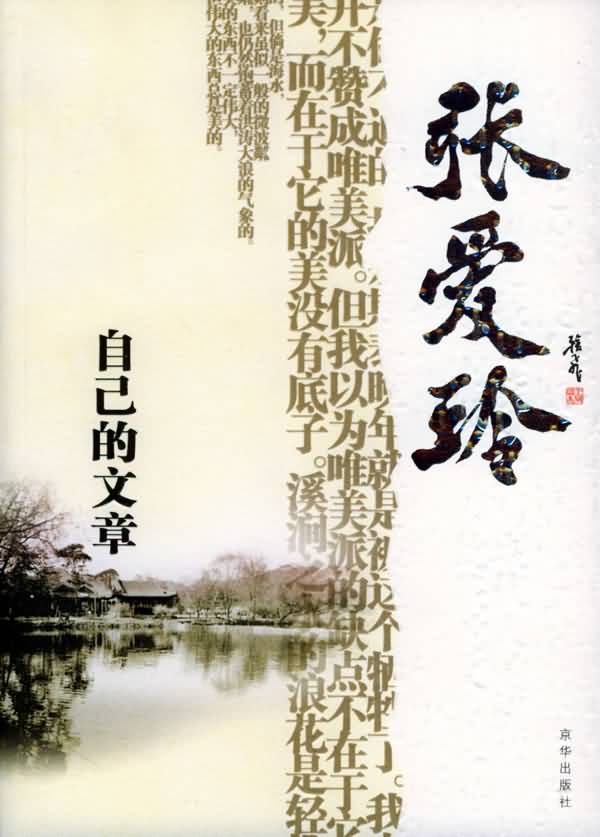张爱玲经典散文集-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顾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分安己,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本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的异像,使人感到华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谈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亲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殊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官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里葡萄于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屈节讨小孩喜欢,在《狸宫歌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妄,辞别祖先。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忧不动,在那寒冷的自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屈屈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侯,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自管自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昧了。
《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颠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领,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跳舞。
(原刊1944年11月《天地》月刊第14期)
二十七、谈音乐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譬如说颜色: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杉,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还有一次,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有一种新的立体。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烟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崭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昧,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昧。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人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站始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
我被带到音乐会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中国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终沉默着,坐在位于上动也不动,也没有睡着。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母亲和始妨窃窃议论一个红头发的女人:“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只有绿。红头发穿绿,那的确……”在那灯光黄暗的广厅里,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女人,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头发难道真有大红的么?很为困惑。
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远远坐着不买票,享受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我客气地微笑着,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才用手绸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我还不会说英文,不知怎样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回来,骄傲快乐地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虽然已经隔了一天,还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味。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替我们开门,我很矜持地,从来不向他看,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