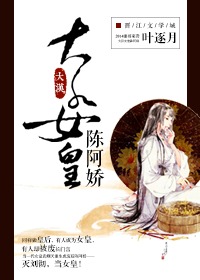清宫汉女-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命阿离吩咐下去准备开宴,亭内单摆一席,只坐了我和线,马两位夫人及刘氏,其他夫人小姐皆在亭外开了两席,这些诰命夫人们素日与夫君出兵放马,少了些许闺阁女子扭捏做态之势,饮起酒来亦是毫不含糊,我一时欢喜,命人取来上好桂林三花酒,亲自与她们把盏。
线夫人挨近我,低声道:“马雄眼高于顶,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了他这位出身书香世家续弦的夫人。”
我心领神会,含笑耳语道:“多谢宝姨提点。”
马夫人与我恰相对而坐,只见她通身上下皆由素雅羊脂细玉点缀,温润恬和,全无半点骄矜凌人之盛气,暗自疑惑不知怎生嫁了马雄这等粗人。她见我打量,只款款笑语道:“妾身可有什么不妥吗?”
我摇头坦然笑道:“我是在想,夫人和马将军真个不似一对夫妻。”
她亦笑道:“我也不知怎么嫁给他地。”面上却浮起温柔眷恋神色,我知线夫人所言不虚。
刘氏接口道:“在咱们桂林,谁人不知马将军爱妻如命呢。”
我执银酒壶为马夫人斟了杯酒,举杯真诚道:“愿将军与夫人感情如同此酒,愈沉愈醇,历久弥坚。”
她感激一笑,一饮而尽道:“多谢格格。”我敏锐的察觉到,她美目之中已不似方才那般防备冰冷之色。
宴席直到日落时分才散,众人一一告辞,待人去园寂,我方欲起身,却觉脚下无力绵软异常,推开上前扶我的雪寒,勉强扶着桌子站起,只一阵天悬地转,我颓然坐到石凳上。雪寒忙道:“格格,您略歇歇,奴婢去厨房弄碗醒酒汤来。”
我挥手要她去了,一个人摇晃着走到玉带桥上,伏下身子去戏水,玉带桥下养里一群锦鲤,极是不怕人地,见我伸手在水中,纷纷来嘬,痒痒的触觉使我咯咯笑起来,却浑然不觉身后一双探究地眼睛。
直到雪寒捧着醒酒汤过来,惊呼道:“额驸,您怎么站在这儿?”
转过身子,果见孙延龄在我身后,不知站了有多久,痴痴地盯着我看,我歪着头瞥着他道:“我好看吗?”
孙延龄接过雪寒手里的汤碗,命她去了,方坐在我身侧,扶着我地后背将碗送到我嘴边,我接过仰头喝尽,甩手将碗扔在草丛里,抓住他的前襟逼视着他的眼睛道:“孙延龄,我好看吗?”
孙延龄搂住我的身子,柔声道:“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我嘻嘻一笑,松开双手,从他怀里挣脱来,指着他朗声道:“可是,孙延龄,你是个懦夫,你不敢爱我,你。。。。。。。。。。。。。。
尚未说完,只觉口中污秽之物喷薄而出,不禁蹲下身子吐的昏天黑地,耳边一声叹息,我眼泪瞬间纷纷而至,那叹息竟是如此熟悉,我不顾一切的扑过去,双眼迷蒙,悲凄道:“是你吗?你来接我了,是不是,不要,不要再离开我。”
那人只将我拦腰横抱起,一言不发向前走去,我紧紧攥住他的衣角,疲惫的闭上双目安心的沉睡去。
梦里,岳乐骑着高大的飒背对朝阳,披着一身金光,象初次相见那般嘴角衔着一丝令我心安的微笑飞驰而来,他停到我的身边,双眼亮亮凝视我半晌,伸出手来拉我上马,在我耳边轻声道:“从此我们四海为家,再不分离。”
待我醒来之时,已是深夜,昏暗的卧房内只留了一盏若明若暗的宫灯,孙延龄合目沉睡在一旁,一只手臂紧紧揽着棉被下一丝不挂的我。
我翻身下床披上寝衣,推开厚厚的殿门,月色如水洒在我悲喜莫辩的苍白面庞之上,突然听到外面好象放烟火的声响,抬眼望去,那些流光异彩的烟花一道的一道滑过,又重来一道一道。那样的灿烂总是可以让你瞬间忘却所有,不管是忧伤或是孤单。。。。。。。。。。。。。。
无力的靠在门框上,双目干涩的竟留不出一滴泪水,我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坚守着什么,那些想要忘记的没有被忘记,反而更清晰的闪现,更深刻的触及。
一瞬间突然就有些恍惚,莫名地,就感觉到一种悲伤在心头蔓延。
第二卷 峥嵘岁月 第十章
年后,我和孙延龄多次到桂林周遍巡游,大多县镇皆是民生凋敝,所见百姓衣衫褴褛,日子过的极是艰辛,由于藩府所需开销巨大,军饷又严重不足,因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不管以何营生的百姓皆怨声载道,贩卖子女亦是寻常事,骨肉离散,家园荒芜,这些惨境是自幼娇养在王府,深宫之中的我从未料想到的,放目过去,满是憔悴凄苦的百姓,哀鸿遍野,心内沉重的如同压了千斤大石。
更叫我心头难安的是孔家军,这些年来频换主事将军,政令不一,士兵们散如泥沙,军中士气低落,粮晌短缺之时便伙同起来抢夺百姓,毫无军纪可言,在百姓眼中,孔家军甚至比苛捐杂税更来的可怕。
一日,走了大半个镇子,我们是轻车简骑,也为掩人耳目,大多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远路,实在累的捱不住,与孙延龄,阿离并几个侍卫随意在街边一简陋茶篷坐下歇歇脚。
伙计殷勤的斟上茶来,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几根碎茶叶梗,孙延龄皱着眉头喝了一口,却立马又喷了出来,一个侍卫见状对店家喝道:“老板,你这是人喝的茶吗?重换上好的来。”
店家忙小跑过来苦着脸道:“诸位大爷,有口茶喝就不错了,哪里去弄好茶来呢?”
侍卫一听抓起店家的前襟,恶狠狠的张嘴便骂,我厉声止住了,温言对店家道:“不打紧。你且做生意去吧。”
店家如逢大赦,颤巍巍躲在帐台后不敢再露面,我面带不悦对方才恃强的侍卫道:“谁许你如此放肆的?”
侍卫委屈地站了一旁。偷眼看了看孙延龄,孙延龄忙打圆场道:“他也是一片孝敬之意。惟恐格格饮不惯这茶水。”
我面无表情的将整杯茶喝完方道:“出来这些日子,不都如此吗?你用一日就这样大呼小叫,却不曾想这些百姓年年月月皆是这般度日的。再者,怎可如此动不动蛮力相向?”
孙延龄不再做声,命几个侍卫别桌而坐。又低声道:“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失他丢了面子?”
我闻言只觉烦躁,不耐道:“我只不喜如今将士们有恃无恐地猖狂样,到底是谁给了他们胆子如此无法无天?你不说好生整顿整顿士气,反倒说起我的不是来了。。。非到惹出大麻烦,百姓与我们离心离德才算完吗?”
孙延龄正待反驳,却听一阵嘈杂声传来,众人俱抬眼望去,原是几个书生在临桌争论些什么。不经意一瞥只瞧见一张似曾相识地清秀面孔,见我蹙眉苦思,阿离笑着在我耳边提醒道:“是那日在小食摊见过的公子。”我这才恍然。命阿离去请来。
孙延龄疑惑不解的打量着站在我们面前的一袭蓝衫的书生,那书生怔怔瞧了我半晌。低呼道:“孔四格格!”只拱手一礼便罢。
我和阿离相视皆惊诧不已。他忙解释道:“当日在桂林之时,一小食摊前与格格有一面之缘。格格怕是记不得了。”
我尤自不解道:“那日士兵们过来强收租子,公子似乎早已不见了,为何却?”
他淡淡一笑道:“惭愧,本想为摊主打抱不平,却见有两位小姐气定神闲安坐,一时好奇心作祟,站了一旁目睹了全部,也由此得知四格格,却不想今日再见。”
我解了心头之惑,颌首笑道:“原是如此。”又瞥了临桌一眼道:“仿佛每次得见公子,都是在与他人争辩什么。”
他目视远方,朗声道:“在下见不平事,听不顺话总是想辩个黑白出来。”
我点头,孙延龄忽道:“既有如此志愿,何不进朝入仕,谋求个一官半职,岂不更便宜?”他泰然自若面对孙延龄地逼视,淡淡一笑道:“人各有志,做官非我所愿。”
孙延龄不屑笑笑,我以目示意他噤声,笑道:“不知公子这次和人争论些什么不顺之话呢?”
他亦不掩饰,坦然道:“争论广西当务之急是要做些什么。”
孙延龄冷笑道:“这是你应该操心的事情吗?”
他瞥了一眼孙延龄,淡淡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在下出身于广西,长于广西,广西是在下的衣食故土,眼见如今困境丛生,民生艰难,自当以热忱之心待之。”
我赞叹道:“说的好!公子请坐,不知公子高姓大名?”
阿离为他斟上茶来,他亦不推辞,只在下首坐了,道:“鄙姓穆,单字连。”
我待他坐定又急切道:“穆公子,以你之见广西当务之急是要做些什么呢?”
穆连无视孙延岭不悦的神色,胸有成竹一笑道:“在下所见,正是格格心中所想。”
我一愣,孙延龄没好气的道:你怎知格格想的是什么?”
穆连对我切切道:“格格微服出巡,想必一路感悟颇深,朝廷已有数年未拨粮晌,要想维持军费及藩府开销,必要速速恢复民生。大力扶植农耕生产,维护商贩营生,并减免一切赋税。当此百姓疾苦之时,即使横征暴敛来钱财亦只是杯水车薪。且再取不来,惟有百姓富庶,同舟共济才能使一切好转来。”
我微笑目视他,恳切道:“不知穆公子可否有意去王府住些日子?”
穆连闻言,略有迟疑。我看了看孙延龄,孙延龄冷面拂袖而去。穆连因而随我回府,我在他的身上依稀看出故人的影子,一时却也想不起来那熟悉亲切地言谈气度来自何人。次日,我在银安殿升堂,正式下发若干政令:从今而往,暂免三年农商税务,各县镇衙门当大力鼓励农耕。又命线安国喻全军上下,自此要严肃军纪。但凡有恃强不法,掠夺财务,扰民欺民之事。一经发现以军法处置,绝不姑息。另军中饮食所需。拨出一部分士兵来下田耕种。自给自足,银晌一概由定南王府中所出。
众人听完。皆沉默不语,半晌戴良臣缓缓道:“虽此时无战乱,士兵们仍以操练为主,奴才不知要拨出哪些士兵来种
我冷笑道:“军需官手下不就养了些许闲人吗?再说,平素操练不过只几个时辰,剩余辰光这些士兵们不是无事生非便是赌钱吃酒,长此以往,作战能力必受影响,你倒提醒了我,从此所有士兵们早起耕种,午后操练,轮班更换,若有偷懒逃滑地,重罚不贷。”
众人方不再言。
政令一出,广西民众皆欢天喜地,当街放炮相庆,倒比过年还要热闹上几分,我又特命穆连为钦察使,游走于县镇之中,以免政令被下方官员搁置。累了几日,此时我命阿离以午休之名打发了前来求见的人等,斜斜歪在美人塌上,由秋露为我柔捏着肩膀,卧房外两株茉莉花开地正妖娆,浓浓淡淡地香气萦萦缠绕在鼻尖,夹杂着放在案头上新鲜果子地清甜,我微闭了双目,下意识地伸手抚了抚胳臂,冰销单衣凉沁的触觉叫我醒过神来,又是一夏了。芒夏捧了碗蜜酿樱桃盏来,笑道:“格格用些吧,奴婢听说女子食樱桃最好不过了,极养精神地。”
秋露扶我起身,笑道:“偏你又知道这些了。”又接过来,递到我面前,我含笑执银匙,甜腻的芳香气息扑面而来,忽没由来的一阵恶心眩晕叫我失手打翻了青玉瓷碗。
芒夏和秋露皆慌了神,急急道:“格格,您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清雨赶来为我斟了杯水喂了口压压,又唤雪寒去请大夫,一时,赵麽麽等都赶了来,心神不定地时不时瞥了瞥我苍白的脸色。
过了片刻,阿离匆匆带着大夫进来,不顾得大夫行礼便要他诊脉,大夫细细斟了半晌方问道:“不知格格这阵子可有什么不适?”
我想了会道:“只觉的困的厉害,夜间身上发烫,总也没有食欲。”
赵麽麽心疼的瞅着我念叨道:“还不是这阵子忙的,早劝了您的,您只不听,直把身子折腾坏。”
大夫却捻着雪白胡子笑道:“不妨事,开几剂药吃了就好,小民要恭喜格格了。”说着,起身下拜。
屋内众人皆愣在原地,赵麽麽毕竟经事,醒过神来,大喜过望道:“大夫,你的意思是,咱们格格有喜了,是不是?”
大夫笑道:“正是。”
众人欢天喜地齐齐跪下贺喜,恰孙延龄得信赶过来,见奴才们跪了一地,只是不知所以,待满脸喜气的赵麽麽率众人向他贺喜,这才想明白,惊喜不已,忘形地抓住我的手道:“四贞,你终于怀了我的孩子,我太高兴了。”
阿离等人围住大夫询问着要注意地事宜,赵麽麽已然传了人来,吩咐着八百里加骑去京城向太皇太后报喜。
那是婚后孙延龄第一次叫我的闺名,虽有些意外,却没有想象中地甜蜜,大抵是孩子地缘故,倒也并不十分排斥。
我恍惚着抚摩平平的小腹,那里头竟孕育着一个小小地孩子,我的孩子,这个还陌生却强烈使我感触到归宿感的名字,油然而生的幸福充斥了心头眉间。
第二卷 峥嵘岁月 第十一章
太皇太后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