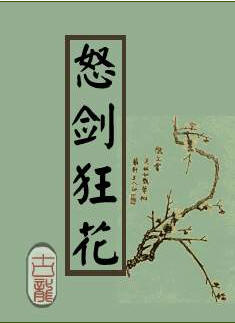狂花凋落-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了,回到卧室沉着脸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于是,五个人喝起了酒。因为心里兜着案子,聊着聊着还是聊到了这上头,小唐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医务室没有人外出,那就说明密件并非那里的人所扒窃——当然目前还不能排除与案情有关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考虑一下:外面的人是否进过‘先锋厂’,与医务室的嫌疑人接触,双方互相策划并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吴荣德、刘城:“有这个可能吗?就是外来人员能否进厂?”
刘城说:“外来人员若是工作关系要进厂的,必须经国防科委批准并出具贴有照片的公函,凭公函经我厂核批后方发给‘临时通行证’。但是,若是只进入家属区,那就只需接待方登个记就行了。
当然,根据规定,那只限于本厂人员的亲属。”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来你们是内外有别——生产区和家属区是分开实施安保的。这就好了,照小唐说的去查一查外来人员最近是否有访问研究所人员的,尤其是医务室。”
吴荣德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刘,你去办一下,这里坐等回音!”
刘城立即出门,去公安处办公室往“先锋厂”通往外面的四个卡子打电话,让火速查明2月份外来人员找研究所人的名单,一会儿,他拿着一叠纸条兴冲冲地奔进来:“有门儿!有门儿!”
这“门儿”就是名单中果然有找研究所医务室的,来人是个女知青,登记本上填着名叫卞学君,贵州省榕江县九里坝公社新花大队插队知青。二十三岁。接待人是邝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达,2月29日离开。
倪炯敏看了那张纸条,问道:“这个邝裕祥是什么人?”
“研究所医务室主任,一个有着多年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晤,倪老师要不要查阅档案?”
“暂时不查。我们还是先查一下那个卞学君吧!”
吴荣德说:“对!分两步查:一是马上和榕江方面联系,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属区查摸,弄清她来这里的目的及活动情况,重点是2月28日上午案发时间的行踪。”
“对!”
调查进展神速,次日中午,两项结果都已获取:一、榕江方面称确有卞学君这么一个女知青。二、邝裕祥夫妇同在“先锋厂”工作邝妻春节前去南京老家探亲,至今未归,邝一人居住,外甥女来后与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么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听留声机,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调查,所以无法知晓。”
吴荣德说:“就这些,似乎不大有价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终盯着曾厚望那两次‘水土不服’不放,现在冒出这个女知青来,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齐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学君当面询问。第二,找诸慧丽调查给曾厚望看病是怎么回事。第三,查阅邝裕祥的档案。”
刘城副处长带了两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学君调查。这边,小金和吴荣德找诸慧丽一调查,不禁大出意外:原来,诸慧丽在着节后临时借往“先锋厂”医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来,在这期间,她根本没去过研究所医务室,更谈不上开处方了。
倪炯敏亲自查阅档案,也有收获:邝裕祥,1930年出生于贵阳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次年,经部人事部门决定,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直至1959年底。之后,一度仍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担任医务方面的工作,还借调去过北京协和医院。1965年“先锋厂”组建时,国防科委把他调来,先在厂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后来研究所组建医务室,考虑到他技术全面,并且有过当保健医生的经历,便委他担任了医务室主任。邝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邝妻强秀凤系“先锋厂”医院药剂师,平时表现也不错。倪炯敏把档案材料连看了几遍,临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一行文字上,皱起的眉头使目间皮肤形成了一个“川”字。在公安部,他虽然不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但对那个部门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并非一无所知,他听说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破获的一些反革命特务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苏联援华、访华人员的接触或者留学苏联时,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为出卖祖国的间谍的。因此,他产生了联想:眼前这个邝裕祥有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会不会被混迹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这个联想固执地占据着倪炯敏的思维空间,最终成为一个疑点,而被他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次日,转榕江调查的侦察员风尘仆仆驱车而归,带来了同样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县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队确有一个名叫卞学君的女知青,查其档案,系贵阳市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榕江插队落户,她的舅舅是邝裕祥,“先锋厂”医生。但是,卞学君今年春节并未离开生产队,她那个集体户的全体知青都留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侦察员还带回了一张卞学君的照片,果然和邝裕祥的邻居所说的那个“卞学君”相貌不同。
这样,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个女特嫌分子冒卞学君的身份混进“先锋厂”家属区潜伏下来,在邝裕祥的配合下于2月28日去将军坟汽车站窃取了曹秋林所携的密件。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立即传讯邝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向克格勃提供了。
从那时开始,邝裕祥就意识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数据密件上动脑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邝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写)发来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协助特工窃取元月8日中国那颗氢弹爆炸后“先锋厂”研究所数据分析结论赛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达贵阳市的一个地址,显然那里有克格勃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