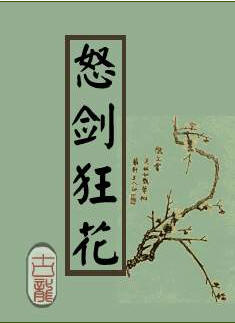狂花凋落-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午生照此办理,去红花峪一说,那边一口答应,说安排一个知青没问题。他便发出了联络暗号。十来天后,朱远芳果然悄悄来找马午生了,随身带来了甘肃方面同意她“转队”至新疆的全套材料。红花峪大队先把朱远芳安置下来,然后去办了有关手续,使她成了一名合法的“插队知青”。
朱远芳潜伏下来后,立刻着手开始活动。她找到马午生,说需要三至四公斤百分之一百浓度的盐酸。说来也好笑,马午生虽然是克格勃特工,但他没受过一天训练,又没上过学,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盐酸。朱远芳给他解释了好一会,才知道那是一种化学药水,具有腐蚀性,但他不知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搞。朱远芳说在化工原料商店或者生产资料商店可以买到,让马午生去购买,并交给他一千元钱。马午生一打听,塔城及附近地区并没有什么化工原料商店,生产资料商店倒是有的,但在塔城市里。10月1日,马午生乘生产队放假的机会去了趟塔城,生产资料商店倒是有盐酸卖的,但是必须出具经公安局盖章核准的单位证明。马午生空手返回,赶到红花峪对朱远芳一说,朱远芳皱眉不语,沉思良久方才开口,让马午生回去,说由她想办法解决。
马午生回队后的第三天晚上,朱远芳突然来了,说她已经侦察清楚,吉也克镇外的解放军7801医院药品仓库里有盐酸,她决定去盗一些来。今晚就去,让马午生给她望风接应。马午生自无二话,当即和朱远芳出发。两人赶到7801医院外面,朱远芳攀墙而人,潜入药品仓库,不一会就盗了两瓶盐酸,从墙头上递给马午生。
两人拿着盐酸回到马午生家,已是拂晓时分;朱远芳便在马午生那里住了下来。
次日,朱远芳一查验,发现所窃的并不是盐酸,而是一种有着浓烈挥发气味的药液,不禁大为沮丧,寻思只得再去医院辛苦一趟了。她考虑到医院方面会“贼出关门”作一些防范,便决定稍停几天再去光顾。这样,她就在马午生家待了下来,出于谨慎,她从不出门,终日缩在马午生卧室里。这样难免寂寞,便让马午生去同村社员处借了本小说来消遣,却不料因此留下了蛛丝马迹。
这时,7801医院失窃了铁克里老汉所献药水的消息不胫而走,终于传到了村里,马午生把传闻告诉了朱远芳。朱远芳闻之颇为吃惊,担心公安局抓住此案不放,一查到底,查到马午生这里来,于是决定把赃物送还7801医院,以让公安局偃旗息鼓。她让马午生去办了这件事。次日,朱远芳派马午生去7801医院探看,得知刑警已经撤走,不禁大喜,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今晚二上医院,把盐酸盗来!”
当晚,朱远芳、马午生二上78O1医院,不料朱远芳在窥探动静时正巧被值勤护士发现,结果差点当场被生擒活捉。两人胆战心惊地逃回巴拉坎二队,一头缩进屋里,再也不敢动7801医院的脑筋。
马午生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罢休了,哪知几天后朱远芳忽然下达指令,命马午生去塔城生产资料商店盗盐酸。马午生不敢违驳,只得答应,便去向生产队长讨了买桐油的差使。朱远芳向他作了交代,告诉他万一失风被捕,可如何推脱,并让他如何应付警方的讯问。朱远芳和他约定:如果到次日下午2点钟还不回来,她就离开巴拉坎二队回红花峪了。如他很快就获释,则速去红花峪找朱远芳。
马午生在塔城行窃失利后,从派出所放出来回到巴拉坎二队,因已过了约定时间,朱远芳早去了红花峪,他便往红花峪去向朱汇报了失利经过。朱远芳没有责怪他,说另外再想办法搞盐酸。总之,盐酸是必须搞到的。
马午生一口气交代到这里,摊开双手道:“我所干的就是这些,都交代了,请公安同志明鉴。”
是“公安”而不是“同志”的刘斯勋一边在听马午生交代,一边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朱远芳这么急切地想得到盐酸,这是为了什么?她要用盐酸来干什么?当下,他便发问:“朱远芳要盐酸想干什么用?”
马午生连连摇头:“这个,我可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敢问。”
“她什么都没说吗?比如露一点口风之类的?”
“没有,一点口风也没漏,只说要三至四公斤浓度为百分之一百的盐酸。”
对马午生的审讯就进行到这里,刘斯勋一班人此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决定休息几个小时后重新审问朱远芳。
马午生、朱远芳反革命间谍案在破获伊始,布拉哈拉县公安局已经向地区公安处作了电话汇报,公安处随即电告自治区公安厅。
公安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该案由自治区公安厅直接审理,于是往布拉哈拉县公安局拍发了“速将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稳妥押送乌市”的紧急电令。刘斯勋回到公安局想去值班小憩一会时,电令刚到,自然是无条件执行。县局当即把该案的全部卷宗材料、证据等聚拢一起,装箱密封,连同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由刘斯勋率领四名刑警、八名武警,连夜押送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对这起反革命间谍案相当重视,特地抽调了五名资深预审员组成了一个审讯班子,组长由已干过二十多年预审工作、突破过多起疑难大案的杜培生担任。杜培生接手该案后,先和其他四名预审员一起仔细阅读了全部卷宗材料,察看了证据,然后商议审讯方案,最后决定先审马午生。
马午生原以为自己的案情不算怎么严重,严重的是朱远芳,没料到竟被警戒森严地押送到了乌鲁木齐,这才知道情况不妙,一进审讯室马上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地仟侮自己的罪行。这样,对他的审讯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却供不出比在布拉哈拉看守所时更多的内容。这样,预审员所期待的从马午生口供中找到对付朱远芳沉默的突破口的希望就落空了。杜培生只能在对案情了解不深的情况下进行对朱远芳的审讯。
朱远芳从被捕一直到押解乌鲁木齐,头脑里自然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应付讯问的思考。根据她在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到的反审讯内容,她采取的方式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甘肃知青,“转队”来到新疆的。这当然不解决问题,预审员告诉她:早在下手拘捕她前,就已经派员去甘肃伊哈托黑作过直接调查,当地并无“朱远芳”其人。另外,那张上面有盖着钢印的她的照片的公安部证件,又作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手枪、无线电收发报机、密写药水之类的间谍证据等等。朱远芳听了以后,恍然大悟:特务学校所教授的东西在实践中似乎并不管用啊!于是,她就采取在布拉哈拉一样的方式,缄默不言。这样,第一次审讯没能达到目的。
几小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朱远芳仍旧不肯开口。
由于案情重大,朱远芳是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的。事先,杜培生怕出问题,亲自去那间监房察看过,并且向看守所长直接交代过:必须派责任心强的看守员负责看守关押朱远芳的那一排监房。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朱远芳竟在第二次审讯的那天晚上上吊了!
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长知道朱远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员小乔值夜班看守几个关押女案犯的监房。小乔二十六岁,当兵出身,“文革”开始那年复员来到看守所当看守员。她在部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所以被看守所长委以重任。这天晚上,小乔倒是格外认真地巡视,但她那几天正开始妊娠反应,常常呕吐。这当然不能在巡视时当着案犯的面进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约在下半夜2点钟左右,小乔又一次去呕吐,这一次吐得极难受,涕泪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些。不料,当她料理定当再去走廊巡视时却发现特务犯朱远芳已经用被单撕成的布条把自己吊在铁栅门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抢救措施又得力,总算把朱远芳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杜培生被这次事故吓得不轻,预审小组商量下来,决定把朱远芳关进另一个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监房,由所方向她们交代注意监视朱远芳,使其无再次自尽的机会。与此同时,继续对朱远芳进行审讯,但她依旧坚不开口。这样,审讯形成了僵持状态。这种情况,对于杜培生这样一个老预审员来说,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暂时不再提审朱远芳,把她“晾”在监房里,使她放松戒备之心,产生无聊之意。
这样,她为了打发时光,自然会和同监犯说话聊天,言多必失,时间稍长,估计她会在不经意中吐露口风的。
这着棋子走得很对,一个月后,经向朱远芳的四名同监犯分别了解,预审员获得了一条线索:朱远芳对北京很是熟悉,对一些街道、胡同简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对东北黑龙江农场也有所了解。预审小组分析了上述情况,初步判断朱远芳是北京人,可能是从北京去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叛逃苏联后当特工,又被派遣回国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杜培生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加大了解朱远芳的力度。经严格选择,预审小组将一名犯流窜盗窃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调入朱远芳所在的监房。按照估计,这个流窜女贼与朱有几点共同之处:北京人,女知青,在东北农常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共同话题,这样,朱远芳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经历、事情会有较多的吐露。哪知事与愿违,朱远芳一听对方是知青,似乎产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触,更谈不上吐露什么了。预审小组见事情不妥,便开始走另一步:把朱远芳的照片、体态特征、口音等材料以“协查通知”的形式发往北京、天津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那边予以调查,想弄清朱远芳的原籍,顺藤摸瓜调查到更多材料后,作为审讯她的突破口。
“协查通知”发出去后不到一星期,一直难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从而使预审小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体健壮的朱远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状是喉痛、头痛,每天去监区作巡回医疗的狱医知道后,估计是感冒,就给她眼了感冒药。但药吃下去后却并不见效,当天晚上朱远芳开始发烧。
当时同监犯都在睡觉,谁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开水时,她们才警惕起来,怀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说不定又在动上吊自杀的脑筋了。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错过了立功赎罪的机会(看守所规定阻止同监犯人自杀的被视为立功行为,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她们不睡,朱远芳倒睡过去了。她的睡,其实是一种高烧的昏沉。几小时后,她开始出现惊厥和说胡话。同监犯见状,摸摸她的额头,烫得简直不能沾手,于是马上咋呼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远芳入院的当天,杜培生就和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埋头研究了她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胡话内容,认为从“三连七排”来判断,应当是某个军垦农场的编制番号,结合同监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龙江农场,初步可以认定她曾在黑龙江境内的某个军垦农场待过。至于“盛炜富”,可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她还说过“咱俩”,因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