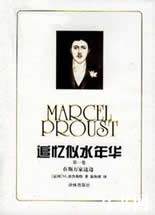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用平常做家教的钱为自己买了一件鹅黄的羽绒服,明亮而温暖的颜色,它让我想到了迎春花,我在镜前端详了半天,想着从前一色的黑与白,那是极端的颜色,万色之总与无色之色,而这黄是多么地柔和啊,它让镜中的人也陡增了几分活泼与明媚。
我开始疯狂地读书,距离期末考只有半个月了,而我欠下了很多功课,每天我把自己定在自修室里,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夜晚的时候,我独自走在校园里,回过头去看,教学楼的灯突然全灭了,只留下一片黑黝黝的阴影。这个学校正年轻。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不怕犯错,因为你年轻,一切都可以打倒重来;你可以很张扬地生活,因为你年轻,你想收获所有的目光无可厚非;你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青春,因为你年轻,你不必回头看,单单看着前面无尽的岁月。拥有青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它的美就像自由的精灵,是要在空气中自由地舞动的,它是有感染力的,让你被它吸引,被它感动,你从微卷的睫毛,从清亮的眼睛,从瑕思的表情中可以见出它的美来,你看到过一个女孩站在盛开的花前微闭起眼睛吸一口气的陶醉吗?或是提着鞋赤足踏过草坪让纤细的足踝陷进毛茸茸的碧绿?或是一路骑着车一路撒下白色的樱花?
可是究竟会有多少可供挥霍的岁月呢。红颜白发只是弹指瞬间的事。再怎么重头再来,心也不是原来那颗心,看似一晃而过,实际上都沉淀下来,这就叫做经历,你可以把它重叠为人生的背景,却不可以把它当成写在黑板上的字一样轻轻抹去,它是有一点就刻一点,刻在你的肌肤上,最后刻满全身的。但它也不是丝丝缕缕都让人不忘的,年轻的时候都是朝前看的,谁顾得上去回忆呢。能够改变这些印痕的只有时光。只有时光,它把爱和恨都可以消褪得淡若云烟,相忘于江湖,相笑于重逢,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走过便成熟悉的陌路人,见证爱的是时间,分离爱的也是时间,锥心刺骨的疼痛,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往回看,看到的也不过是一道浅痕,还有更折磨人的呢,谁知道什么是个极致呢。没有人能够逃得了时光,即使是云为衣裳花为容,云是浮云,瞬息万变,花开的是节令,年年相似,却不是原来的那一朵。什么都是变,能够守住的又有什么呢?
我等待的也是时间。某一天,我也会坐在时光的轮椅里,沐着黄昏时的阳光,淡淡地想起在我最灿烂的季节里有过怎样的悲伤,这悲伤也是消了形的,只是轻烟似地一笔,像泼墨山水画里的远影。我想真正的“老”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不再有什么盼望了,把人生都看到了头,不再有想不通的事情,不再争了,只有一个个的回忆?一重岁月就是一重隔阂,一重心情,老当真是转瞬的事吗,那倒好了,就怕岁月冗长,想让它快点走都不肯。
在复习迎考和考试的一个月时间里,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疯狂地学习,走路的时候我耳朵里插着耳塞,听外语磁带,睡前还背单词,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窗外寂寂的草坪和阳光,这阳光曾经是我所爱的,可现在只希望它快快地挪移,好带走这个冬的记忆。
在这种超负荷的学习状态中,我甚至还读出了学习的乐趣,当一本厚厚的书由复杂变为简单,心里会有多少收获和征服的快乐。况且,玻璃窗、灯光和读书人,这样的场景是浮躁中的恬淡和安静,任你流光飞舞,只守我的一灯如豆。书里的知识还是实打实的,不和你纷争,也不教你欺骗,只是安静地守望着你,等待着你,书包里的书还是你忠实的人生伴侣,你把它们丢了,沾了灰尘,它还在角落里守候,让你有一天重新拾起,掸开上面的灰尘,说就是你呵,我要找的就是你。
期末考结束的时候,我还是倒了下去,十门功课,战线打得老长,我像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终于到达了终点,身心都已虚空,再也填不下任何东西。
我懒懒地躺在床上,看着室友们整理着东西准备回家,一边忙碌还不忘问我,禾子,你又不回家吗?我说嗯。她们说那你不想家吗。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她们说那你家里人会想你的。我说他们也习惯了。
我有家么?哪里是我真正的家?我抬眼看着天花板,那上面爬着一只蜘蛛,那个黑色的小生命也在忙碌着,起劲地织着网。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是很残忍的,看着一只蜘蛛结网,等它结好了这边就弄坏这边,结好了那边又弄坏这边,结果那只蜘蛛就忙碌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补了这边补那边,本来是想结下网来捉昆虫的,结果结一张网还结不完。长大之后似乎变得善良了,对这些小生命也心生悲悯,不再去破坏它们了,也许这也是同命相怜吧,都是一样地渺小,谁比谁伟大一些。
我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头痛得紧,思维却很清晰。耳朵里还有管楼的阿姨收音机里正放着的戏剧选段,不过倒能听清一二,因为在这边呆得久了的缘故,他们的方言也大概能懂。放的是《打金枝》选段,金枝挨了附马的打正回娘家哭诉呢。其实这声音也听不分明,外面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告别的声音,我看了一会儿蜘蛛,还是睡着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其间有过迷迷糊糊的时候,隔着帘子也能感觉到人影晃动,还有搬东西说话的声音,我的意识里是想醒来的,可就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似的,怎么挣扎也回不来,梦是断断续续的,纠缠不清,我怎么理也理不清楚。
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只有很大一片光亮笼罩着我。我拉开帘子发现对面坐着一个人,我揉了揉眼睛,看清是彤云。
你醒了,她说。
嗯。我躺在床上仍然不想动。
放假了,你去哪里?
就在这里游荡。我懒懒地回答她。
她嘴唇张了张,随之又闭上了。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马上要走了。
哦。我从喉咙里冒出一个字。
她站起身,拿起行李,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走了出去。
我想她是想和我谈谈杨涛的,但她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是绝对不愿谈及的。不去碰了,就自然慢慢淡化了,一碰,过去的时光就回来了,隐藏得再好,也是一个旧病复发,还以为自己真是刻骨铭心,永世不忘了。
我爬起来,站到窗边,正午的阳光正温暖地照着,我该去哪里呢?
第十三章
黎乡,一个水乡的小镇,从火车站出发,乘两个小时的火车,再乘半个小时的汽车,一片连绵的屋宇被一脉流水环绕的,便是了。
我曾经在江南的很多地方行走,想从那一扇木窗、一处阁楼、一块青石板中找到它千年的遗韵,然而毕竟是远了,新砌的小楼一幢幢地立起来,流水也不再是清洌的了,混沌一片,上面还漂着垃圾,沃野千里的土地也被征占用来建造为工厂。
黎乡也不例外,当我站到它的边缘望去,我找不到母亲所说的痕迹,母亲的记忆中是流水绕孤村,沿河红杏招的景致,二十年的光阴,像蝉蜕一样,一层层地蜕了皮,我终于明白母亲在十多年的岁月中一直不肯重回江南,因为她害怕回忆的触痛和物非人非的难堪。
但越往里走,古镇的风貌便一滴滴地展现出来,仿佛岁月在此凝滞,一色的黑的瓦青的檐,屋檐下还有燕子筑的巢,临街是敞开的门,临河也是敞开的,是以前供主妇们到河里淘米洗濯的。路人很少,迈着悠然的步子,有小孩子窜来窜去地闹着玩。
我手里拿着抄写的地址,黎乡红石巷120号,这是母亲少女时代住过的祖屋,但它是否还在呢,我又该怎样介绍我自己呢,我会得到承认吗,对这些,我都无法自己作出回答。唯一可以证明我身份的是母亲的照片,这是她以前带走的一张,梳着两根麻花辫,有着纯真的眼睛和白里通红的脸。母亲喝着水乡的水长大,她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江南女孩的古典和温柔,即使年岁逐增,她仍然保留着心思的细腻和敏感。
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仅仅是一偿母亲的夙愿吗,还是我自己想要追寻母亲年少时的踪迹,还是我有解不开的江南情结,想把它的精华收纳其中,还是我认为这个平静的小镇可以让我养伤?很多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我却发现我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走进这户江南的人家,当初母亲的出走对亲友来说是个谜,而二十年过后我带给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越是走近,我的心里便愈加忐忑,但还是到了,却是门扉紧闭,荒草丛生。
我到附近的人家询问,他们告诉我这里的人家早就搬迁,有个叫张平的一家就住在前面的新街。张平的名字我从母亲的口里听说过,是她的堂哥,从小一起长大,两人的感情是亲兄妹一般,在母亲很小的时候由于一场意外事故,父母和弟弟都遭遇不幸,便寄居在他家。
这是一户看起来家境也不错的人家,三层的玲珑的小楼,当街一道门檐,锁住里面的院子。我刚走到门口,一条狗蹿了出来,把我吓了一跳,这狗却是不咬人的,只隔着一段距离汪汪地叫,因了狗的叫声,里面走出一个男人,中年,有些发福。
请问张平在吗?我问。
我就是。他狐疑地看着我。
我是张月的女儿,我叫佟禾。
张月,他喃喃自语。我突然后悔了,二十年的时光可以改变多少事,他还记得母亲吗?我站在那里一时颇为尴尬。
但他马上想了起来,随即是不能置信的表情,直到看见我母亲的照片,才确信这个当初不告而别的小妹妹有了这么大的女儿。
那你妈妈呢。他急急地问,并朝我的身后望,好像是母亲跟他开玩笑,故意要藏起来似的。
我说我母亲四年前因病去世了,他一下子怔住,随即红了眼睛。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前提及母亲的离世,这也是不能碰的,隐在心里太久了,一碰就是痛。今天在这个被我叫做舅舅的人前,我的悲伤才一下子释放了出来,这就是亲人了,血浓于水,隔也隔不断的,你走累了,受伤了,就可以到他们的怀抱里歇一歇的。人其实都是很脆弱的,脆弱得经不起一点伤害,或者一点温情。
就这样我走进了江南的人家,在这个冬日的下午,我和舅舅聊着二十年里的人和事,和母亲有关的都被抬了出来,长久的想像一下子变得真实,反而让我觉得迷离恍惚了。这时光就像水上的桥和壁上的青苔,再怎样不着痕迹,年复一年地生,也是经不起岁月侵蚀的,是不变里的变,是天远地长里的沧海桑田。
他说,你母亲的命也真够苦,不过幸好有了你这样一个有出息的女儿,小月一定也是欣慰的。
那个男人呢,他过得怎样?我颤颤地问。
他蛮好的,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儿子,就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舅舅说。
那他找过我妈吗?我问。
找过,后来没找到另娶了。我的舅舅,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他永远不会明白母亲突然出走的原因,他以为从小性格有些孤僻的母亲突然对未婚夫不满意了,或是吵架了,一气之下做出的叛逆行为,可是真相又有什么重要呢?时间的沙漏已滴完一层又一层,不是有“一笑抿恩仇”之说么?
舅舅留我过年,说你就把这里当自己家吧,以前我没照顾好小月,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学校里。
我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拒绝显得矫情,何况我实在不想忍受一个人锁在一间屋子里的孤寂,那让我窒息,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见过了舅母和他们的女儿张雨薇,舅母是一个普通的慈爱的妇人,她并不知晓我母亲的事,在她嫁入张家之前,母亲已经离开,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忙来忙去,看我在看她,便温和地冲我一笑。雨薇比我小几岁,刚上高中,还在一个纯真但很容易感伤的年龄。
吃饭的时候,他们老往我碗里夹菜,说这个你尝尝好不好吃,那个怎么样,雨薇的话却是很多的,讲着今天她到哪里看见了什么好笑的新鲜事,边说边笑,咯咯咯地把饭也吃得断断续续。她爸妈微笑地看着她,饶有兴趣地听她讲,并不责怪。这幕合家欢的场景是普通一景,却是要叫我掉泪的。这样的场景于我是陌生的,在饭桌上我总是沉默寡言。舅妈注意到了我的异样,说,怎么了,吃不惯吗。我忙抬起头说,不是的,只是吃得有点急,被哽住了。她忙递给我一杯水,看着我喝水,问好点了吗。我说嗯。
晚上,我和雨薇睡在一起,天下起了雨,我拥被靠在床沿上,听着嘀嗒的雨声,想这就是幸福吧,有温暖舒适的床,有明亮的灯光,在冬日的边缘可以自由地想些人和事,有多少疲惫的旅人会眷恋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