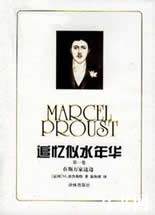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于金雷
。
第一章
我叫禾子,来自西北。
开学报道的这天,我背着两个包,一脸风尘地来到这座城市。由于火车晚点,到达车站时已是夜里一点钟。校车早已离去,当人群渐渐散尽,留下的只有我和一些等车的旅人。
这是我陌生的城市,我将要在此生活四年,但此时,我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浪人。我决定在车站呆一晚,尽管有被驱逐的危险。我把包放在脚下,靠在椅子上。大厅里很安静,有人在椅子上打着盹。对面有两个中年妇女看了我半天,目光中有好奇和同情,我知道我的大包,我脸上的风尘,和我的矮小引起了她们的怜悯之心,也许她们认为我是个正应当在中学里念书但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孩子。她们的眼神带着一个母亲的慈爱,然而这对我早已陌生,我没有向她们的好奇报以一个礼貌的微笑,只是转过了头透过窗看着这个午夜的城市,想像它白昼的模样。
我很困,并且很不舒服,几天的旅途早已折磨透了我的神经,汗水和车上带来的种种气息困扰着我,我的一件白衬衫早已被染成了黄黑色,我就要以这副模样见到我未来的老师和同学。
巡逻的人来了,问我是否是等车的人,要我出示车票,因为车站不许人宿夜。我解释说我是个大学新生,我今天来晚了,并给他们看我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佟禾,华东大学,金融贸易专业。他们说,来晚了,那为什么不住旅馆。我说我没找到旅馆,到处都客满了,我就在这呆几个钟头,天一亮我就走。也许是通知书和我憔悴的模样打动了他们,他们最后答应了我。
其实我只是不想浪费钱,尽管我最不能忍受别人的怜悯。
我迷迷糊糊地打着盹,但手里一直紧紧抓着脚下的包的带子。在四点钟的时候,天就开始亮了。这座东方的城市很早就苏醒了过来,空气变得微薄而透明,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不远的一座大厦,写着“五星饭店”的字样。霓虹在晨曦中逐渐失却颜色,灰白的鸽子在一排排低矮的屋宇间盘旋。
我在车站的洗手间里洗了脸,并用梳子梳理了一下我的头发。从镜子里,我看到了一张憔悴苍白的脸,没有血色的嘴唇和疲惫的眼睛。这是一张并不生动的脸,一脸冷静和倔强。
报到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露出惊讶的神情,但这只是在我的预料之中。两个女生把我领往各处去办理手续,在去寝室的时候,她们说,你好能干哦,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只是笑了笑。
我的寝室在11幢302室,看得出来才整修过,有未散尽的油漆的味道。刚进房门,一个红色的影子就蹿了过来,接住我的东西,说,你来了,就剩你一个了,刚才我们正说你,然后她看了看我的身后,说,你父母呢?我说,我是一个人来的,她惊讶地张了张嘴说,哇,真了不起!要知道你是我们中最远的人呢!在这时候,我已看清了她。她很漂亮,有一头乌黑的短发和慧洁的眼睛。她的红裙子象火一样的烧,说明她热情、外向、开朗。
另外四个女孩也在,大家分别作了自我介绍,我一时记不准,只记住了那个红裙子女孩,她叫彤云,人如其名。轮到我时,我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叫佟禾,别人都叫我禾子。然后在她们略楞的时候转身整理我的床铺,我很累,何况身上的气息让我渴望清凉。
当这一切都整理完后,我钻到水管下舒舒服服地冲了半天。水漫过全身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我的大学会是怎么样的呢?我曾经对她有过很多的想象,那是我一个人坐在夕阳的余辉里看着它渐渐垂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或者是在穿过阴暗的小巷里的时候,我的眼前会幻化出它美丽的图象,它像电视画面中的校园一样,有着幽深的林荫道,在一片繁花前面,一个批着一头长发的女孩拿着书静静地默看,偶尔小声读出书上动人的词句。还有,我想象中江南,我所背熟了的“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迹”和“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报道之后是十来天的入学教育,每天花半天时间去听院长、班主任、辅导员、图书馆等等的教育,其余时间是无所事事地闲逛,一不小心迷了路了,想旁边的人打听,他们热情地指引着你,然后在转身之后窃笑着说:“新生!”
晚上,舍友们经过几天的沉默后,开始逐渐引出话题,她们首先谈到了中学时的生活和自己家乡的风景。我听到了来自四川的王贞所谈到的秀丽的巴山蜀水。南京的李晓的六朝金粉。她们都说完了然后问,禾子,你呢,说说你吧,你最远。我说什么呢?我的记忆越过一重重山峦,看到了那片土地。每天早上,太阳会早早地升起,照亮一望无际的草原,在草原的边际,便是沙丘,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草原会被染成一片玫瑰色的绯红,我常常会痴痴地看着那轮落日,那样美丽的又悲壮的沉落,那时,我的心是孤独的,因为天地间自身的渺小,然而又是满的,满的要往外溢,因为整个天地都在我的心中,我盛满了宇宙的寂寥与苍茫。于是,我跟她们说起了那轮夕阳,说起了草原上的牧歌,说到“一片孤城万仞山,”说到阳关的千年雪。我的记忆被打开了,所有动人的词句都涌到我的脑海里,我滔滔不绝。等我说累了,她们又问,禾子,真的有那么美吗?我们早就想去看看,以后跟你一起回去。我沉默了。真有那么美吗?是的,它有壮烈的美,有博大的美,然而在我居住的小城,脏乱不堪,夏天有成群的苍蝇飞舞,冬天冰凌接满一地。永远都是明晃晃的太阳,它让我感觉不到慰心的温暖。何况还有贫穷呢?还有自然生态的恶化呢?回去?我会回去吗?那里有我留恋的东西吗?那有属于我的家园吗?
又一个夜晚,彤云问我,禾子,你为什么叫禾子呢?你们那里有稻禾吗?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我母亲,她是江南人,她是为了怀念。“哦”,她们都很感到惊讶,但我转移了话题,她们也便知趣地不再问。
母亲,一个水乡长大的女孩,她有清秀的脸和灵秀的眼睛。江南是母亲唯愿长醉不醒的梦,是她索饶了多少年厮缠了的多少年默念了多少年的宿愿,几番相思又相思,然而十五年的时光她始终不曾重回江南,她总是给我讲着乌蓬船和流水,剥开皮白嫩脆生的红菱,还有广阔的稻田和河边新生的芦苇。母亲讲着这些的时候眼中一片柔情,我知道是一次次经过记忆的过滤而愈加美好的的画面让她沉醉了,我轻轻的靠着她,看着她被太阳晒红的脸庞上爬满了风霜,她已经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但她的神情像一个初恋少女一样幸福与甜蜜。然而当她回过神的时候总是轻轻地叹息一声,眼里的光彩也黯淡下来。直到最后的时刻,她抓了我的手,嘴唇蠕动,我知道她所要说的是她家乡的名字,她的眼里写满了遗憾。
第二章
我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当有人嚷着不适应的话,当第一次离开家的人说开始想家,当有人埋怨打水为什么这么挤时,我已从图书馆借来了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在我用布帘围起来的空间里静静地阅读,这是我一直向往的书,最初是被它的书名打动,“生活在别处”,一句多少富有哲理性的话,我还不能完全知晓它的含义,只知道它是如此简单而有力的击中了我。
当我正看得入神的时候,彤云一把拉开我的帘子,说,禾木,怎么这么用功啊,今天是中秋节,英语角有活动,一起去啊,在这里多孤单!说完就把我拉走了,我这才想起今天已是中秋,这是团聚和思乡的时候,但对我而言,它只意味着月圆而已。
月色很好,清辉满地,还有桂花的香暗暗地送来,彤云在我身边絮絮地说她想家,她说她家里的人一定在吃月饼赏月了,刚才她打电话回家时差一点哭了,她说,禾木,你怎么不问候家里人一声。我说不必说了,我们家不讲这些的。她奇怪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说,这所学校大而冷清,又是在郊区,住在这里会很寂寞的。我说其实寂寞跟人多少与否没有关系,置身人群反而更加孤独。彤云说,禾子,你是个比较奇怪的人。我说,我只是一个太过平凡的人,仍进人堆就找不见。
英语角比较热闹,还请了几位外籍教师,但我如同听天书,做在那里不明所以。后来又搞了活动,几个人抽签坐在一起,用英语对话,我的组里有两个大二的,一个大一的,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英语有多蹩脚。我结结巴巴地说,但我的发音还是让他们如在云里,他们的神情写着茫然,但仍很礼貌的对我笑着,我的脸已是在发烫,觉得自己像是在台上演讲时忘了台词般地难堪。后来一个人接过话题,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告辞,我看见狄云还在那里谈得兴高采烈,就独自离开了,回来的路上,仍然是冷清的月光,当我开始觉得孤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可以很好地融身于人群里的人,在陌生的人群里,我的笑容僵硬,带着伪装的表情,然而熟悉又怎么样呢?曾经在周围的人,因为熟悉,却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压抑。
回到寝室时,我无心看书,听着室外不绝于耳的蛙声和虫鸣,这样的宁静和我在家时不同,那也是宁静的夜,那时,人声都归于沉寂。我独自坐在狭窄的庭院里看星空,那里的天空很近,似乎可以听到星星的呓语,还看月亮,看它表面的阴影和它在云中轻轻地滑行,怀想传说中的故事或自己再臆造一些凄美的故事。我平静的坐着,但我知道我的内心骚动着,我早已厌倦了周围的一切,我渴望着逃离,逃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熟悉将我紧紧地束缚,让我窒息,而现在新的一切在我的面前缓缓的展开,我可以在高远的星空下散步而不遭遇同样的目光。
彤云回来后,脸兴奋地发红,她说,禾子,你怎么一个人走了,今晚真是好有趣,我遇到一个英语说的很好的人,一个大二管理系的男生,以后可要向他多多请教。后来寝室里的人也回来了,她们有的是开同乡会去了,有的找同学玩。我在这里的同乡是很少的,何况我又拙于交际。
中秋过后,开始正式上课了,我们班是四十人,男女各占一半,虽然开学时都见过面,作过自我介绍,但早已印象模糊。从宿舍到教学楼有一段长长的路,有很多人骑自行车挤在大道上。我是喜欢步行的,因为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对着一个迎面而来的路人猜测他们的内心,然后在擦肩而过时想象有可能的交集。清晨的空气里有淡淡的草香和树林里潮湿的气息。太阳在我身后拉长了影子,照着我白色的布裙。这条裙子是我临走时赶做的。只是一快棉布,我把它做成最简单的式样,只在前面打了一个蝴蝶节。
经院的楼是新造起来的,雪白的墙壁上尚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与之相对的是紧挨其后的文科楼,一幢老式的木结构的房子掩映在千竿修竹之中。毫无疑问它是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城堡,还没走近,你就可以闻到从那些雕花的门窗里散发出来的故纸的气息。
走到教室的时候,人还很少,大家礼貌地打着招呼,只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女生没有回过头来,她的桌上摊着一本书,似乎已沉浸到了书里。我喜欢在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很从容,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别人,何况保持距离可以让自己清醒。我打量着教室、大阶梯、有一壁明亮的窗,这是我喜欢的,可以侧过头去看风景。
《西方经济学》,一本全英文的教材,我知道我将遇到一个大的挑战。从第二天开始,我六点种起身,跑到学校的花园里读英语。雌菊已经开了,金黄的耀眼,宁静清新的早晨,旁边的水杉林里有白鹭扑腾腾的飞。
但我的英语还是没有多大起色,英语课上,安德先生在课堂上眉飞色舞,手足并用,但我仍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回答问题时我依然涨红了脸,用一点都不纯正的发音搏得同学们善意的嘲弄。我开始在课堂上出神,那天,安得先生正在讲台上解说英国文化时,我的眼睛和深思都飘到了窗外,我看到窗子下的那棵红枫已经有了如火的叶子,阳光透过它的枝叶斑斓陆离。不远的文科楼里,有女孩穿着纯白的长裙翩然而入。邻居突然捅了捅我,一下子把我从恍惚中惊醒。我转过头来,看见安德先生责备的目光和全班同学的注视。先生没有说什么,继续讲了下去,但他在下课的时候把我留下了。
此后的日子我依然到花园里早读,只是不再一味留连天空的颜色和草丛里的昆虫。从一个个单词的发音开始,我艰难的爬行。
这时和寝室的同学都混熟了,我知道彤云的话最多,她的衣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