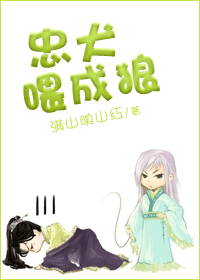巴别塔之犬-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吧,”我说,“不过你真的确定要做吗?”
“当然,”她说,“我很确定。”
当时,我发现自己很厌恶这种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根本就是那对父母在伤心欲绝中的举动,因为他们无法割舍自己的女儿。虽然我不认识这个女孩,但我很怀疑她是否会选择这种方式让双亲对她永远怀念。她愿意把过世时的那张脸摆在家里,让他们随时转个头就能看到?她愿意把自己死亡的那一刻永远深植在他们的心中吗?我想,如果悲伤的目的是为了释怀,是为了在失去亲人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那么这些悲伤中的人们的行为只会造成反效果,不仅对他们自己不好,也会伤及他们对那个可怜女孩的回忆。
但现在,和悲伤已变得如此亲密的我,已不敢再确定他们是错误的了。
露西去世时,我承认,当我看见她的脸并没有因为从高处坠落而淤青时,心里确实偷偷感到一丝安慰。不管我过去怎么说,但在露西的葬礼我一样不能免俗,必须让亲友瞻仰露西的遗容。每当有人对我说“噢,她看起来还是这么美”的时候,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慰藉。那时我跪在她的灵柩旁,思绪突然一片空白,忘掉了小时候所有学过的祷词,我只知道把手伸出去抚摸她的脸,只知道要以最用力的方式凝视她,将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特征全都牢牢地凝固在自己的记忆里,因为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把视线落在她的身上。那么,我是否改变了主意,也希望能留下一张露西遗容的面具挂在墙上,或许还挂在那张她在世时所制作的面具旁?不,我还是不想这样。不过,我以后再也不会对那些失去亲人的悲伤者说他们的这种要求是错误的。我再也不敢这么说了。
我原本担心露西接下这份有点病态的差事后,多多少少也会让自己陷入忧郁的情绪,没想到当她回家时,竟然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她很漂亮,”她说,“虽然因为生病变得很瘦,但仍看得出她的脸真的很美丽。”
我试着想象死去的少女躺在棺木中的景象,却完全没办法和“美丽”这个字眼对上号。
“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替她化妆,因此她的皮肤很苍白。我的动作必须很快,他们给我的时间只有一个下午,不过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把模子打好了。并不是我故意草率,而是当你不需要一直叫人安静别动时,事情就简单多了。”
“她的身体冰冷吗?”我问。我接触尸体的经验并不多,即使是我自己的父亲过世,葬礼中的我都刻意和他的尸体保持一些距离。
“没像冰那么冷,但有点凉。体温当然比活人低。”
“你和她的父母谈过话吗?”
“当然。我坐下来和他们仔细讨论,以了解他们希望面具做成什么样子。”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说到这里,我还是无法想象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会要求做这种事。
“看起来相当正常。当然,难过是免不了的,她父亲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不过我愿意为他们达成心愿,他们都很欣慰。原本他们还以为不可能找到任何人做这项工作。”
那是当然的,我心想,但没把话说出来。
“好吧,”我改变话题,“你说我们出去吃个晚餐如何?折腾了一天,你需要重返活人的生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说,“我们叫外卖食物来家里好吗?我有点急着去地下室,想趁着印象还鲜明的时候把工作做好。”
“没问题。”我回答。其实我有点失望。这天是星期五,我盼了一整个星期,只希望今天晚上能和露西共度,一块儿做些甜蜜浪漫的事,从晚餐开始展开周末的生活。虽然那时我们还算是新婚期间,但我很久没见过她因为工作而如此兴奋,因此尽管心里不怎么舒服,我还是决定别破坏她的工作热情。于是我走进厨房,拿起电话订了一份披萨。
露西整个周末都在制作这个面具,偶尔几次从地下室上来,也只是为了到厨房拿东西吃,或是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沉思,罗丽和往常一样,这段时间都待在地下室陪露西,因此对我而言这几天可说是相当孤单。到了星期天晚上,我坐在客厅不知看了多久的书,一抬头才发现罗丽站在我面前。
“嗨,妹妹。”我说,同时伸手拍拍它的头,当我这么做时,我注意到它的项圈上粘了一小张纸。我把纸撕下来,看见上头写着:“露西·蓝森小姐想邀请您移驾到地下室,为她新出炉的作品举行发布仪式。”我顿时出声大笑,这几天的不快活一笔勾销。我连忙走向地下室入口,由罗丽在前替我领路。
我一下楼,便看见露西瘫坐在那张旧沙发上。那张刚完成的面具就放在工作台上,盖在一块布下面。
“你现在才收到字条吗?”她问,站了起来。“我半个小时前就派罗丽送上去了。”
“我猜,这家‘背脊犬快递公司’的效率并不太高,你永远无法预料它何时会不按计划,溜去吃个东西什么的。”
“你准备好欣赏我的作品了吗?”她的语气很兴奋,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当然。”我说。我已经作好准备,只等她征询我的看法时,就说出最美丽的谎言。
她要我坐下,闭上眼睛,然后把面具放在我手上。我有点惶恐地把眼睛睁开。
这张面具很美。这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张脸居然这么漂亮。在我先前的想象当中,我以为她会完全依照实际的样子上色,以为她会依照死者的模样,在面具上漆上苍白的肌肤,画上残存一点点红的苍白嘴唇,并画上明显的睫毛以突显紧闭的眼睛。我是说,先前我认为这张面具看起来会和死者一模一样。然而,她却不是这么做的。她的确为这面具漆上了纯白色,但那只是背景,重点是为了强调画在脸上的娇艳花朵。她使用的色彩都是鲜明的——没有柔和的淡色彩,也没有粉红色或婴儿蓝。她用明亮鲜活的绿色,画上茎干和叶片,再覆以红色、紫色、黄色和蓝绿色的花朵。她还在花瓣上饰以金色花纹,制造出阳光照耀的效果。这些花都不是葬礼上用的,不是那种经过可以排列,既正式又令人感到肃穆的殡葬花朵。她绘在面具上的都是不知名的花朵,是那种会随风吹到各地、以各自独特的样式生长的野花。
女孩脸型的特征只能依稀分辨,露西不但未作任何强调,甚至让人在一瞥之下,不会以为这是一张人的面孔。浅浅的眼洞、微隆的鼻子和稍弯的嘴唇,都宛如羊皮纸一般被花朵覆盖。而当我一旦注意到这些脸部特征,我便无法不继续细看下去。我能看见呈现在这张脸上的青春,看出她成年后肯定会更加散发的美丽。面具给人的感觉丝毫不悲伤,这是最难能可贵之处,尽管我知道这张面具是依据一名早逝少女的脸型制作的,可我在凝视时并不会感到难过。在某个程度上,我甚至认为那种在生前拍的照片,即使笑得再灿烂再充满活力,却只让人看了更加沮丧——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些发生在毕业典礼之夜的车祸,隔天,毕业纪念册相片会伴随新闻出现在报纸上。这种事总是屡见不鲜。看见这些不幸的孩子别扭地穿着新裁的衣裳,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确实会让人心碎。不过,这张面具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它不会令人感伤,它呈现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可能。看着这张面具,我理解了即使是死亡也能死得优雅和美丽,我理解了当女孩的双亲拉着露西的手,恳求她去看一眼他们的女儿时,他们那时候所见到的景象。
我捧着面具坐在那儿,大半天说不出话。原本准备好的谄媚恭维的客套话语,此时早都烟消云散了。
“如何?”露西问。
“太美了,”我说,“我压根儿没想到会这样。”
“你本来以为它看起来会很恐怖,对吗?”她笑着说。
“要我老实说吗?没错。”我再仔细地把这张面具看一遍。
“不过,你觉得做成这样是那对父母想要的吗?这张面具做得有一点儿抽象,说不定他们希望你做得比较写实一点。”
她很认真地看着我,“什么意思?”她说。
“意思是,我只担心,万一他们希望符合现实,希望完全依照她实际的模样去描绘上色。”
“她的脸就是这样,”露西固执地说,“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的就是她的脸。”
“对,那是当然的,但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你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制作?”
“‘这种方式’?”她说,“你说的‘这种方式’是什么意思?”她的音调拉高了。
我起身向她走去,伸手想拉她的手,但她却躲开了。
“别误会,”我说,“我认为这张面具美极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你所做过最好的一个。我只是担心那对父母太保守而不懂得欣赏它。”
“你觉得他们会不喜欢,”她说,“你一定觉得它还不够好!把面具给我!”她一把从我手中抢过面具。
“不,露西,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她垂着头,面具在她手中不停颤抖。“你不喜欢它。”她尖声说。跟着,她的眼泪掉了下来,忍不住开始啜泣。“你不喜欢它,因为我做得太糟了。”
“不是。”我说。
“是!”她说,“你讨厌它。”她把面具扔在地上,用力以脚践踏。凝固后的纸浆非常僵硬,赤着脚的露西一时无法将它破坏。
“住手!露西!”我说,“你这样太可笑了,快住手!”
她捡起面具用力丢向工作台,随手拿起一把用来修裁面具边缘的利刃,把刀尖一遍又一遍用力往面具上戳。纸浆顿时裂开,扬起一阵细微白色粉末,但她仍不停止。直到面具表面布满了破洞,直到面具鼻部完全碎成粉末,她才把刀放下,看着自己干的好事,接着她用手捂住脸,哭得全身发抖。
我后退了几步,感到既惊讶又生气。“你干吗这么做?”我厉声说。
“不知道,”她说,声音像卡在喉咙里,仿佛无法吸进充足的空气。“我也不知道。”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无法向前一步给她任何安慰。好一会儿后,她才把手从脸上移开,抬头看着我。她的脸很红,但额头上却出现一道白色新月形状的痕迹,那是她把指甲深深掐进皮肤所造成的。
“你知道吗?”她说,“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有孩子了吗?”说完她转身冲上楼梯。
我呆站在地下室里,看着已毁掉的面具,听着她的脚步声从我头上越过。我听见大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知道自己现在又是孤独一人了。
25、打字
我无法控制,每天都打电话进心灵咨询中心,只希望能听见阿拉贝拉夫人的声音。通常我只要一听见人名,确定接电话的人不是她,便会马上挂断电话。但偶尔,当我觉得孤独的时候,就会继续留在电话线上,等着听听看她们(虽然也有男的咨询师,但接电话绝大部分的都是女性)会和我说什么话。有时候我会主动告诉她们整个故事,有时则让她们自己去猜。“我敢说那绝对是个意外。”她们总是这么说。“看来她是非常爱你的。”她们这样告诉我,“虽然你可能有这种感觉,但其实你并不孤单。”她们还说,如果我再等待下去,就会有一笔意外之财和料想不到的爱情。她们要我别丧失希望,告诉我塔罗牌呈现的是一片晴朗的天空。“死牌”代表改变,而非死亡。她们问我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是自杀的吗?我永远也没办法让自己说出这几个字。我能教会狗儿说话吗?这么问岂能不惹来一番嘲笑?我曾问过其中一个人:“你看见过任何关于动物的预兆吗?有没有看见关于狗的景象?”而她则立刻要我放心,说我那只走丢的狗目前不但平安无事,而且很快就会自己回家。这些咨询师中有些既狡猾又心狠,她们会想尽办法让你留在线上。其中有一个说我生了重病,另一个则说她预见到一场灾难,但只要我别急着挂断电话,或许就能找出预防和化解的方法。“最近你会觉得很疲惫吗?”她们总是这么问,但凭良心说,有哪个在凌晨一点钟和陌生人讲电话的人没有这种感觉?她们会说:“有个和你一起工作的女人……我看见她好像有个S开头的名字?好像又是R开头的?”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位咨询师问我是否认识一位R开头姓名的女人时,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然而,当她发现我没有马上回答,无法从我的语气探出任何肯定时,她便马上改口:“不对,好像是T开头的女人。泰莉?泰丽莎?”而我才发觉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候,也许是我把这些事说太多遍了,我会不小心主动说出露西的名字,而她们立刻询问她的出生日期。她们一边理牌,一边要我想着她的脸。我照做了。我完全集中思绪想着她。她们会根据我和她的星座,说一些关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