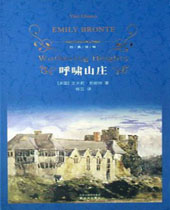起解山庄-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过神来,余悸犹存的古瑞奇不禁怒火如炽,抡起大半截木桩就往庄翼头上猛敲,木桩挥落,却“碰”的一声闷击在横里伸出的火旗上,他人被震退两步,回顾皇甫秀彦,正待叫骂,皇甫秀彦已冷着声丢下一句话:
古瑞奇才只一楞,皇甫秀彦已赶过去救援两个同伴,那两位,一个断手,一个断足,人躺在血泊里,混身抽搐,就差不曾辗转哀号啦。
………………………………………………
红雪 OCR 扫校
起解山庄……第二十章 阴毒
第二十章 阴毒
是左肩胛一阵接一阵的剧痛,把庄翼给痛醒了,他勉强撑开涩的眼皮,瞳孔立即受到光线的刺激,但觉一片眩花,他闭上眼,再缓缓睁开,这才比较适应了些。
其实光线并不强烈,只是白昼的天光罢了,透过墙上的窗口映进来,明晃晃的,好像久不见踪影的冬阳也露了面。
庄翼发觉自己睡在一张竹床上,下面着极厚极软的褥子,身上还盖着棉被;置身的所在,是一间石屋,石砌的墙壁,石块地,见光的窗户嵌有铁条,整个格局相当冷硬粗糙。
他手足匹肢都没有任何束缚,仅仅腰际扣着一付铁环,铁环连接着一条铁嵌入石壁之内,简单明了,却极为有效,堪称别出心裁了。
肩头的骨伤,已被接合凑拢,显然经过治疗,疗后的余痛十分耗神,他同时也察觉面颊上的伤口亦已上药贴敷起来,不知是谁有这份好心?但可断定不会是那“大棍王”古瑞奇。
全身仍然感到虚脱乏力,内功难聚,有似大病一场后的孱弱疲态,他默默忖思,自晕迷到现在,其间又隔了几多时空?
另外一桩令庄翼纳闷的事,是他奇怪自己仍然活着,照道理说,对方没有留他活口的必要,这会增添许多麻烦,且难保不节外生枝,只有一个解释,那便是“一真门”的邵康尚在己方控制之下,令对方投鼠忌器,不得不暂留退步,可是,这个顾虑,抗得过古瑞奇强烈的报复意愿么?
不论是什么原因,好歹他还没死,这个事实却不容争辩,人有一口气在,就表示仍有希望,目前,但在一步算一步,且等着应变吧。
于是,门开了,听那门栓响动的声音,可以确定那是一扇铁门。
有人走了进来,庄翼定神瞧去,不禁笑了,来人正是皇甫秀彦。
皇甫秀彦来到床边,微俯上身,脸上的气色虽然青白憔悴,却透着友善与关切:
“总提调,料想你也该醒过来了,如今觉得好了些吧?”
庄翼的声音哑:
“还好……皇甫兄,那一剑,我非常抱歉……”
皇甫秀彦强颜一笑:
“没关系,所谓『当拳不认父』,交手拚博之际,原本谁也顾不得谁;我还要感谢总提调手下留情,你那一剑,只要锋口再移寸半,就能直插心脏,替你除掉一个后患了!”
庄翼摇头道:
“也许是巧合,皇甫兄无须领情……”
皇甫秀彦手抚右胸,低沉的道:
“这里一道半尺口子,剑刃由下往上划过,只要你当时稍稍挪臂挫腕,微带剑势,受创的部位便完全不一样了,总提调,我心里有数。”
略一沉默,庄翼道:
“我还以为,这一倒下去,就再也睁不开眼了,现在还留有一口气喘,大概都是皇甫兄你的维护吧?”
皇甫秀彦苦笑道:
“表面上的理由,是怕邵康遭致报复,其实这不成理由,因为我们原奉有为达目地不惜牺牲、不计手段的谕令,但我为邵康争命,也没有人愿意明着反对,以免留下口实,致遭物议,这一着,算是暂时保住了总提调的性命……”
出于庄翼吃力的道:
“古瑞奇一定大为不悦吧?”
皇甫秀彦道:
“何止『大为不悦』?简直暴跳如雷,和我吵翻了天,他非要立即置你于死不可,是我坚持不能拿邵康来殉葬,在对邵康的问题有所处置之前,决不可断然行事,他拗不过我,一气之下,已亲自赶回门里,向我们当家的要裁示去了!”
庄翼道:
“皇甫兄,你判断鸥老将会如何因应?”
叹一口气,皇甫秀彦道:
“不瞒总提调,我们门主十有八九会依其所请,下令照古前辈的要求去办,也就是说,你已危在旦夕!”
庄翼倒看得开,他淡淡的道:
“凡是人,都有个大限,限期早晚,莫非是命,活得长、活得短,也只有看自己的造化了。”
皇甫秀彦愤然道:
“为一个严良,为古前辈赌一口气,竟要你遭受如此报复,实在不值,严良是个什么角色,我们清楚得很,仗着有这么一层关系,人死了还在穷搅合,以非作是,胡打滥仗,真令人不平!”
庄翼道:
“你有你的立场,皇甫兄,感谢你的相惜相助,仗义执言,但却不要由此伤害到你自己,否则,我就更于心不安了!”
皇甫秀彦欲言又止,好一阵,他才轻声道:
“总提调,我是『一真门』的人,是我们当家的心腹左右,所以,我不能私纵于你。”
庄翼平静的道:
“我明白。”
咬咬嘴唇,皇甫秀彦接着道:
“可是,如果别人来救你,又在我的力量难以抗拒的情形下,或者,你自己设法脱困生出,那就不是我的过失,我也对得起家门了。”
庄翼笑笑,道:
“当然。”
皇甫秀彦霎霎眼:
“不过,此中尚须有点技巧。”
庄翼慢吞吞的道:
“皇甫兄,你们有几个人在这里?”
回望门外一眼,皇甫秀彦道:
“连我一共三个,但那两位如今躺在床上疗伤,根本已派不上用场。”
庄翼悄然问:
“此地距『老龙口』多远?”
皇甫秀彦道:
“就在『老龙口』近郊……”
庄翼仔细的道:
“距离『老龙口』城内『鲤鱼牌坊』,大约有多少远近?”
估量了一下,皇甫秀彦道:
“不出五里……”
顿了顿,他又迷惑的道:
“总提调,你问这个干什么?”
庄翼笑了笑,道:
“皇甫兄,请问一句,我的剑,是在你那里吧?”
皇甫秀彦道:
“在我那里,只要时机适宜,自当奉还。”
庄翼放低声音道:
“有烦皇甫兄取出我的本色剑,旋开剑柄后端的锥头,里面浅槽内盛着大约一匙量的淡红粉末,皇甫兄只要将那些粉末洒于屋外附近,就算成全我了。”
皇甫秀彦望着庄翼,有些莫明奇妙的道:
“这,这算帮了你什么忙?”
庄翼道:
“其中自有道理,还请皇甫兄偏劳。”
皇甫秀彦道:
“你放心,总提调,我等会一定去办,但能不能告欣我这样做到底奥妙何在?”
略略移高平躺着的身子,庄翼道:
“剑柄浅槽内的淡红色粉末,名叫『七里传音』,用人的鼻子去闻,它毫无味道,但对一种称为『小鹞鹰』的异鸟却特别敏感,这种『小鹞鹰』放飞空中盘旋,只要范围不超过七里,它都能嗅到『七里传音』的气味,指引出正确目标;而『小鹞鹰』的放飞准点便是『老龙口』城里的『鲤鱼牌坊』,距离以牌坊为中心向四方估算,所以我才有先时的几个问题请教,这样一说,皇甫兄大约明白了吧?”
一拍大腿,皇甫秀彦道:
“绝,真是绝,总提调,难为你是怎么想出这个追踪妙招的?简直匪夷所思!”
庄翼道:
“这不是我的创作,皇甫兄,这乃是我们祖师爷留传下来,嘉惠本会弟子的德泽,我有幸蒙受,却不敢掠美。”
怔了怔,皇甫秀彦疑惑的道:
“听你的口气,总提调,你也有家门、在帮口?”
庄翼笑而不答,皇甫秀彦接着道: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晚上那几个面人,闻说身手凌厉、功夫了得,从他们的打扮及行动上看,都不像是公门中人,总提调,可能就是你背后那个组合里调派出来的高手吧?”
庄翼坦然道:
“不错,他们五个,的确极为优秀。”
皇甫秀彦摇头嗟叹:
“是我们低估了你,又昧于敌情,第一波行动才闹了个灰头土脸,全军覆没,古前辈当时还以为胜券在握,吃定了呢!”
庄翼苦笑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风水轮转,比人们想像中更快,第一遭我拔了头筹,眼前不就裁了头?无论是谁,都没有『吃定』这码子事!”
皇甫秀彦微带窘迫的道:
“老实说,总提调,我们虽然赢了这一局,可不怎么光彩,使的手段未免迹近卑陋,但这是古箭辈的设计,我实在不好反对……”
庄翼谅解的道:
“我也猜到是古瑞奇出的点子,难为他还亲自易装上阵哩!”
皇甫秀彦搓着手道:
“提到他,我可得快点去办事了,万一他老人家提早回来,场面就不好处理啦。”
庄翼忙道:
“皇甫兄,粉末子散出去之后,大概很快即有反应,为免误会,你最好能先做回避!”
皇甫秀彦问道:
“会来得这么快法?总提调,那『小鹞鹰』,该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放在天上飞吧?”
庄翼解释着道:
“是这样的,一旦在我身上发生警兆,也就是出现不明的危险状况之后,我身边的暗桩会立时传报我的组合,组合里就会轮留不停的放出『小鹞鹰』升空寻觅,一只鹞鹰可以在空中盘旋两三个时辰之久,几只鹞鹰轮番放飞,一天十二个时辰里,几手就甚少间隙了,所以『七里传音』散洒世去,很快就会奏功……”
皇甫秀彦道:
“你确定他们已在找你?”
点点头,庄翼道:
“这是无庸置异的,皇甫兄,只要六个时辰之内不能确知我的行踪,警兆即行发出——我来到这里,大概不止六个时辰了吧?”
皇甫秀彦道:
“我们是昨天傍黑遭遇上的,现下已到今日午时,早超过六个时辰了。”
庄翼笑道:
“是以我肯定他们已经展开行动,皇甫兄,你也得预做因应才好。”
皇甫秀彦震奈的道。
“问题是,我不能回避……”
庄翼不解的道:
“为什么不能回避?”
皇甫秀彦道:
“这么一来,岂不是做得太明显了?我们古前辈必起疑窦,反而弄巧成拙,脱不了干系!”
沉吟着,庄翼道:
“倒也有理,事情要办得似模似样才好,不能把你牵连进来,落个徇私纵敌的罪名,不过,待假戏真做,又怕发生意外,皇甫兄,我们之间的默契我们知道,但来驰援的人却不知道,双方一朝动上手,是个什么结果,就难说了,假如有个万一,叫我两边都不好交待!”
皇甫秀彦笑道:
“你宽念,总提调,我的本事虽不算高明,可是连打带走的穷门还懂,到时候,我会表演逼真,进退有致且皆大欢喜,包不叫你为难……”
庄翼道:
“这要分寸拿捏得极准才行,皇甫兄,你有把握?”
皇甫秀彦信心十足的道:
“等着瞧吧,总提调。”
望着皇甫秀彦开门出去,又将门在外落锁,庄翼的一颗心却总定不下来,世间事,变数太多,在没到尘埃落地之前,是谁也说不准的。
***
入夜之后,气温然下降许多,别看白天出过太阳,一到晚间,那股子冷冽更甚,不曾飘雪,却更觉寒意逼人,吸一口气,都像拿把冰碴子掖进喉里。
石屋内没有火盆,当然就无法取暖,庄翼躺在床上,不错是盖着棉被,但棉被在此时所能发挥的御寒效益竟然奇差,人盖着被,仍觉冻得慌,丝丝寒意,透过棉絮的间隙钻入,人冷得肌肤上直起鸡皮疙瘩,这还是在屋子里呐,呼吸之余,口鼻前已是白雾成团。
庄翼奇怪自己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怕冷起来?这表示体力衰退了?
他随即又自我解嘲似的笑笑,身后两处创伤,迷药的药性刚过,加上昨午至今晚粒米未进,体力怎会不衰退?
皇甫秀彦大概全心用在安排如何施计纵人方面,连送水送饭这点最起码的招待都忘啦!
正想着,他忽然听到门外传来轻微的拨动铁锁声,那不像是钥匙插入锁孔时的清脆声响,倒像是什么人在小心翼翼的试探铁锁的结构性能。
“卡喳”一声脆响又起,跟着门被推开,一个全身黑衣的面人倏闪而入,人一进来,立即背贴墙上,目光炯然四搜,很快便落定在竹床上:
“是六爷么?”
棉被掩盖的庄翼伸出头来,压着嗓门问:
“樊庆堂?”
黑衣人一个箭步抢到床前,单膝点地,这个时候犹不忘施礼请安:
“六爷受苦了,弟子等接应来迟,尚乞六爷恕罪!”
庄翼忙道:
“无须多礼,庆堂,且先把我腰上的铁环打开再说!”
那樊庆堂先将手上的一对铁拐斜插后腰,迅速掀开棉被.十指略一伸展,就着铁环四沿仔细摸索,不片刻,他已摸到环扣上的锁眼,又从靴筒中抽出一截带勾钢丝,插进锁眼开始拨弄起来。
庄翼一边等开锁,边闲闲的道:
“这次来了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