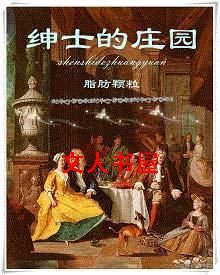庄园-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兰桂坊。它静静的立在维港之畔,挂一方不算大的招牌,在灯红酒绿,五光十色中自显一分傲气。KR里面有路易十六更有顶级碧螺春,有水晶杯更有竹青筒,有按摩椅更有美人榻。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就那么自自然然的相交织,没有矛盾没有尴尬,仿佛本来就该这样。纷飞纱幕相隔,在那一瞬间的迷失里,早已不知今昔是何夕了。
门口立着接引客人的女孩儿见了我,甜甜的一笑,“两位晚上好”这些女孩儿据说都是内地来港读大学的孩子,利用空余时间,赚点生活费。我对这没什么概念,倒是庄恒很是鼓励这种自食其力的行为。庄氏就有招聘兼职学生的惯例,更有些出色的,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庄氏旗下的企业,成为庄氏的员工。
“请问您有位吗?”
“怡宁斋。”我道。穆怡说是定了那里。
她带了段路,便在廊前站定,“两位里面请。”
挑帘进去,那贵妃榻上倚着一人,见了我们,眼波流转间似有光华闪动,不是我们董穆怡小姐还能是谁?!杨林大笑道,“乖乖,弄成这样,也不知道招惹谁呢。”
穆怡撇了撇小嘴儿,站起来,“早早的就来了,等你们没得把我饿死。快快快,叫他们上菜。这怡宁斋特配的可是上等的竹叶青,好喝的很。”
四个凉菜,四道主菜,一樽雕花酒壶,几个小小的荷叶陶瓷杯一一被端了上来,末了还远远的扬起阵阵琴音。我点着头笑道,“有意思。嗯,要是佳冉回来咱就全了。”
徐佳冉要说还是穆怡先认识的,后来连带着和我们混熟了,也是个干脆利落的爽快人。她是正儿八经的吃金融饭的女人。做过一阵子操盘手,基金、股票、期权、期货炒得门熟。五年前被汇利高薪聘了过去,没过两年,又被宋天明挖到了庄氏。她当时还跟我笑言,“可不能再跟你没轻没重的瞎胡闹了,你可是我正正经经的老板娘。你一个不高兴,跟老板吹点枕头风,我徐佳冉就不用在香港混了。”说着又扑上来跟我姐长姐短的了。她在庄氏市场业务系统干了一段时间,就被提升到庄氏母公司参与证券投资的管理。前段时间去了美国公干,听庄恒说是让她去跟李继刚一起安排庄氏国生在美国的上市的事儿去了。
佳肴美酒,知己相伴,从时事到八卦,挨个儿侃。
“对了,亲爱的,你跟庄恒怎么了?”酒到酣时,穆怡问我。
“还能怎么了,昨天有人需要他,我放手让他去了。”我仰头又喝尽了杯中酒。
“那女人到底想怎么样啊?”杨林忿忿的问。
“不知道。明摆了,人家不要名,也不图利,吵都不知道怎么吵。”
穆怡看着我,眼里的悲怜一闪而过。我知道,她也很尴尬。她现在担的角色似乎正正跟骆清珏一样。她能说什么?
我了然的拍了拍她的手,“我明白的。你别瞎琢磨,你跟可她不一样。我,庄恒和她之间夹杂的除了情爱,还有恩义。有些事,糊涂了,就让它糊涂吧。倒是你,你跟黎隆源到底怎么打算的?就这样没名没份的跟着他?也不要个孩子?”
穆怡是喜欢孩子的,光看她疼庄宇他们的劲儿就知道了。一晃都四十多的人了,立马生都免不了当高龄产妇。想当初,我知道穆怡跟黎隆源在一起,还是因为她惨白着脸,来找我安排做人流。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杀了黎隆源的心都有了。
“我没告诉隆源,我不能要这个孩子。如果注定这辈子我董穆怡只能爱上有妇之夫,我也决不能让我的孩子成了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这是穆怡十年前说的话。没想到,时至今日,她孤身如故。
穆怡的眼里亮晶晶的一片,我不忍再说什么了。杨林在旁边握着我们的手,叹道,“有时候看着你们,真不知我自己算不算极端幸运的了。”
“不说这些了,来,咱们干。”穆怡甩了甩头,吆喝着。
“来,干!今朝有酒今朝醉。”
“就是,干了!”
三只酒杯碰到了一起。
记不得我们喝了多少酒,总之是一直喝到深夜了。等我们摇摇晃晃的相扶而出,才发现我们好像谁也开不了车了。相视苦笑,她俩招部计程车也就算了。我恐怕就有些麻烦了。得,找司机来接吧。我晕晕乎乎的按了半天,才算是按对了家里的电话,也没听清是谁,总归不是荣妈就是福庆。报了地点,叫她安排司机来接我。
你还真别说,我们家这司机来的简直就是神速。没过多大一会儿,就到了。穆怡非要自己打车回去,理都不理我,摆摆手自走了。我自己开来的车只能停在KR那边了。先送杨林回太子道,再绕回半山庄园去。
下了车,我脚下有些个不稳,福庆赶上来扶着我。夜里的风吹过来,我胸口有些个闷,干呕了几下,吐不出东西来。福庆急得直叫,“太太,太太。”又赶着招呼当值的小丫头过来扶我。正忙乱间,一声低斥传来,“怎么回事?”
朦胧间,好多个庄恒的影子朝我走来。“蕴茹!”我被揽进了他怀里,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急急的抱起了我。转而吩咐了福庆一大堆的事儿,什么放热水,冲酽茶,叫崔炯过来。听得我直发晕,我只记得自己挣扎着跟他说了四个字,“你别管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20章
这一夜睡得极不安稳,一会儿像是被火烤,一会儿又像是被冰镇。身边似乎人来人往的,梦也是乱七八糟的。醒过来时,已换好了睡衣,躺在床上了。四周都是黑蒙蒙的。我艰难的咽了口口水,喉咙生疼生疼的。头重的很,晕是不晕了,就是太阳穴发紧。扭头看看,庄恒不在身边。我撑起身子,想去摸床头柜上的水杯,不料水杯没摸着,倒碰倒了什么瓶瓶罐罐的,乒乒乓乓一阵响。“蕴茹!”庄恒从与卧房相连的露天阳台外赶过来,顺势扭亮了一盏小壁灯。“怎么醒了?感觉怎么样,还难受的很吗?”他一边扶着我,一边在我腰后垫上枕头。“来,喝点水。”说着,他将备好的水杯递到我嘴边,我就着他的手喝了两口,然后摇摇头。
“什么时候了?”我问。
“三点多了。”他坐在床边。
在晕黄的灯光中,我看着我的丈夫。记忆中已经好久好久不曾这样打量过他了。不知从何时起,我这永远都那么英姿勃发,温和淡定的丈夫居然也让皱纹爬上了额头,居然也已两鬓染霜、银丝点点。他皱眉凝视着我,我有那一瞬间的冲动,伸手去为他抚平,不成想,我们的手在同时举起时相触,他迅速的握住了我的。
“蕴茹,”他唤我,有一点点难以置信的喜悦。“要不要吃点什么?叫他们煮点粥来?还是,”他微微靠近了我,带着点笑意道,“我去给你煮?”我知道他想起了什么,在美国那会儿,我不舒服闹着不肯吃东西的时候,他总会亲自下厨煮上一碗香喷喷的白果粥哄我吃。是有好些年不曾动过了,没想到他还记得。
“不要,我吃不下,胃里怪难受的。”我道。
“那叫崔炯再过来看看?他就在客房住着呢。”庄恒伸手覆上我的额头。
“不要。”我大大的白了他一眼。这人,醉个酒还把人家崔炯给召来,小题大做不说,崔炯见了我还不得训死我。没得丢脸死人。
他有些无奈的笑了,复又沉默。停了一会儿,他理了理我凌乱的鬓角,缓缓的道,“蕴茹,有些事这些年我可能想错了,也做错了,对你不住。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我用手指按上了他的唇,“恒,我累了,陪我睡会儿,嗯?”
展眉淡笑中,他脱下披在身上的睡袍,躺到我的旁边,揽我入怀,轻轻的拍抚着。我听着他坚实有力的心跳,慢慢睡去。
也许在今晚,我特别的软弱;也许在今晚,我特别的脆弱。也许我已经撑了太久太久了。时间?不光他需要一点时间,可能我也需要,好好的想想我的生活,我的路。
翌日我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居然发现庄恒也还睡着,一手还搭在我的腰上。这可是奇了怪了,我轮值应是下午返工,起来再去也不晚。他可是一年365天除了不在香港和公众假日外,雷打不动9点整要坐到庄氏的主席室里去的。我推推他,他“唔”了一声,不情不愿的睁开了眼,含含糊糊的道,“早啊。”
“还早呢,这都几点了。起了吧。”
“嗯。”他慢慢的坐起,顺手把放在床前榻上的外袍递给我,自去洗漱了。等我们穿戴好下楼去,就看见崔炯和宋天明都在厅里侯着。
“恒哥,嫂子。”他们一起站起来。
“正好,崔炯在这儿,给你做个检查。”庄恒对他们摆摆手,径自对我道。我受不了的白了他一眼,崔炯对着我极不认同的摇头,嘴上恭恭敬敬的答,“恒哥放心。”说着带头走了。
我只得跟着崔炯过去。因为我工作的需要,庄园里设着一个诊疗室。说是诊疗室,其实是可以跟外面那些不大不小的诊所相媲美了。身后传来宋天明和庄恒的对话。
“指数多少了?”
“今早低开,但走的还不错。我嘱他们了,798到了您之前吩咐的位,就出货。这是报告。”
“嗯,766的位还不够低,再压一压。”
“是。恒哥,胡焕明今天早上来,想见您。我说您没回来,请他先回去了。他还想见楠少爷,正巧楠少爷今天在交易所那边,也没见着。”
“这个老胡啊。我知道他什么事儿。这样,你去打听打听,看看他跟汇利那边接触过没有。你跟我上书房来。”
当我坐到诊疗室里时,崔炯和他的助手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我赶紧声明,“你别给我做胃镜,钡餐也别给我吃。”
“现在我是你的医生,听我的还是你的?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崔炯带着口罩,眼里一丝笑意也没有,更全然没有对庄恒的那份恭敬。我们熟得很,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同学。不过是我在港大的时候的事儿了。那时候我整个人一天到晚都浑浑噩噩,心不在焉的,压根儿都不知道自己同班有些什么人。说来也巧,庄恒雇家庭医生的时候把他给请了,我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同学。他在港大毕业后,又到英国去留学5载,回国后在一家高级私人医院当医生。做的是有钱人的生意。用他的话说,走的那是高端路线。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穆怡,据说是一见钟情了,追了3年,可惜襄王有梦,神女无心。伤心之余,他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等再出现的时候,突然宣布要结婚。新娘居然还跟我有那么一点沾亲带故,就是施蕴晴的小姑赵晓曼。我见过她几次,那一脸的假笑,直叫我心里寒颤。也可能是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总觉得崔炯从穆怡到赵晓曼品位落差实在太大。不过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各花入各眼,说不得。
检查结束后,崔炯摘下口罩,很严肃的对我说,“你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穿孔那是迟早的事。还有你的颈椎,转起来那么咯噔的响,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就是不肯坚持做牵引。”
“我有做spa的,美容也会有按摩…………。”我试图狡辩。
“那能是一回事儿吗?”他哭笑不得。确实,碰到我那是医生的悲哀。
“胃那是老毛病了,我少喝点酒就是了。颈椎那是职业病,你敢说你没有?”我满不在乎的道。正好看见崔炯的小助手站在他身后抿着嘴儿窃笑。
庄恒想错做错了什么事,我没兴趣知道;他需要多少时间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次,可能是由我做出决定了,轮也该轮到我了。
三天之后,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在推迟了很多很多年之后,终于发生了。那天我带着何英、王竞他们巡查病房,“3号床昨日日间有腹痛的症状,晚间伴有低烧。”
“药用了吗?”
“用了,腹痛止住了。还有点低烧。”
“一个小时之后,给他抽血化验一下。”
“好的。”王竞点头答应着。
“还有,你盯着点观察室那边。就算其他科室没有病房,放到急诊观察室,你们也要安排好。我昨天过去,就看见怎么把孕妇安排在流感病人旁边了?床位再紧张,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在我们急诊科出现。四个观察室可以调整的嘛。不要把人往里一带就算完事了。”
“好。我去调整。”何英道,“观察室那边也有困难。注射室就占了两个,冬季寒流来了,打点滴的人特别多。”
我正想说话,就听到一声细柔的女声,“施蕴茹医生?”
我回头望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