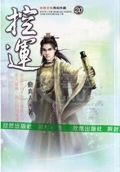主体的命运-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此,需要把穷人禁闭起来。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由于穷人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因而无社会地位,穷人只有禁闭起来DG。但福柯紧接着又说,禁闭是个严重错误,是一个经济失误:它通过排除和清洗,抑制了贫穷,又通过救济穷人,维持了贫穷。尽管由于工业发展需要劳动力,穷人可以再次在国家机体中发挥作用,但劳动力市场有限,因此,穷人无法摆脱贫穷DH。即使所有闲散人员都有工作,人类也不能消除某种贫困,贫困注定要发生,并且必然与各种社会形态共存,直至人类历史的终结。原因在于贫困使富裕成为可能,穷人穷了,富人和国家才会富起来。贫困是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 102
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75
分,倘若没有穷人,全人类就会变得贫困,穷人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荣誉。这种贫困不能受压制,也无法得到压制,而是应该受到歌颂和尊敬。
D I福柯还指出了18世纪有关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根本不是癫狂之解放含义上的;我们决不能说它允许人们给予癫狂之人以更多的仁慈的或医学的注意。
相反,它通过双重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使癫狂更加牢固地与禁闭相联系。“
D J 这里说的双重联系无非指:使癫狂成为禁闭力量的真正象征和拘禁世界内荒唐和无法挣脱的代表;把癫狂看作所有拘禁措施的典型对象。
古典时代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在17或18世纪,禁闭实践与医学互不认可,医学与癫狂的治疗很少有关,医学远没有治疗的权利。但是,不把癫狂分析为一种特殊痛苦,而是许多疾病中的一种,却十分重要。哲学问题和医学问题指引着这种分析。哲学问题关注的是“理性”的本质以及“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间的区分,关注那些把癫狂假定为“理性”的对立面并把“理性”当作判断疯人的行为的伦理标准的来源的问题。而医学问题关注的则是癫狂的行为、倾向和多样性的分析。然而,在17和18世纪,这两个问题不仅密切联系,以至于癫狂的医学分析往往诉诸于哲学问题,而且精神和肉体在癫狂的分析中也是密切相关的。
只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两个问题才渐渐分离;只是到了19世纪精神病学的出现,人们才开始把癫狂看作精神的疾病。因此,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并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始于17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而是在19世纪对应于当时的特殊哲学问题而发
…… 103
85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生的。
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癫狂之间的连续对话,古典禁闭则是一片沉寂。但这并不绝对:语言介入了并非被真正抑制的诸多事物中。禁闭、监狱、土牢、甚至拷打也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言对话(即斗争的对话)中。
然而,在18世纪末,人们把癫狂视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这就提供了对话的破裂的可能性,并把癫狂与理性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的、结结巴巴的、不完善的言词都抛弃、遗忘了。
癫狂与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
在精神疾病的平静世界里,现代人不再和疯人交流思想了。精神病学的语言,作为理性面对癫狂而作的独白,只有在这种沉寂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来。
三、现时代的癫狂
类似巴歇拉尔的科学史方法,福柯的癫狂史看法也有两个主要的决裂,一是发生于17世纪中期的大禁闭,二是18世纪末P。比奈尔和S。图格把疯人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体验癫狂的新方法就是把癫狂视为“精神疾病”的现代心理学看法。
福柯认为,“对疯人进行治疗的时代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时代”。
有关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理论发展促使人们把癫狂视为精神疾病。
在英国,贵格会教改革家S。图格在1795年在约克城外成立了收容所,从而迈出了疯人解放的第一步。收容所位于约克城一英里外的富饶畅快的乡间,不太象监狱,更象是农场。它给疯人以人道款待。而法国医生比奈尔在比赛特释放
…… 104
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95
疯人、给疯人以自由这个经过却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图格的收容所和比奈尔的疯人院起相同的作用,但图格却在宗教背景(贵格会教)内建立自己的道德体制,而比奈尔的收容所则建立在纯粹的世俗的道德秩序上。这实际上就是解放疯人的两种形式:一是成立全新机构以摆脱旧机构;二是对始于17世纪中期的古典机构体制进行改头换面。
他们两人都把疯人从旧的总医院的肉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确立起“家庭”
环境。由于医生象父亲一样监视和惩罚病人,因此,通过迫使他们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罪责,医生象父亲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他们。图格赋予家庭以一种社会尚未默认的具有原始价值的威信,以使这个家庭发挥一种反精神错乱的作用。
由于在疯人院中,人们不仅把疯人看作有罪的孩子,而且还是其行动需要别人精心监视和估价的陌生人。这样,在以前总医院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医生,现在在疯人院里因发挥着父亲和法官的作用而成了关键人物。
福柯认为,收容所能起到一种道德上和宗教上的隔离作用,所以图格的“慈善”行动并非一般“解放”。我们必须重估图格的工作的实际意义。实际上,在图格创办收容所的过程中,他用一种沉闷的、令人痛苦的责任替代了癫狂的自由恐惧。确实,收容所不再惩罚病人的罪过;但它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组织了这种罪过;把罪过组织为疯人的自我意识,作为与看守者的一种非相互关系DK。图格以“道德治疗”
为名在收容所里加以实践的劳作本身就是有一种抑制作用,比所有肉体上的强制手段都要高明。因为这种劳作丧失了任何生产价值,而只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强加给癫狂病人,病
…… 105
06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人毫无自由可言。图格还提出了一种比劳动更为有效、比其他观察更为有效的方法,即“受人尊敬的需要”。
倡导疯人院,实行精神病学改革,这确实把疯人与其他非理性之人区分开来了,穷人不再受到禁闭,疯人的肉体也得到了解放,并被置于一个道德教育体制中。然而,福柯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为了从精神上更好地控制疯人,其实就是巨大的道德监禁。
在疯人院的沉静世界里,病人受到理性的正式代表(医生)的永久判定和对象化,医生则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客观癫狂,使疯人对自己不能吸收合理的行为准则而悔恨。医生的任务是对病人进行伦理监视,并宣称自己拥有科学知识。
实际上,医务人员的行动不必依据有关疾病的客观定义或具体的疾病诊断,而是要依靠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以及爱情等的秘密的那种威望。因为他的观察、他的言词足以使病人吐露隐情,使癫狂的假定消失,并且最终使癫狂屈从于理性。
医生的言行具有消除狂乱、恢复道德秩序的力量DL。然而,对医生本人来讲,他自己的权力的合理性以及病人的地位则要求一种有关科学客观性的实证神话,因此,某种有关癫狂策略就转变成精神病学这门学科了。
福柯在《精神疾病和心理学》中略为鲁莽地指出:如果没有道德监禁的极度残暴,即19世纪的“博爱主义”在伪善的“解放”幌子下禁闭癫狂,那么精神病学等心理学就不可能存在。福柯强调,以治疗疯人的精神为目的的道德实践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精神病学首次在西方科学史上表现出几乎是完全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断使隐藏的道德
…… 106
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16
力量发挥作用,以摆脱实证主义的限制。
图格和比奈尔所创立的疯人院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结构和价值观: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父亲的权威为中心,违法与惩罚的关系以司法为中心,癫狂与无序的关系则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医生正是从这些关系中获得了治愈疾病的权力。
然而,从19世纪初始,医生全然忘掉了了这种道德实践的意义,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封闭在实证主义规范之中,其结果是这种实践活动愈加变得隐蔽,精神病医生的力量愈加神奇,从而医生与病人间的关系日益陌生,医生成了魔术师。
福柯的结论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病学实践是某种产生于18世纪末、保存于疯人院生活习俗中并且为实证主义神话所掩饰的道德策略。”
D M 长时间来,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癫狂被监禁在道德世界中。疯人院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宗教的道德内容一如既往,疯人院是社会道德的延续地。
弗洛伊德的态度较为模糊。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物理科学的客观研究的一种延伸,因而他是实证科学的倡导者。但另一方面,他是第一个在实证精神病学的空洞形式下面发现医生与病人之间特殊关系的人,他是第一个把这种关系看成动态整体并加以严肃看待的人,并消除了所有其他疯人院结构的神秘性。尽管他改变了比奈尔和图格在禁闭中所确立的结构,并确实使病人从他的“解放者”
、疏远他的疯人院存在中解脱出来,但他并非把病人从疯人院存在的本质因素中解脱出来,他重组了疯人院的力量,并通过把这些力量集中到医生手中而使这些力量膨胀到最大值。这样,由于精
…… 107
26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神分析没有压制医生的力量,医生作为一个疏远的形象仍是精神分析的关键人物,因此,精神分析不能、也不可能倾听非理性的呼声,也不能在非理性之人的身上辨认疯人的迹象。
“精神分析虽能解释某些癫狂形式,但它对非理性的独立运作仍然陌生。它既不能解放,也不能描述,更不能最为合理地说明这一运作中最关键的一切。”
D N如果说,在古典时代,曾存在癫狂与理性之间进行对话的痕迹,在禁闭癫狂的行动中以及疯人选择放弃自己作为理性存在并受到癫狂的奴役的自由的瞬间中,我们能发现这个对话,那么,虽然在18世纪末,非理性生活在荷尔德林、内浮尔和尼采、阿尔托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但也是昙花一现,而在19世纪初,即使这种并不充分的对话和自由也被剥夺了,因为非理性的力量正面临并抗拒一种巨大的道德监狱。
显然,福柯并不认为比奈尔和图格解放了疯人,他并不接受“解放”故事的通常说法,即把“解放”描述为仅仅是由人道主义情感激发出来的博爱事业的结果。因为这种说法不仅掩盖了现代疯人院产生的条件,而且还看不到这些条件并不主要关切疯人的人道治疗。
在使疯人院成为可能的诸多条件中,医学和医生本身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
福柯把发生于18世纪末的对待疯人的态度变化看成前现代禁闭体制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前现代禁闭体制并不是惰性的,内在于该体制的变化为18世纪末疯人院的产生提供了某些条件。
尽管福柯对改革家们作了讽刺评论,但他无意攻击改革家们的动机。
《癫狂与非理性》之于古典时代的文化如同尼采的《悲剧
…… 108
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36
的诞生》之于古希腊文化。前者考察了为古典理性所排斥的非理性,后者则阐明了处于日神秩序压抑之下的酒神因素。
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福柯思想呢?比较客观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不能纠缠于细节,切莫用某个简短时期、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特例来辩驳福柯的思想。因为他考虑的是较长时期的、全欧洲的普遍情况,这就蕴含着福柯的论述不可能丝毫不差地符合他所限定的那个时期内的每一个特殊时刻或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区域,因为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真的东西。他的限定只能是近似的、总概的。其次,福柯尽力把癫狂的分析置于特定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中,弄清楚前后左右的关系,如在论述人们对待癫狂的态度时,联系到当时发生的经济危机、法国大革命的政策等。这应该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学说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再次,福柯不仅重估了比奈尔和图格等医学改革家的实际工作,公正评价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且还向传统发出了两个挑战:一是引了帕斯卡的话“人类必然会发疯,若不疯便是另一种癫狂形式”
,这就立即引起了读者质问自己现有的关于理智与发疯的任何简单区分,因为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