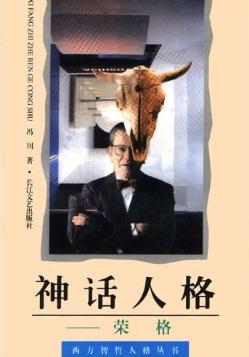人格裂变的姑娘-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碧尔脱去潮湿的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踢掉湿鞋,颓然倒在窗前的绿色靠背椅上。
她不认为这房间是自己的,但从服务台女人讲的意思来看,她也不认为这房间是属于别人的。
一时间,她只是瞪着大眼,茫然望着窗外,看着那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费城晨报》社占用的旧房。但总是坐在那里也没有意思,她便取出那两份报纸来。
费 城 调 查
城 市 版
适宜各阶层人的独立报纸
我眼皮累得要合上了。星期二早晨,1958年1月7日
1月7日,这意味着我丢了五天。
◇ 人被射上186英里高空 共产党人如是说
◇ 加文谈导弹发射台价格问题
◇ 85界国会 今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我不在世上时发生了那么多事!飞行员完成爬高壮举后完全降落
我的爬高也是壮举。那些街道。那些台阶。那么多街道。我丢失了时间,这就不仅仅是降落了。
费 城 晚 报
星期二,1958年1月7日
付帐。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西碧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是她穿着上床的?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这不是她的风格。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西碧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西碧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但西碧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西碧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西碧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人格裂变的姑娘》作者:'美' F·R·施赖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二章 内心世界的战争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
西碧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西碧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西碧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开了。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①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西碧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她母亲在西碧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西碧尔的父亲,更不用说西碧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母亲(自称为“伟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她不会听从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西碧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西碧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